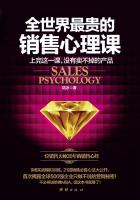后来,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公司股份,这些股份本可以让他成为百万富翁。一天,我告诉他,一些年轻人因为拥有公司的股份,他们赚的钱比他要高得多。我们已经投票表决过,想要吸纳他成为合伙人。他无须承担任何金融义务。因为按我们的惯例,他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钱,我们将在日后从红利中扣除。
“不,”他说,“我不想一直想着公司运作的事。我要管理工厂已经够忙的了。只要你们给我一份你们觉得合适的薪水就行了。”
“好的,船长,我们会按美国总统薪水的标准付你酬劳。”
“一言为定。”这个小个子威尔士人说。
炼钢行业的竞争者一开始并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很清楚炼钢厂起步时的困难,不相信我们在一年内能生产出钢轨,因此,他们拒绝承认我们是竞争者。我们刚起步时,钢轨的价格大概是70美元一吨。我们向全国的代理商征求订单,给他们最优的价格,在我们的竞争者发现前,我们已经接了好多数量的订单了——足以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有了如此先进的机器,如此完美的计划,琼斯船长挑选的如此有才华的职员,加上他是个如此卓越的经理,我们大获成功。我想我得特别提到这个记录,我们第一个月的营业利润达到了11000美元。我们的会计系统也相当了不起,让我们可以了解确切的利润数额。我们从铁厂吸取了经验,了解到一个确切的会计制度意味着什么。在制作过程中,材料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每个步骤都有专人核对,这是最好的提高利润的方法。
这次在炼钢行业的新尝试有如此好的开端,我开始思考去度假,我一直渴望的环游世界可以实现了。于是在1878年的秋天,J.W.范德沃特先生和我出发了。我随身带了几个小本子,开始每天用铅笔写下一些感想。我并没有想过要出书,但是我或许可以自己印一些我写的随笔,在私人圈子里传阅。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装订成书的感觉相当好。当印刷商把包裹送来,我把这本书重新读了一遍,试着决定是否值得把这本书送给朋友。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还是把书送给朋友,然后等待他们的评价。
一个为朋友写书的作者,没有理由去担心刻薄的反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被批评的危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朋友们的反应都很好,都说很喜欢这本书,至少他们说的有一部分是出自真心。每个作家都倾向于相信赞美。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克希尔是第一批来信赞扬的,他抱怨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一开始读这本书就舍不得放手,直到凌晨两点读完后才休息。我还收到了几封相似的信件。我记得有一天,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先生来见我,说他准备好好赞扬我一番。
“为什么呢?”我问道。
“哦,我把你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是吗,”我说,“但这不算是什么夸奖。我的其他朋友也这样啊。”
“哦,是的,但是可能你的朋友中没有像我一样的人。除了账本,我几年没读过一本书了。我一开始也没打算读你的书,但是当我读了个开头,我就放不下了。五年来,能让我看完的书只有我的账本。”
对于朋友们的话,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但是一些其他人从我朋友那里得到了这本书,也很喜欢,我就这么兴奋地过了几个月,但我相信这些话并不是谄媚。我又加印了几次,满足越来越大的需求。报纸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精选摘要。最终,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要求我出版这本书。所以,《环球之旅》出版了,我也终于成为一个作家。
这次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当时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正处于鼎盛时期,我对他们的作品颇感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者的角度,审视人类生命的不同阶段。在中国,我读孔子;在印度,我读佛教和印度教的着作;在孟买,我在帕西人中研究拜火教。我的旅程给我带来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曾经混沌的一切,现在却井然有序。我的头脑得到了休息,我最终得出一个真理。基督的话“天国就在你心中”对我来说有了新的含义。并非未来,也不是过去,只有此时此刻,才是我们心中的天堂。我们的职责在于此刻的这个世界,尝试脱离现实的举动是不切实际的,注定不会成功。
那些伴我成长的宗教理论,史威登堡教派留给我的所有印象,现在都不再对我产生影响,或者左右我的思维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完全说清宗教的真相,但又都能揭示宗教的一部分真相。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伟大的导师,佛陀是一个,孔子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导师在伦理学上的教义都极为相似。
用我的朋友马修·阿诺德的话来说:
孩子们啊,上帝那神力的眼睛,永远审视着人类,轻蔑地看着没有宗教的地方,他不会轻视一个人,有谁没鼓励过意志柔弱的人,告诉他有着无穷的力量?
有谁不渴望有雨水滋润干渴的心田?
有谁不因失意而哭泣?
但是你必须重生。
这时埃德文·阿诺德的《亚洲之光》刚好出版了,这本书带给我的快乐是其他诗集无法比拟的。那时我刚刚去过印度,这本书让我重温那里的一切。
我对该书的欣赏传到了作者耳朵里,后来我和他在伦敦结识,他把诗集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这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之一。一个人如果有机会环游世界,即使要作些牺牲,也一定要争取这样做。与环游世界相比,所有其他旅行都是不完整的,只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局部的、模糊的印象。当你的环球旅行结束时,在归来的途中,你会觉得你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只是大概的),这些东西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你会发现无论在哪,人类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最终都走向一个特定的结局。
环游世界的旅行者要是仔细研究过东方各种宗教的话,会有很大的收获。他们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为能出生在自己的国家而高兴,同情那些异乡人,觉得他们不够幸运。他们会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
在我的《环球之旅》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点。
当我们拜访新加坡附近森林里的工人时,我们看到他们忙碌的场景,孩子们光着身子跑来跑去,父母们穿着松松垮垮的破衣服。我们一行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们让导游告诉他们,我们来自另外的一个国家,那里这个季节池塘的水会结冰(我们面前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直接从冰上走过,有时候冰结得非常的厚,马,甚至马车都可以从宽阔的河面上经过。他们很惊讶,问我们为什么不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看起来,他们真的十分快乐。
还有个例子:在去北极圈的路上,我们去了一个拉普兰人的驯鹿营。一个水手充当我们的向导,我跟着他一起回家,当我们经过一个峡湾时,我们看见对面海岸有几所二层的小屋在建设中。我们问,这座新房子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特罗姆瑟人盖的,他在外面赚了大钱,现在回来安度晚年。
他十分富裕。”
“你说你环游过整个世界,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等很多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想在哪里养老呢?”
他的眼睛亮了,他回答说:“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虽然这里地处北极圈,一年有6个月的漫漫长夜,然而特罗姆瑟是他出生之地,是温暖甜蜜的家乡啊。
或许在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中,有不完美、不公平,甚至是残忍的地方。但是,我们为各地人们的善良和甜美而感到赞叹。不管家在哪里,对家园的那种深深的爱,无疑就是最美好的。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之中,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几乎各个种族里都存在着这种对家的深深的眷恋。这种未知的力量没有忽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