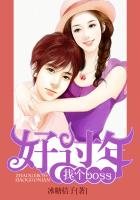“舒小姐,您,您这是要去哪儿?聂总很快就回来了!您 ”助理一阵小跑着追在了舒然身后,舒然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自己莫名其妙地在酒店里醒来,一看时间居然都是晚上了,她怎么睡得这么死?睡了一个下午了,而且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怎么来的酒店,怎么下的车,怎么会睡着,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舒小姐,舒小姐,请等一等!”助理追上舒然,被舒然手里拿着的那把伞直接给抵住胸口位置,“站住,别跟过来!”她说着,人已经走到了总台,侧脸看向服务台的前台服务员,“把电话给我!”
前台看着舒然那表情,怔得急忙把电话递给她,舒然接过电话,闭着眼睛回忆了一下曾经在尚卿文的手机里见过的几个电话号码,手指尖飞快地按下一串数字键,她突然记起了张晨初电话号码,然而电话才刚打通,座机便被一只手轻轻地按下,舒然转脸便看见穿着黑色商务男装的聂展云,他刚从外面回来,肩膀上带着一些雨珠子,白净的手指摁在座机按键上,看着舒然,不动声色地淡声说道:“不是要见他吗?我带你去!”
“伤者重伤在腿上,失血最多的地方,右手骨折,检查出有碎骨,需要动手术取出来,必须输血,血型RH阴性血,查查血库里有没有,急用!”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舒然一到医院,脸色就变得苍白起来,那晚上的那个梦再次在她脑海里重现是,那么多的血,粘得她眼睛都睁不开,一想到那个场景她就忍不住地浑身打颤。
内心深处在疯狂地喊着他的名字,卿文,卿文
舒然心里不好的预感越发的强烈,她直接推开车门就跳下了车,看着医院入口处停放着两辆救护车,救护车上的警示灯还在闪,她走过去,看到从车上退下来的空床上,染着一片的红,她的眼睛被那刺目的红灼得一阵眩晕,她剥开人群伸手抓住了一个从车里下来的医务人员,苍白的脸色一阵紧张,“谁受伤了?伤者叫什么名字?严不严重?”
那名医务人员吓了一跳,急着要挣开她的手,“一辆车被追尾,坠落下山脚,一死俩伤,正在抢救!最近因为天气缘故事故多发啊!”
舒然什么都不再说了,她已经没有勇气再听下去了,她站在原地,情绪紧张到了极点的她转身看向了聂展云,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带她来这里。
舒然脸色苍白,唇角在颤抖着,看着站在自己身后的男人,压制着内心快要崩溃的情绪,她的声音在发抖,唇角更是被咬出了血。
“带我去看他,带我去 ”
D市,张家私人停机场,从车里下来的两位骨科专家步伐奇快地登上了一架私人飞机,张晨初在临走之前安排人将所需要的医疗设备都准备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吩咐出发。
“张晨初,离约定的时间还十分钟,你怎么就提前走了?”还在路上开车狂奔往张家这边赶的司岚对着电话一阵低吼,张晨初那边声音开始还闷闷的,在司岚还要说话时,张晨初突然冒火了,大吼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老子没你那么稳得住,等不了了!”
被挂断电话的司岚一把扯掉耳朵上的蓝牙耳机,将保时捷汽车一个右靠,靠边嘎然停下,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低咒一声,MD!
司岚想了想拿起手机拨通了朗润的电话,“别往那边去了,张晨初已经过去了,很快就能把他接回来!”
“邵先生,请签字,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手术了!”手术室外,护士将笔递给了邵兆莫,空寂的等候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显得很突兀,声音虽然很小声,却凌乱不堪,碎急的,慌乱的,毫无章法的,邵兆莫此时心烦意乱,握着笔的手好不容易冷静下来正要签字,被这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打断,偌大的空间里响起一道低碎的哽咽声,强压住的低吟声,“卿文,卿文,你在哪里?卿文 ”
邵兆莫猛的抬头,转向了声源这边,便看到一个颀长的女子身影,头发乱了,穿着一件碎方格子的衬衣,外面套着的薄款长毛衣,笔直的铅笔裤下,雪白的板鞋已经弄脏了,她站在等候室的中央空地位置,目光转向了四周空旷的座椅,在飞快地找些什么,毛衣长袖遮住了手背,她抬起手捂住自己的嘴,只留下两只通红的眼睛还在朝四处慌乱地看着。
邵兆莫一时间不知道是气怒还是该庆幸,庆幸的是她终究是没事了,完好无损,但气愤的,她没事了,可是手术室里的那一个
如果不是为了找她,尚卿文不会这么着急着赶去市里,也不会出事!
邵兆莫握在手里的笔重重地‘啪’的一声落在了大理石的台桌上,扔笔的动作把等着他签字的护士都吓得愣住了,而他这一声扔笔声也引起了舒然的注意,舒然那紧绷着的弦随着这一声突兀的清脆的声音,视线飞快地转移凝聚到邵兆莫所站的位置,在看清邵兆莫的相貌时,一阵急促地扑到他面前,顾不上男女有别,伸手抓住他的胳膊,用力地晃动着,“尚卿文呢?他在哪儿?求求你告诉我 ”
邵兆莫看着面前这个情绪已经失控的女人,涨得通红的双眼始终没有流出眼泪来,但眼睛却红得可怕,他看着舒然,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去哪儿了?”
舒然被邵兆莫那冷漠的眼神看得心脏直颤,她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睡着的,她咬着唇,却控制不住自己浑身的颤抖,哽咽着像是在低低着哀求,“求求你 ”她要见他,见不到他她要疯了!
“你去哪儿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寻找,他找你快找疯了,你知道吗?”邵兆莫突然用力地甩开舒然的手,伸手一把揪着她的手腕,脸色变得严肃而冷厉,“舒然,我们一直在他庆幸着,庆幸着他终于找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可能别的好处没有多少,但是对女人,他一旦认定就会全心全意地付出,毫无保留地付出,是,你觉得你有优势,你比他年纪小,你觉得自己年龄小就应该享受着他百分之百的呵护和疼爱,你很享受这种被宠爱的感觉是不是?他是你男人,不是你父亲,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男人也是需要人疼的!在他为了找你徘徊在生死线上,你却跟你的旧爱在一起,舒然,你到底该有多博爱,还能站在这里假惺惺地哭!你有心吗?你这里还有他的位置吗?”
被邵兆莫抓着手腕动弹不得的舒然在他的一个用力下一推跌倒在地上,舒然跌下去的时候被大步走过来的聂展云蹲下身扶着肩背才没有撞倒在地板上,聂展云抬头,一张脸冷得吓人,“邵兆莫,你别太过分!”
邵兆莫冷笑一声,跟聂展云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一阵火花四溅,薄唇轻启,“聂展云,你最好祈祷他能活着出来,否则 ”
邵兆莫转身捡起扔在大理石桌台上的签字笔,沉了口气,伸手将笔直接扔给了还坐在地上舒然的面前,“签字!”
邵兆莫一直看不透舒然这个女人,刚才他的言语已经是很过激,而他也清楚地看到了她那双通红眼睛里一时间聚集而起的悲凉,疼痛,焦虑和不安还有混合着恐惧,当他将她推倒在地上的时候,以为她会崩溃到嚎啕大哭,他的言语伤人足以让一个女人情绪崩溃,但她却像傻了一样,被推倒在地,尽管脸色苍白,尽管眼睛涨得比刚才还要红,可是那眼泪始终没有流出来。
她捡起地上的那支笔,挣开聂展云的手,飞快地爬起来,趴在大理石的台桌上在那份自愿书上飞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只不过她签字的手有些控制不住地颤抖,她的右手手腕被邵兆莫刚才那用力地一拧已经疼得快失去知觉了,最后还是她咬着牙关用左手摁住右手的手腕,将最后一笔重重地添了上去。
“麻烦你了!”舒然将笔捏在手里,却对着那名护士说了声‘谢谢’,那护士看着她,心里忍不住地惊讶,好淡定啊!
聂展云看着舒然签完字那苍白的脸色,伸手去拉她想让她坐着休息一下,舒然却避开他的手,一个人转身在最边的那个角落坐了下来,手术室的等候大厅不小,两边都有座位,其中一边没有开灯,对于有夜盲症在灯光昏暗的地方看不清楚的舒然,此时却选了那个最阴暗的角落,她安静地出奇,不哭也不闹,只是坐下去时,双脚弯曲着,弓起来,伸出手把自己的腿膝盖紧紧地抱在怀里。
她坐在那个角落,周边都是空荡荡的,她抱着膝盖缩成一团,像只受了伤了的小兽,其实有些真正会痛的人是不会哭的,他们会把自己藏在一个角落里,害怕身边的人,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安静的空间里才会是最安全的,聂展云好似看到了十三岁之前的舒然,受伤的时候会躲起来,明明在黑暗中就看不见,即便是磕磕碰碰也要躲在黑暗中。
但她却绝对不会说一句,我害怕!
我害怕,我害怕
紧抱着双膝的舒然身体在颤抖着,眼睛紧紧地看着手术室门上的那盏灯,邵兆莫说他找自己找了快五个多小时,还说如果不是为了找她也不会出事!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邵兆莫刚才说那些话她句句都记在心里,是,她任性,她一味享受着他给予的宠爱,却没有回报给他相等的爱。
如果她不瞒着他来贵州,是不是他就不会出事了?
舒然插进乱发里的十指扣住了自己的脑门,用力地抓扯着,试图用这种痛来缓解身体里那锥心的悔意。
张晨初带着人赶来时就看到这么诡异的场景,手术室外除了邵兆莫和他的助理,还有一个聂展云,而最角落里的那个人,是舒然!
“手术还有多久?”张晨初走到邵兆莫面前询问,邵兆莫摇头,表示不清楚,张晨初朝舒然那边看了一眼,坐下来时抽出一支烟点燃,见聂展云起身去接电话,他又朝舒然那边看了看,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呼出一口气时,淡淡地说着:“有句话说得对,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