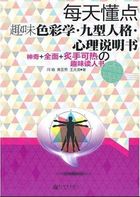吃过饭,本想帮娘收拾碗筷。她却宠溺的拦住我,把我按在凳子上,自己收拾起来。我闲来无事,趴在桌子上看着娘忙碌的身影。在自己家里就是好,不用为了别人的事而每天忙碌,也不用听到闲言碎语耳根清净,更看不到他,或许,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了。
不禁苦笑一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眼皮越来越重,我趴在桌子上准备会见周公。“婉儿,要睡去床上睡。”娘忙完了,见我眼皮打架,上来轻推我。
我极不情愿站起身挪动着脚步,缓缓向床“爬”去,说是爬,其实我的身子已经大半前倾了,及其渴望能有个依靠之处。要不是娘一直扶着我,我怕我直接就会趴到地上去。
“我回来了。”一个又尖又细的嗓音从屋外传来。我没有在意,继续往床前进。可娘的身子明显抖了抖。娘子,想我了没?”声音越来越近,此刻已经到了门口。
那声娘子一下把我的睡意消除了一半。向门口看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自然的坐在凳子上,两眼放光。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的眼睛就想起了一种动物,老鼠。
我正准备问他是谁,娘先一步走上前,肩膀剧烈的颤抖,手一扬,指着门口:“你回来做什么,你给我出去。”话中带着冷漠,伤心和气愤。
“娘子,别发火嘛,为夫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不出门迎接倒罢了,现在还赶为夫出去。哼哼,真是没有规矩。”那男人显然没有理会娘的愤怒,走到灶前看了看,自己给自己添了一碗小米粥,又旁若无人的坐回来狼吞虎咽的喝起来。
娘子,那男人叫娘作“娘子”。不用再猜了。这个人肯定是我那好赌成性,十恶不赦,杀千刀的爹。我冷眼看着他,心里已经把他给诅咒了十来遍。
他似感觉到了一簇冷飕飕的目光射来,抬起头,嘴边还挂着饭粒,看着就恶心。“婉儿啊,看着爹干嘛,想爹了不是?”他见是我在看他,随即咧开大嘴呵呵笑了,只是他笑的太假,有股市井流氓之气。常常在赌坊出没的人,有几个不是一身骚的。
我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他那句爹真的让我浑身不舒服,厌恶的的撇开眼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娘已经迅速回身,挡在了我面前,一脸的防备。“你走吧,你还害得我们娘俩儿不够惨吗?”语气也不似先前那么激动,平静了许多。
那个男人,哦,不,那个爹轻佻一笑,随即戏谑的瞟瞟我和娘,开口说道:“要我走也可以,昨儿手气不好,输了银子,你们今儿要能给我个十两八两的,让我转转运,我立马离开。”
“什么,你又去赌钱了。十两八两?我们这个家哪样东西值十两八两。”显然,娘已经情绪失控,分贝也提高了,大声的训斥着爹,嗓子都几乎破音。
“呵呵,上次我欠的十两银子是你们娘俩儿还的吧?既然上次都能一次拿出十两这么多,这次也一定能。再说了,这个屋子里的东西确实不值十两,但是。”说着,戏谑的看着我,手摸下巴,一脸的算计。
敢情还真是只老鼠啊,一只养在米缸里的老鼠。他还是不是人啊,为了赌,居然打亲身女儿的主意。
娘听爹这么一说,顿时胸口起伏得更加厉害,一副伤心欲绝的摸样,语气几乎哀求和绝望:“你这个杀千刀的,你怎么能打婉儿的主意啊!你还是不是人啊?”说完,嚎嚎大哭起来。我看不得娘这种哭法,急忙护住她。她已泣不成声,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
“哼,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迟早都是别人家的。养了十几年的赔钱货,难道不该给我点好处吗?”说完,他也是一脸的义愤填膺,自以为说的句句在理。
我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你走,你不配做我爹,你最好马上消失。”我也没办法再忍下去了。
“要我走可以,钱拿出来,我立马就走。”他手往桌子上一摊,一脸的无耻。
“好,明天来拿钱,十两是吧。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拿了钱之后就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我一刻也不想看到这个混蛋,只盼他立马消失。
只见他眼珠来回转着,像在盘算着什么。然后抬头又是无耻的笑;“好,婉儿既然能再孝敬爹十两银子。爹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找你们娘俩儿要钱了。”
“那你还不赶快滚。”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无赖一口一个爹的。真是嫌恶,再也不想跟他纠缠下去。他见我对他大呼小叫,脸色也变得铁青。正欲要上前,又想到什么,顾及了一下。二话不说,出了屋子。只是院子里还回荡着他的声音:“明天我来拿钱!”
一会儿,听着院子门吱嘎关上的声音,我知道那瘟神是真的走了。像被抽离了最后一丝力气,软软的摊在了床上。好似打了一场仗,疲惫不堪,真想立马合上眼去。耳边又传来娘的哭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