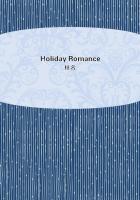2。白日
白天,我不去李大哥的茶店了,也不想上街转,从前星期天王斌会来叫我去出转,但现在我又不想去了,受不了那些嗡嗡声,到处是人,到处是喧哗嘈杂,我只能远远地躲开。
放假了,家里,不是妈妈在,就是继父在,他们约定好守护我,可是与他们任何一个人在也不觉得特殊的温暖,大慨是习惯了被看护,没感觉了。
这些日子,我不再与他们任何一个争辩,争辩没有任何用,我知道他们都让着我,让我占上风,可是原则性的事还是他们的老主意硬。比如,前些天,BJ那位医生,打电话叫我去他们的医院再检查一下,他在电话里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我回答说,按时吃药,好多了。他说,那就更应该去,介绍一下好转的过程。我说,有事,不去了。他又说,按上次拿走的药量应该用完了。那意思,是想让我去买药。我说,我丈夫这些天不在BJ,麻烦你给寄过来,钱先垫上,之后我给汇过去。医生说,这恐怕不行,他很忙,没有时间寄。我忘了爸爸在旁边听着电话,他亲自跑了趟BJ,坐了两夜火车把药拿回来了。其实,上次的药,还剩一些。人老了特别相信药的作用。
可是我总觉得我的身体不需要药片,而我的精神需要,所以我找到了李大哥,而后来我喜欢跟李保平聊天,就是因为他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是挺阳光的,而我恰恰缺失的就是这种精神头儿。
这会儿,我侧身躺在我的大软床上,像个乱世中的城堡,在我心中,它并不安全,冀国栋回来,他和我在一起,平日里是妈妈和我在一起。医生说我不能单独睡觉,他们都很听话,其实,许多时候我很讨厌这样。但人家也是为我好,能说什么呢?
现在我不想起床,为什么要起来呢?我用不着再像许多人一样,匆匆忙忙去上班,挣钱。我习惯于靠在床榻上写字,用那个结婚时冀国栋给我买的笔记本,过去写的一切没地方寄,现在有了李大哥,听说他忙着写小说,一般不和我聊天,我这些自言自语般的叙述,无非是我内心对外面世界强烈冲突后的产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吸。病发时,我好几次差点断气,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比我想像中的要差得多,完全扭曲了,变形了,而我心中所有的美好都是幻影。
即使我是个研究哲学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人一旦人格解体,随时都有可能疯掉,记得当年,我犯病的时候邻居们就说我疯了。疯就疯吧,我不在乎,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都在游戏人生,享乐至上,疯掉的我不也在享受吗?
那些日子,我感到无边的空洞和贫乏正一天天重复着从我的脚底下升起,一直升到我的头脑中。日子像一杯淡而无味的水,让我无法振作起来,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什么,我总是想到人生就是一场悲绝的相遇。
也许,我还需要一个人爱,并不是一个丈夫,我知道,单纯的***是多么的乏味,那简直是一种酷罚。而我的丈夫并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人,他只是看上我的样子,后来,我听到他们家人的言论,说早知道我是个病人就不找了。早知道,我也想早知道啊,可惜晚了。你们明白的太晚了,而最先明白的是妈妈和继父,但他们都想让我嫁人,他们说嫁了人这个病就好了,而我也半信半疑。其实我另有想法,我觉得我嫁了人,死后就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