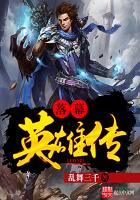她看上去听得很专心。我觉得,她那孩子般的明眸又湿润了。“您应该认识他啊,”她喊道,“您认识了他,就会更爱那些被称做小人物的人!在我还不满三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我只有他唯一一个亲人,可在我八岁上,我突然又失去了他。”我们走着,谁都不再吭声。我们抬起手来,把伸到路中间的枞树枝拨开。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像是想讲什么,可好半天才迟疑着说了出来:“我现在想给您,我的乡亲,再讲一个情况。说来奇怪,但它的确又经常发生。我总觉得,从前,当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父亲——我怕他,躲着他,他老是对我很凶,还打我和我的母亲……这是不可能的啊!我自己请人去查过教堂里的婚配登记簿,我母亲只有一个丈夫。我们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挨冻受饿,可却从来不缺少爱。还记得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在一个礼拜天,我那时大概六岁。我们勉强把午饭对付过去了。可晚上呢,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实在饿得慌,而炉子差不多已凉了。这时,父亲用他那双好看的黑眼睛望着我,我便向他伸出小手。转瞬间,我就给裹在一块破旧的毯子里,抱在这个壮实的汉子胸口上了。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道,走啊,走啊。头顶上,星星全都亮了。我的眼睛一会儿瞅着这颗,一会儿瞅着那颗。‘在那上边,住着谁呢?’我终于问,父亲回答:‘仁慈的上帝住在那儿,他不会忘记咱们的!’我又望着那些星星,它们都静悄悄地、慈爱地在俯瞰着我哩。‘爸爸,’我说,‘再求求上帝吧,求他再给咱们一小块面包,今天晚上已经没有啦!’这时,我感到一颗滚烫的泪珠掉在我脸上。我想,这是仁慈的上帝他哭了吧。——我记得,我后来躺在小床上,肚子仍然饿着,但却安安稳稳地睡熟了。”
她沉默下来,我们在林间的小路上慢慢地走着。“我母亲还在世时,”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父亲的情况就记不那么准了。
对那时的他,我只有一个凶暴可怕的印象,我再怎么想,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突然,她蹲下身子,摘了一把那种喜欢长在贫瘠水地上的淡红色千日红,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她就开始用千日红编起花环来。我仍然想着她最后的几句话,脑子里慢慢出现一个狂暴的小伙子的影子。他,我是太熟悉了,可又叫不出他的名字。“就连孩子们,”我终于提起话头,眼睛盯着她灵巧的双手,“他们有时也会想到那不可见的四处游荡的死神,感受着恐怖的袭击,因而胆怯地伸出手去,紧紧抱住自己心爱的人不放。再说——您一定清楚地知道,社会给孩子们的都是些怎样的父亲。——也就难怪您的想象力,要给自己记忆里的空白填补上这个可怕的印象了!”
高贵的妇人却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您的道理讲得很好,”她说,“只不过,我倒从未吃过这类胡思乱想的苦头。而且,在父亲死后收养我的这些人,是一个孩子所能指望的最好的人了,他们就是我丈夫的父母。他们当时在去温泉的途中,在我们城里停了几天。”
这当儿,我仿佛听见身后的泥沙路上传来了脚步声,便转过头去,发现林务官已经走近。
“您瞧,”他对我叫道,“我不是又把您找着啦!可你,克里斯蒂娜,”他抓住妻子的手,歪着头,盯住她的眼睛,“你看来心事重重,你这是怎么啦?”
她微笑着,把头靠在丈夫肩上:“弗朗茨·阿道夫,我们刚才谈起了我们的故乡——你可知道,他是我的乡亲啊——只是我们都想不起当时对方的情况来了。”“我们今天请他来做客,这不就更好了吗?”他应道,同时握住我的手,“至于当年的事儿,那可老早就已经过去了啊!”妇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挽住他的胳膊。我们又走了几百米,来到林间的一座池塘边上。我从未见过黄色的鸢尾花开得像眼前的这般茂盛。“瞧,你最心爱的花儿!”林务官嚷起来。“只是你会把鞋弄脏的,让我们男人去为你采一束来好吗?”“今儿个不劳驾两位骑士,”她回答,姿态优雅地向我们鞠了一躬,“今儿个我去过姑娘们那儿,知道这里有个地方可以采到好花,把我的花环扎得更完美!”“那我们在这儿等着你。”林务官对已经跑去的妻子喊道,同时以深沉的、充满爱怜的目光护送着她,直到她消失在不远的林中。紧接着,他突然向我转过脸来。“如果我请您不要再对我妻子提她父亲的话,您可别生气呀。”他说,“在你们身后柔软的泥沙路上,我走了已有好一阵。夏日的微风,给我送来了你们不少的谈话片断,剩下的部分我一猜也就猜出来了。要是我早知道你俩是这么近的乡亲——恕我直言,——我就会放弃邀请您来做客的乐趣了。真正的乐趣啊,我说,不过眼下这样更好,咱们相互更了解啦。”
“可是,”我有点莫名其妙地应道,“我向您保证,我对一个叫约翰·汉森的工人,真是一点儿影子也想不起来。”
“可您没准儿会突然想起他来呀!”
“我想不会。不过,您尽管放心,我一定保持缄默,虽然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缘由嘛,”他回答,“我愿用一句话告诉您:我妻子的父亲,他诚然叫约翰·汉森,可人家都只管叫约翰·幸福城,即用他年轻时蹲过监狱的那个地方的名字来称呼他。我妻子既不知道这个绰号,也不了解产生这个绰号的那段往事。而我呢——我想您会有同样的想法——也不愿意她什么时候再知道这个。因为要是那样,她孩子般地崇敬着的父亲,就和经常出现在她幻觉中的那个可怕形象吻合起来了。而且遗憾的是,这又并非纯属幻想呀。”
我不由自主地握住他的手。接着,我们便往回走去。我呢,已沉浸在一幕又一幕地涌现在脑海中的往事里。当我再抬起头来时,妇人早已走在我的身边,手里正编着花环。“请原谅,”我说,“我常常犯这样的毛病,往往由于突然想起什么,便忘了眼前的一切。小时候在家里,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哥哥便要提起那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来,说道:‘别碰他,他那只老鼠又从嘴里跳出来啦!’可我向您保证,以后一定把老鼠管得更牢。”
林务官向我投来谅解的目光。“我们这儿也有同样的迷信,”他说,“不过没关系,您现在是与朋友在一块儿,虽说是新交。”
我们又谈开了。当我们慢慢走近林务官的邸宅时,巨人般高大的橡树已经给路上投下浓黑的阴影,空中也充满了闷热的夜气,一群猎犬跑来迎接我们,不吠也不叫。从池塘背后暮霭升腾的草地里,不时传来鹌鹑咕咕的啼叫。到处是一派和平宁静的田园景象。
妇人先走进屋去,我与林务官便在大门前台阶旁的石凳上坐下。他的手下人一个接一个走来,或向他报告当天的事务,或接受第二天的指示。猎犬在人中间钻来钻去,也有猎獾犬与猎鹧鸪犬,领头的是一条嗅觉特灵的赤褐色良种狗。林务官没有工夫与我谈下去。接着,我那乡亲出现在敞开着的大门边,邀我们去进晚餐。我们在一间舒适的房间里坐下来,喝着一瓶上好的陈年哈尔特酒,林务官便扯起他那条褐色爱犬的历史来:它从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手中买过来时,还是条小狗,可对付起此地异常凶猛的野兽来却表现得很出色。接着,又讲开了狩猎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可是有一次,在谈话的间歇里,克里斯蒂娜像从长时间的沉思中清醒过来似的说:“那所小茅屋没准儿还在吧,在那条大路的尽头,门上有一个树节疤眼儿。每天傍晚,我都凑着它往外瞧,看父亲下班回来了没有。——我多么渴望再去那儿看看呀!”
她瞪着我,可我只能回答:“您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变啦!”林务官却抓起她的手来,轻轻地摇动着。
“醒醒吧,克里斯特尔!”他呼唤道,“你想去那儿干什么哟?咱们的客人自己不是也离开了吗?留在这里吧,这里是你的家——再过八天,你儿子就回家过暑假来啦!”
她仰起脸来望着丈夫,眼里流露出幸福的神情。“我只是说说罢了,弗朗茨·阿道夫!”她柔声道。
过道里的壁钟敲了十响,我们站起身来。林务官点着一支蜡烛,同下午一样送我到了后楼上的客房中。
“喏,”他把蜡烛放到桌上,说,“咱俩现在想法一致了,对吧?您理解我了吗?”
我点点头。“理解了。我这会儿无疑已经知道,这个约翰·汉森是谁。”“是啊,是啊,”他高声道,“从大路边上的尘土里,我亲爱的父母替我捡回了这个小姑娘。如今,每天清晨,我醒来瞅见她那宁静的脸庞儿,看着她酣睡在自己身边,或者从枕上向我点头问安的时候,我就打心眼儿里感激他们。好啦——晚安!让往昔的一切,也安息了吧。”
我们握了握手,接着便听见他穿过走廊下楼去了。可是,在我的脑子里,往昔却不肯安息。我走到敞开的窗前,眺望着池塘,以及那躺在黑色的平湖上如月光一般皎洁雪白的朵朵睡莲。池塘边上的菩提树已经开花,夜风送来缕缕清香。从林中传来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的啼鸣,一会儿一声,一会儿一声。然而,这生机勃发的夏夜,没有能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在我眼前,却轮流地,反反复复地,出现两个荒凉的所在:一是在我故乡城郊的旷野里,在从前建过一间硝皮房那儿,有一口井栏已经腐朽的废井,儿时我一个人捉蝴蝶时去过那里,曾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住了;二是与此交替的另一个地方,是出城向北去的大路尽头那所小茅屋,草盖的房顶,上边总长着大丛大丛的艾蒿,那么低矮,一伸手就可摸着,小屋整个摇摇欲坠,而且小得仅能容下一间卧室与一个小小的厨房罢了。小时候去郊游回来,我总爱默默地站在茅屋前,心里幻想着,如果能独自住在这小人国的房子里,既无父母,也没有老师,那该多美呀!稍后,我已是中学生,那里又多了一层情况:从那所小小的屋子里,常传出来吵闹声,使过往的行人都停了下来,有好多次我也站在人群中间。一个男人洪亮的嗓门儿在诅咒着、谩骂着,同时可以听见沉重的殴打声,以及摔碎坛坛罐罐的声音,其间还隐约可闻一个女人轻轻的啜泣声,但从来不曾听见她呼救。后来,一天黄昏,我看见一个粗鲁的小伙子一脚踢开了门,冲出房来,涨红着脸,黑色的鬈发披散在额头上。他把自己长着个大鹰鼻的脑袋往后一扬,闷声不响地扫视着周围站着的人。他的目光射到了我身上,使我觉得他似乎在冲着我喊:“给我滚开,你这穿得漂漂亮亮的少爷!我是揍了自己的老婆,与你有什么相干!”
这就是约翰·幸福城,我尊贵的女主人的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叫约翰·汉森。
约翰·汉森出生在邻近的一个村庄里。在服兵役期间,他是个好样的士兵,只不过在入伍之初,如果不是一位同伴有力的胳膊拦住了他,他差点儿拿刺刀戳翻了那个喊他“德国狗”的丹麦连长。服役期满,他回到故乡,浑身牛劲儿却无处使,连当个帮工的活儿也不是马上找得到。于是只好进城去,暂且寄食在一家地窖酒店的老板那里。酒店中进进出出的有各种各样的外乡人,一批被雇来修建水闸的工友也住在这儿。
他们中有个因为好酒贪杯而遭到开除的人,但是仍然留在店里继续大吃大喝,要把剩下的几个钱花完了事。他与约翰都闲得无聊,因此常常搅在一块儿,要么躺在城外的海堤上,要么蹲在晦暗的地窖里。这个外来汉给约翰讲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流氓和罪犯故事。这类事儿他知道得真不少,而且多半都是他亲身参加过的,只是由他讲出来,结局都很愉快罢了。一次,他俩又躺在城外堤坝上的草丛中闲扯,周围只听见西风的呼啸与海鸥的鸣叫。这当儿,小伙子突然心血来潮,决定也亲自去冒冒险。他伸出筋肉强健的胳膊,晃了晃拳头,眼睛里几乎喷出火来。“见他的鬼!”他嚷道,“既然没有正经活儿做,就干干这个呗!”
躺在一旁的那位老手,刚才讲故事时只是盯着天空中飘动的浮云,这会儿却从侧面觑了觑约翰。“真的吗?”他神秘地说,“——喏,那可是挺好玩儿的哩!”
约翰没有回答,一队工人打堤上走过来了。流浪汉站起身说:“走,约翰,这伙子人认识咱们,跟着一块儿回去吧!”
第二天后晌,约翰想找份工作的希望又落了空,两人于是再去躺在昨天那个地方。流浪汉不吭声,约翰从地里连根拔出草来,摔出去打那些从近旁飞过的燕子。
“瞧你闲得无聊,竟破坏起堤坝来啦!”那人取笑他。约翰咒骂了一声。“你昨天不是要给咱讲什么吗,文策尔?”他问。文策尔心不在焉地望着海上一面缓缓移动的白帆。“我?”文策尔道,“我有什么要对你讲来着?”“你自己明白。那可是挺好玩的哩!你自己说过。”
“真的吗?就算是吧!我当然记得,不过,那可是危险多于好玩儿呢!”约翰纵声大笑起来。“笑什么笑!”文策尔道,“这可是掉脑袋的勾当啊!”“我只是想,肯定很有意思!”对方跳起来问:“你不在乎自己的脑袋吗?”
“不在乎,文策尔,而且咱觉着,咱这脑袋长得挺牢靠。你就说说,怎么干合算吧!”
他俩凑得更拢,谈话变成了咬耳朵,而且不时地还去一个人到堤坝顶上望望风,只是连人影儿也不见一个罢了。夜幕降临,两人摸黑回去,走进地窖。一张张桌旁还坐着喝得醉醺醺的吵吵嚷嚷的人们。
三天后,一桩闻所未闻的抢劫大案轰动全城,所有的警察都出动了,而且忙得不可开交。出事地点是凸出在大市场边上的那所宅子,里面住着前参议员万茨伯格和一个老仆人。人们发现他的时候,这位瘦弱的老人被捆绑着,堵住了嘴,丢在床边。自此好几个礼拜,就再也不见老先生准时到外面来散步了,害得街上的一帮小孩子再也闹不准时辰,上学不是到得太早,就是去得太晚。过后,老先生终于又出来了,只是胳膊肘底下少了一把绸伞,火红的假发上戴着的那顶高高耸起的毡帽更显得颤巍巍的。老尼柯劳斯可更惨,他被一棒打昏过去,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没有让灵魂和肉体分家。
就这件事,使好样儿的士兵约翰蹲了六年大牢,并且得了约翰·幸福城这么个雅号。怪就怪在判决一下来,城里有些有声望的人竟对被告表示同情。他们特别强调的是:约翰把劫获前参议员的一只金表,在作案的次日就送给了乡下一个准备行坚信礼的表弟。自然,这件礼物随后便成了逮他的物证。“可惜这小伙子,”有人说,“可惜他成了个坏人!瞧他这般行事,不是满有资格当一位将军吗!”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啊,他就像那种侠盗,作案主要是为了练本事,钱倒在其次哟!”
好也罢,歹也罢,约翰可还是得去坐牢,而不久以后就让人们给暂时忘掉了。
六年的牢狱生活终于过去。约翰必须蹲满六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德国既无新王加冕,也没太子降生。他释放出来后,同服兵役时一样拿着品行良好证书又回到城里来找工作,可是谁又肯雇一个坐过牢的人呢?加之他那对黑色的眸子现在射出凶光,有一股子叫人害怕的桀骜不驯的劲头儿。“这小子看上去很危险,”有人说,“咱可不愿意在夜里单独碰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