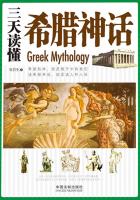谭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不管是哪个班的学生,只要在他面前打闹嬉戏,他都会叫住批评一番,给讲好多学习的道理。因此,差不多全校的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班的都怕他。记得班里一名女生,上课做小动作被谭老师发现了,他走下讲台让这名同学站起来,给她说:“你的父母背朝青天面向土,辛辛苦苦在那儿干活,汗珠摔成八瓣,让你坐在舒适的教室里,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风吹不着地读书,你还在这儿玩,你是对得起父母还是对得起老师?”“在家父母管你,到了学校我就是你的父母,就要管你。”在读课文《我爱韶山的红杜鹃》时,一个同学把“红彤彤”读成了“红丹丹”,谭老师便让这名同学把这个词正确的读法读了十遍。这也使我们自此形成了不认识的字不把握的字绝不胡读,养成必须查字典的习惯。至今我的电脑前一直都放着一本《新华字典》。而对于学习好的学生,谭老师一直是关爱有加的。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书籍还很匮乏。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满满的两大架书既是他的宝贝,也是同学们的渴望。凡是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就能有到他办公室翻阅《辞海》等工具书查阅资料的资格,有的还能顺便借上一两本书业余去读。但读他借的书,一要做笔记,二要保护好书,三不能转借。这是谭老师要求的。
在班里我的学习算是比较好的,谭老师对我的关心是另外的方式。由于家里穷,买作业本都成了问题,实在没办法就把用过的本子反过来当作业本继续使用。为了区别,用过的数学本当语文作业本,化学本当物理作业本。谭老师知道这些情况后,每学期都要给我准备几个本子,并告诉我没有了给他吭声。平时时常还拿点白纸给我,我则把它们订成本子,正面当家庭作业本,反面当成草稿演算纸用。高中三年,谭老师给了我多少本子多少纸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份感激的情怀却是终生也不会忘却的了……
冬天的夜晚是漫长的,谭老师要求我们班同学必须在六点二十以前到校,那时候的天还是完全黑的。到了快要高考的一学期,有些同学还不到六点就到校了。谭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就在我们教室隔壁。每天不管多早,只要有一个学生到了学校他必定起床看看,然后在办公室看书。在我的记忆中,每天到校不管多早,他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着的。看到了灯光就感觉到了温馨、注目和责任。
我们是乡村中学,且每个乡只有一所。全乡几十个村的人都在那儿上高中。许多同学住得都很远,大多都是带着中午饭的。夏天大多同学带点饼子馒头之类的,带米饭和菜不用热也能吃,但冬天则不同了。天冷,大多数同学都带的是米饭,然后在炉台上热热,中午就可以吃一顿热乎饭了。由于人多,教室两个火炉,每个炉口周围都堆了十几个饭盒,摞七八层高。下课了把饭盒转个方向,几节课下来饭盒已是热腾腾的了。有时候炉火太旺或者饭盒靠炉口太近,上课过程中就能闻到烤焦的饭味。每当那时,凡是带盒饭的同学都有点坐不住了,偷偷地焦急地观望着,是不是自己的饭烤糊了?已经没有多少心思能听进老师的讲课了。这种现象不久就被谭老师发现了。从此,他要求所有带饭的同学到校后把饭盒全部放在他的房间里,由他负责在不上课时把大家的饭盒预热。从此大家既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饭,又不再操心热饭或烤煳的问题了。记得有一次中午放学了,有的同学回家了,有的也开始在桌上吃饭了,而我由于正专心地在解一道题,忘了去拿饭。大约一刻钟后,谭老师把饭盒端到了我面前说快吃吧,吃完再写。”转身的当儿又回过头来微笑着说:“你们家是不是没油了,看你吃的菜里一点油都没有,我给你加了点,快趁热吃吧。”说完轻轻地转身走了。那时的我,已是心潮澎湃,满心温暖的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忍不住掉进饭盒里。那盒饭,就着眼泪,就着谭老师加的香油,我吃得是最香的……
谭老师是教语文的,多读多背多写是他对语文学习的一贯要求。从高二开始,谭老师要求我们全班每个同学必须每年要背会80篇文章,其中30篇古文,50篇现代文。为此事多少同学愁得连觉也睡不好,每个同学都硬着头皮去背了,我的背诵时间主要在上学来去的路上。十多里路单趟行程需要近一个半小时,便成了我极好的背文章时间。哪位同学背会了一篇文章,就在自习时间或放学后拿上书到谭老师办公室,老师拿着书,同学站在那儿背。顺利地背下来了,谭老师就会在本子上专门的一页学生的名下,记上已经背过的文章名称。若背得不顺利或有错误,则回去继续背,背熟了再去。不知不觉一年下来,我真的背会了很多文章,《荷塘月色》《松树的风格》《白杨礼赞》《我爱韶山的红杜鹃》《春天来了》《海燕》《母亲》《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长篇游记《天山景物记》等等,都会流利地背下来,到现在也还能背上几句。古文包括《师说》《劝学篇》《商鞅变法》《促织》《琵琶行》《梦游天姥吟留别》《岳阳楼记》等等都背过。当时,背诵那些文章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不曾想这些大量的阅读和背诵习惯也为后来的喜欢阅读喜欢文学打下了基础。之后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工科,但喜欢文学作品,喜欢阅读和思考,喜欢做笔记和写点感受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庆幸过去谭老师的要求和背诵。走上工作岗位后直到今天,不管是自己的报告还是单位的材料都是自己写的,也包括网络里的浏览和偶尔的随思与涂鸦。一个老师带点强迫的举动,影响了多少人的一生啊!我们班当时有60人,包括后期重读的,先后共有54人考上了大学、中专,这在当地堪称奇迹。现在,在银川工作的十几个高中同学中大部分都是单位的“一支笔”,并因此铺就了自己的仕途之路。
大学毕业后我到银川工作,从此别离了家乡和过去读书的地方,渐渐地也与老师和许多同学减少了联系。后来听说老师被平反了,本来可以回上海的,但他选择了继续留在中卫工作。再后来,听说谭老师不教学了,当上了中卫县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组织领导地方志编纂、文史资料整理也是他工作的主要部分之一。那几年回家碰见过几次,平反昭雪了,谭老师心情更好了,每次见面都是笑容满面,分别时总说:“到了县城就来找我,我就住在红太阳广场毛爷爷像后面的楼上,好找。”尽管谭老师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等等不公平的待遇,但与我一样,对毛主席的情感一直都是纯朴浓厚的。中卫红太阳广场有一尊塑像,雄伟高大,是“文化大革命”后全国保存下来的不多的毛主席塑像之一。据说正因为有了这尊塑像,才使得中卫县繁荣昌盛,发展迅速,最终升格为地级市,这是题外臆测的话。
工作久了与谭老师的联系慢慢也少了。有一天正在上班,门房通知说有人找我。出来一看是谭老师,正笑眯眯地满头是汗地站在大门口:“看到你就好了,还怕你不在。”我激动中带着惊奇:“没想到是您来了。”请到家里,坐下喝了口水,谭老师才说到银川开政协会,带了两本《中卫县志》,另外有一本张大千儿子张心智写的签名送给我的书,知道你一直爱读书,所以专门给你送来了。”多少年了,没想到老师不但记着我,记着我的爱好,还这么老远来送书。我那时工作的单位在银川市郊区,距离市中心较远,也没有通公交。问起老师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是边问边找走过来的,走了快两个小时了。霎时间,我的心中充塞了满满暧意,老师哟……
把老师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栽树种花的园丁,生命的启蒙者。对于我,这一切都是真的。
有师,人类在知识中进步;有师,生活在快乐中丰富;有师,社会在和谐中发展。在物质文明困乏的时刻,老师是我们生活的典范。他们以平凡创造着伟大,以认真负责担当着社会责任,以自律自强诠释着人类奋斗的本性,以关爱和慈善演绎着人间的真情。
我深深地铭记着我的谭老师。
十五穿透岁月深度
谭学荣先生于1958年4月因“反右”补课在上海被打成“右派”,以下放名义到中卫接受劳动改造后工作。在中卫整整生活了40年,这里的山水和风土人情早已融入到他的血脉之中,也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卫人,颇为第二故乡大批弟子追捧和民众爱戴。
好的家风代代相传,维系着一个家族及至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谭学荣老先生与许多在文化事业上卓有建树的人士一样,对文化事业的钟情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由于治学严谨,对学生严格,提倡学富五车,不幸在那个年代却就此毁掉了他自己的锦绣前程。
追溯家世,八世祖谭纲先祖有诗《西花园》“老树参天水绕门,幽人曾似寄琴樽。遥空一带烟云起,犹是当年笔墨痕。”谭氏西花园在镇西三里庙河南,梁启超曾往一游。原来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的着名文化人士,其耀眼的光环也正是谭学荣血脉中的根。祖父谭德钟(组云)是中国近代杰出的书法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曾与友人合作出版《十人书画册》《三谭书画集》,并在当时的上海大新公司展厅举办“三谭书画展”,引起轰动。其着述有《海香诗抄》《海陵印存》《海陵书画集》《续艺舟双楫》等。父亲谭少云,20岁时拜吴昌硕为师,攻书画篆刻,得到真传,成为吴门高足。1957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颐和园为其举办谭少云个人画展,展出作品150件。父亲一生书画作品甚丰,出版书画册有《吴昌硕谭少云书画合集》《王一亭谭少云书画合璧》《艺海书画谱》《海陵谭家书画舫》《十家书画集》等十多种。谭学荣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受祖父和父亲影响,从小就敬仰有文化的人。当时,家里摆满了祖父和父亲的书画作品。每逢传统节日,他都会得到一些书画小礼品,年幼的谭学荣非常高兴,有时也就拿起父亲的画笔涂几下。父亲见他聪敏好学,就悉心传授,精心指点,他由此开始了五彩缤纷的梦想。水乡景色,令他心旷神怡;荷塘写生,他也仿父学画。儿时梦想的生活,就是将来像祖父和父亲一样当个画家,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用笔描绘塞北江南的绮丽风光。
喜欢读书的谭学荣,从小就领略了读万卷书的家风,养成了良好的思维品质和分析能力,同时获得丰富知识。他说这种能力将使一个人终身受益。谭先生自幼胆大,随祖父书画会友,不满10岁竟敢抓大笔写大字。5岁时祖父书联赠之,此联于抗日战争时期丢失。不意竟在美国出现,其表兄购得带往台湾,又转至上海,再到南通,81岁重见,读了又读,这真是一件奇遇。他曾经读过的书可谓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明清小说,几乎无所不包。广泛的阅读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也为后来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1958年10月19日中午,一列火车将谭学荣送出上海,送到了银川。当时的银川有火车经过却没有站台,他和一批有苦难言的“右派”在没有站台的地方下了车,个个脸上都是一派茫然。眼前的银川火车站似乎没有房屋,只有帐篷,真正的建筑只有一座水塔。所谓的贸易部也就是几个帐篷小商店、小吃店。然后,一辆全程都在咯吱咯吱作响的卡车又把他送到了中卫。中卫当时的情景更是让他吃惊,不但车站没有站台,连电灯也没有。一盏煤油灯挂在一个水泥桩上,这使他想到曾在电影上看到西伯利亚。恍惚间,竟然以为自己置身于西伯利亚了。后来,一辆木轮牛车来接,说是接他们却不让坐车,只让他们把行李放在车上。那天已是深夜,因为没有灯光,到处都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他是一个习惯于思考的人,他深知,另外一种生活必将在一个没有站台的地方,又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开始了。他想,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
那是一个集体发烧的年代,谭学荣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他在中卫县柔远公社扫过大街,淘过大粪,挨斗挨批,受过很多苦,但对中卫土地的富饶,尤其是中卫民众的善良,也有一些温馨的回忆。他庆幸在艰难的人生岁月中,曾认识了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老先生虽然也受到运动冲击,但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他从先生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情操的品格和忍辱负重的精神,特别是何先生传递给他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要停止学习,学习和人生是紧密相连的,有所学才能有所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才能成为一个生理和心理都健康的人。再者,就是注重做人,无论生活露出怎样的面孔,都要坚信春天会来,阳光终将铺展在未来的路上。
谭学荣回忆过去,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真情洒落在人生道路上,让他久久沉浸于激动之中。记得在中卫县东园公社曹闸三队参加劳动改造时,乡亲们中的很多人都因饥饿全身浮肿,但家里只要做好吃一点的饭菜都要喊他去吃。有一天,一个叫王生富的农民让孩子喊他,说是让帮着算账。他进了这家院子,就让孩子把院门锁了在院门外玩,端上了仅有的一碗米饭和一点咸菜几片猪肉让他吃。“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每天接受批斗,回到住地便又冷又饿。一天晚上,有一个叫李学堂的学生提着瓦罐来敲门,瓦罐里装的是猪肉粉条和米饭,让赶紧吃,并安慰他别怕,说他没啥罪状,是那些混蛋胡整人。在他后来重新走上教师岗位后,领导也暗中保护他,说县城复杂,让他到中卫县柔远公社莫楼学校去,陶生珍校长把全校唯一的一盏煤油罩子灯给他用。结果去后第二天上午县委统战部部长马从章来看他,宣布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是啊,这就是人生处处有真情,当生活变脸的时候人生并没有满盘皆输,而关键时总有温情在转弯处透出希望的光芒来。受客观条件制约,人生的转弯不可能像画笔那么连贯,多少有点笨拙,处理不当还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他必须从岁月深处去发现真善美,去品味人间的真谛。
人的意志力在高压环境下,又会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张力。虽然谭学荣曾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磨难,但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自己的未来充满阳光。因此,无论自己处境如何险恶,他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品格,人在党外,心在党内,时刻为党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