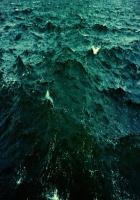是一把制式步枪。侯风连忙划开他能划得到的所有袋子,吩咐乌鸦将里面的东西都掏出来。答案出来了,在西面,是差不多一百多袋面粉,剩下的绝大部分麻袋是沙土,而东面的角落里有整整十只袋子,里面的沙土埋着二十把步枪和一把手枪。另外有十只袋子里的沙土下是黄澄澄的子弹。
就在为刚才无意间偷到狱长的手枪而洋洋得意的侯风,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由有点发愣。怎么办?自己绝对没法同时用二十把枪,可如果这些枪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他侯某人的处境就大大不妥了。他和乌鸦面面相觑,只能呆呆地看着这些枪。同时,两人的脑海里都在飞快地盘算着。
侯风从乌鸦的表情看出了他对枪的出现感到的诧异不是装出来的,这和他看到面粉口袋里的沙土时硬装出来的惊讶根本就是两回事。那么,是谁将这些枪藏在这里的?拿这些枪怎么办呢?枪都藏在这里,也难怪鹘山监狱里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佩枪,除了狱长。
想到狱长,侯风忽然笑了。他再仔细地看那些枪,枪身乌黑,但是长时间沙土的覆盖使得其本来乌黑的表面黯淡了不少,仿佛是被去了势,失去了武器与生俱来的杀气。看着看着,侯风脸上的笑容更加爽朗了。这个姓陈的!还真他妈有一套。毫无疑问,这样的事情只能是他干的。侯风问乌鸦道:“狱长是不是下令不许人拥有枪械?”
“好像有这么回事,他上任之后就没有看守持枪了。”
“为什么呢?”
“不太清楚,不过有传言说他到来之后就要求所有的枪械都由他保管。”
“那些看守们也心甘情愿?”
“其实也没有什么,看守们不佩枪出来犯人们也不敢怎样,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枪到底在哪里。何况狱长自己是佩枪的,所以就算有人想冒险也不敢轻举妄动。”
侯风一笑:“听起来,你跟看守们可熟得不得了啊。”
乌鸦知道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掩饰道:“不不,只是有些交情而已……”
“不错,有些将他们没有枪都告诉你的交情,看来交情不浅。可是为什么他们打你打得那样狠呢?做给谁看?我么?”
乌鸦的汗珠出现在他的额头,他说不出话来。侯风却嘿嘿一笑,仿佛根本没事一样:“嗯,狱长怎么会把枪藏在这个地方?他是什么意思?啊?装什么老实?你他妈说话啊?别他妈再装了,乌鸦,你的演技让我很恶心。老子知道你跟看守是一伙的,现在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把枪藏起来?你最好回答我的话,不要忘记了!”他拍了一拍腰间。
乌鸦瞄了一眼地上的枪,侯风笑吟吟地看着他。终于,乌鸦估算完距离,认为自己绝对没有把握在侯风掏出枪之前跳过去拿上枪再上好子弹干掉对方,于是开口道:“是……本来枪就放在这里。可是忽然有一天,枪全部不见了,大家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大家都以为是狱长把它们拿进自己的房间了。却想不到,想不到被狱长藏在了这里。”
侯风笑道:“这些事情必须一晚上干完,工作量够大,他的勤奋真让人佩服啊,呵呵呵呵。不过,真是奇怪了,为什么要把这些袋子排成一面墙的模样?空地方还有那么多为什么——哼!后面是什么?”
“不……知道。”
侯风用力一拉,一片麻袋垮了下来,露出一个黑糊糊的洞口。
“这个算什么玩意儿?”侯风注视着乌鸦,乌鸦颤抖着嘴唇,答不出话来。两人之间,一股杀气弥散开来。到底杀不杀乌鸦?这个洞自己也可以钻进去探察?乌鸦还有价值活着吗?在良久的沉默中,侯风颇有点拿不定主意。乌鸦的目光呆滞,充满了惶恐和绝望,脸上布满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滑落下来滴在地上,想必是知道自己命不长久吧。
“啊——”
就在这时候,外面厨房的马宣忽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侯风霍然转身,迈出了门。马宣嘶着嗓子道:“是你……快叫狱长——”
“什么狱长?谁是狱长?这里根本就没有狱长。”
“什么?”
“那个狱长是假冒的。”
乌鸦一个箭步冲上前去,飞快地抄起地上那把手枪。多年的经验让他从枪的重量知道,弹匣竟然是满的。他没有犹豫,对着侯风的后脑勺扣下了扳机。
“砰——”
鲜血从乌鸦裂开的右手飞溅而出,染红了他的半边身体。他嚎叫着滚在地上。
“你的智商真让我失望,”侯风头也不回地说,“那些枪所有的枪管和枪身的连接部分都被人不轻不重地砸过。砸的人非常小心,乍看上去并没有破坏什么,可是这些刚好堵住了子弹的枪如果开火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炸膛并顺便将拿枪人的手炸掉。本来我是想干掉你了事,但是看起来你非常英勇地验证了狱长和我对枪械的熟悉程度,也省掉了我的麻烦。可别恨我,那都是狱长干的,我可最怕别人恨我了。别人一恨我,我就只有干掉他。现在,”他不再理会在地上滚来滚去嚎叫的乌鸦,转头对抱着头惨白着脸坐在地上的马宣道,“你他妈又在鬼吼些什么?怎么每个人离我近了都要乱吼乱叫?老子的面相不够善良么?你他妈到底看见了什么?”
“鬼!有鬼——”
“你说什么?”
“鬼!鬼来了,它们来了!”
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侯风盯着门,将手放在了腰间。
“是我。”狱长的声音在外面响起。看起来,他似乎知道自己在里面,侯风想。
和侯风一样,狱长一脚踢开门,和曾通前后而入。狱长一边看着侯风手指间转动的手枪,一边道:“哦呵!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一个一身是血半死不活的人,一个被阎王遣送回来面无人色的人,还有一个洋洋得意的家伙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狱长——狱长,救命——”马宣看见狱长的到来,忽然像看见救星一样大声嚷起来。
“鬼叫什么?”侯风顺势踢了他一脚,冷笑着举起枪,闭上一只眼睛瞄准狱长:“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狱长道。
“一切都结束了。”
“你都知道了?”
“是。”
“夸”的一声,侯风打开了保险。
狱长毫不在意地走到一张桌子旁,将桌子推到门边,刚好顶住了被踢坏了的门。桌子的另一端抵着厚实的甬壁,除非将门敲碎,否则外面的人根本无法进入。
“那么,现在我想我们还有些许时间,我洗耳恭听。”
“开玩笑,”侯风笑着摆摆手,将枪塞回腰间,“我还没完全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他一指地上的马宣和乌鸦。
“谁先来?”狱长道。
乌鸦停止了呻吟,和马宣对望一眼。
“乌鸦,别他妈挺尸了,”侯风喝道,“你的伤不过是破了点皮,又不是伤筋动骨,老趴在地上想证明你的恋地情节?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别再耍花样,嗯?”
狱长道:“现在让我们回到事情最初,回到那个焦点人物身上。”他看向侯风,侯风点点头:“老舜。别再笼统地说什么这个可怕那个恐怖,说具体的。”
侯风一边听着乌鸦的叙述,一边冷冷地上下打量狱长。狱长今天的表情看起来相当怪异,白净的脸上泛着红光,仿佛是三天三夜未曾睡觉一样兴奋地急促地呼吸着,他的衣领也和他侯某人一样脏。这可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原因让狱长这样一向对自己仪表非常重视的人也忘记了换干净衬衣了?他和曾通今天到底看见了什么?侯风斜眼朝曾通望去,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表情,侯风想。曾通的脸上或多或少和马宣有点相似,但他的眼睛里却透露出好奇和探索,他正紧紧地盯着乌鸦。
乌鸦道:“五年前我们来的时候,我从号子里的其他兄弟那里听到一个秘密,一个关于老舜的秘密。最初,大家都没有在意,但是接下来,大家开始发现这里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似乎每个人都不愿意谈论这个事情,或者说每个人都在逃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逃避什么。后来有一天,我被分配到照顾那些快要死了的病人。那个病人是个傻子,不,是大家都以为他是傻子,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叫他袁痴。平时,他要不就是胡言乱语,要不就是整天地一声不吭,但是在他临死的前一天,他忽然清醒了……”
“……知道,咳咳,知道老舜么你?”袁痴躺在床上,他的每一声呼吸都带着类似金属碰撞的尖锐声音。乌鸦知道,他命不久矣。
“听人说过。”
“哦……我敢打赌,没人,没人愿意跟你说老舜究竟是什么。”
“是啊。”乌鸦惊讶这个袁痴似乎神志正常了,他将脸盆放下,走到袁痴的床边。袁痴的脸上布满污垢,这是成年累月没有洗脸的结果,乌鸦想。
“想……知道么?我,我可以告诉你,”袁痴挣扎着举起右手,“反正,反正我已经活不了几天了。在鹘山监狱,我这样剩下最后几天的人,咳咳,都会被放到外面去……外面的戈壁上去等死。”
“谁是老舜?”乌鸦问。
“我不知道。”袁痴用调侃般的眼神望着乌鸦,满脸满眼的嘲弄。
“你真是疯了。”乌鸦不耐烦地将袁痴的右手甩开。
“不,你听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老舜,是因为老舜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什么?”
“老舜不是一个人。你来鹘山监狱多久了?”
“刚来,就两月。”
“你来的这些天里,有没有发现一些怪事?”
“……”
“你有,是吧?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从脚底传来,或者一些奇怪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晃而过?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奇怪的,咳咳,和常识不符合的事情?”
“你看见过什么?”乌鸦不愿意回答,他反问道。
袁痴摇摇手:“老舜。老舜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人。咳咳,在鹘山监狱,也许从鹘山监狱开始的时候就有老舜,一直到鹘山监狱被地陷吞掉为止,都会有一个老舜,”他举起手,压住乌鸦的询问,“我也不知道老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的。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老舜是谁。操,反正不会是我。咳咳,但是,现在肯定会有一个老舜。一个老舜死了,另一个老舜接着。”
乌鸦侧坐在床边:“你是说,老舜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并不是特别指向一个单独的人,而是一个类似职务一样的代号?比方说,像狱长这个称呼?”
“对,咳咳,就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你认真地回答我,你,你相信有鬼吗?”
“……”乌鸦吞了口口水,这个问题如果要较真的话,他没法简单回答一句相信或者不相信。
袁痴看出了他的迟疑:“你回答不了,对不对?你原本是不相信的,但是进来之后,发现有些事情,没有鬼就没法解释了是不是?”
乌鸦迟疑着,最后狠狠地点了点头。
“我告诉你,咳咳,我相信有鬼的,我亲眼见过。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幻觉,我以为我是被关疯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乌鸦摇摇头,袁痴继续道:“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书上说一个人是不是疯了他自己永远都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没有疯,因为,当我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正常的,并且也认为自己是正常的,而是很焦虑地思考着,怀疑着自己是否正常。我猜想,一个疯子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疯子,而一个正常的人则会有这样的思考,你说是不是?”
乌鸦听不大懂,他问道:“你说的老舜……”
“对,老舜。”袁痴加重语气,“现在的老舜是谁,前任的老舜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老舜是怎么来的。咳咳,我知道!”
“怎么来的?”
“在鹘山监狱,总会有些人失踪,他们莫名其妙地失踪,就那样,就不见了。你知道吗?你才来,还没注意到。反正,他们就那样失踪了,也不是逃了。”
“死了?”
“对!被,人,杀了。”袁痴挣扎着想坐起来,乌鸦连忙扶着他。
“被谁杀了?”
袁痴看着乌鸦:“可能是被任何人。任何看守,任何犯人。这是,咳咳,一个曾经想要杀死我,结果反而死在我手里的人在咽气儿前说的。这个监狱,被恶鬼控制着。人们不知道它在哪里,却知道它要干什么。”
“那恶鬼就是老舜?”
“不是,老舜不是,老舜是代言人。”
“代言人?”
“对,有一个游戏,叫作找出老舜。这个游戏你玩过吧?”袁痴忽然笑了笑,乌鸦连连摇头,袁痴道:“你现在就在玩这个游戏了,哈,咳咳,不是吗?找出老舜,然后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谁是老舜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老舜是邪恶的代言人,他告诉大家的那些事情,都会实现。”
“什么事情?”
“比如说,谁会死。”
“你会死吗?”
“没人告诉我我也知道我会。我也想过,会不会我是老舜?我可以预言自己死,但是,我却不能预言你会不会死,虽然说,人人都会死,但是我却不知道你会不会死在这个号子里。所以,我知道我不是。”
“那么怎么找出老舜?”
“找出你要怎样?”
“……”
“杀了他,对不对?咳咳,”袁痴道,“很正常的想法。我还可以告诉你一条线索,老舜是不可能被人杀死的。因为,咳咳,因为……”
“保护他,那些鬼?”
“对,”袁痴点点头,“所以,找出他,也没什么用处,最多问一问,自己会不会死。但是,如果能出去的话……不,没有人能再出去,当老舜出现之后,没有人能再出去!”
“什么?”侯风皱眉问道,他对乌鸦在关键时候打住非常不满。
乌鸦正用一只手压住另一只手止血:“没了,他忽然又不说话。我一问他,他就又胡说八道起来。我觉得那算是回光返照。”
“后来呢?”狱长问。
“后来他就不行了,第二天我和另一个弟兄把他抬出去,还没走到一半就咽气了。”
“这算什么?”侯风怒道,他和狱长对望一眼。狱长摇摇头:“这倒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囚犯一个接一个地失踪。可是,如果是被人杀死的话,总会有尸体留下来。”
乌鸦道:“我揣摩他的话,最后想到,老舜就是一个杀人的游戏。杀死别人,也提防被别人杀死。最后那一个,就是老舜。这个监狱太大了,失踪的尸体总可以有不可能被发觉的地方藏起来。”
狱长点点头道:“这也是一种模式。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你相信这种鬼话,你为什么不逃出去?”他扭过头问马宣:“你相信老舜吗?你为什么不逃出去?如果你想出去,可是有大把大把的机会。”
马宣看了乌鸦一眼,正待回答,门外遥遥传来看守们蜂拥而至的嘈杂声。侯风道:“我看他暂时不需要回答这个,先让他满足我对那间房里的地道小小的好奇心。”不能让看守们看见这个乱七八糟的混乱场景,在一瞬间,侯风和狱长达成了共识。狱长点头道:“库房的地道是通向哪里?乌鸦?马宣?你们谁告诉我们,谁活下去的机会更大。”
乌鸦和马宣再次对望一眼,乌鸦道:“是通向另一侧的一条甬道。”
“有多远?”
“不好说,不到一千米吧。”
“你们想通过这个越狱出去?”
“失败了,我们以为能另开一条通道,但是监狱里有太多的甬道不为人知道,结果一路挖到另一条非常罕至的甬道上去。”
侯风道:“怎么不接着挖了?你们不是想越狱吗?”
乌鸦道:“在甬道里挖,太不安全。”
侯风了解地点点头,虽然这里离外面很远,但是如果在外侧的甬道开挖的话,很难保证不被别人发现。可是如果乌鸦的人掌控了所有在厨房工作的看守,这件事情就好办了。虽然远了很多,但是在鹘山监狱,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的就是漫长的难以打发的时间。
狱长道:“开挖的时候,有不少怪事吧?”
乌鸦无声地点点头,侯风愣了一下,马上就明白过来,失踪的囚犯就是从此而来。狱长接着忽然冷冷地笑道:“如果我提议大家现在就从这里出去,有人反对吗?”他锐利到接近凶残的目光扫过曾通。
地道非常狭窄,仅仅能容下一个人半蹲着前行。五人排成一长串,乌鸦在前面带路,侯风跟着乌鸦,马宣在侯风后面,曾通在马宣后面,狱长断后。
“这样的安排似乎不大对劲。”在安排顺序的时候,侯风忽然阴阴地反对。
狱长道:“这里的事情还有很多还没解决。在解决完那些事情之前,我们的事情暂时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