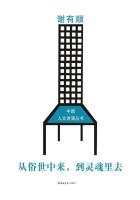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第6章
“拓凌,快回来——”哽咽而惊慌失措的语音卡在最后一个字上,刺得苍拓凌的心都纠起来了:“雪,怎么了?”他一下子由椅子上弹起来,冲着手提电话焦急地喊着,弄得在座的洽谈客户不明白发生何等大事。
“不是回来,回来了没用,你去买些……”委屈的哭腔已传来,但宣示答案的部分却被女主角越说越小声,以至无从听闻。
拉高了耳朵也没听到关键,苍拓凌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用眼神示意昊然接手他的工作,他拿着手提电话边向外走边安抚自己的心脏,命令自己镇定下来,虽然在听到冬雪急哭的声音时很难。“有歹徒胁持你吗?”
电话那头的冬雪拼命摇着脑袋,跪坐在床上,搂着电话不敢乱动,恍想起苍拓凌看不见才小声应了句:“没有。”
“家里着火了?”没有生命危险,那就好。他正在电梯内,向一楼接近,等又是一个否定传来,他已快步向停车场跑去,“那你是摔伤,磕破皮流血了,或被利器划伤了?”他能想到的情况全想到了,都不明白是什么让冬雪急得哭出来。
“嗯。”电话那头应着,还没待苍拓凌接收完毕,又是一长串“不是不是不是”连连加以否定。他不算全错,她是流血了,可不是外伤弄的。
车子已在开往公寓的路上,苍拓凌越来越糊涂,也越来越心急。刚刚秘书面有难色地拎着他的手提电话战战兢兢地踏入会议室,她怕死了被董事长轰,也担心电话那头不知明女子的急切。而他的不悦也被那句“快回来”给震没了,满心全是惊惧:“雪,别急,你慢慢说你到底怎么了?”
电话那头静窒了好久,久到苍拓凌恨不得现在就在家门口,拉开门直接找到原因,这时——
“‘它’怎么会来呢?虽然时间到了,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它’来得没道理啊,每次第一天就好多,来得又好猛,现在床上,衣服上弄得乱七八糟……”明显换了口气,“我只是小睡一会儿嘛,‘它’就跑来了,我还以为‘它’不会有的。”只有他能帮她,虽然不想说,可没有选择。
“他”?“好多”?“谁,他是谁?”家里什么时候有人的,不是歹徒破门而入,那是谁会让冬雪打开门让他进去,而且,“好猛”?她这一句话是否有点问题。“你的朋友?”
“嗯,是好朋友来了。”就算隔着电话,冬雪仍是脸红地嗫嚅着,这种事就算是通过电话讲,也让她不好意思。
“男的?”有点吃味,冬雪什么时候有好若至亲的男性朋友,或男友,前一任的?他还真有本事找到他家去。等等,等等,苍拓凌单手扶方向盘,另一只手敲自己的脑袋,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找到他家?他又怎么可能看得见冬雪,又什么时候见过冬雪?
真是要被急糊涂了!
“男的?”冬雪呆呆地重复,这玩意也分男女?“我不知道它是男是女。”不明白他的意思,她只有老实回答。
“那‘他’不是男的了。”可也不是女的,苍拓凌现在头上是一个个问号冒出。人不分男女分什么?哪有冬雪分不清男女的人,“你怎么会让他进来,又怎么会让你急哭的呢?”
“让‘它’进来?是‘它’自己要来,我怎么知道。”冬雪顺口答道,忽然脸色一变,“啊——苍拓凌你——”他居然没弄懂“好朋友”是什么意思!这么半天居然鸡同鸭讲,白忙一场。
无奈的尖叫震得苍拓凌耳朵几乎麻掉:“又怎么了?冬雪?雪?”电话那头没有声音,但隐约听见冬雪低低似压抑着痛苦的呻吟。“说话呀,你怎么了?”
“苍、拓、凌,我要你带些卫生棉回来,现在,立刻。”好痛,刚刚那突然明了苍拓凌根本没有弄懂的生气尖叫使得它来势汹涌。他害死她了。
“卫生棉?”它好像是——
冬雪已痛得双腿酸软无力,也不敢冲入卫生间,只可惜现场像凶杀案现场,惨不忍睹:“我、要、卫、生、棉。”一字一顿吐出,丝毫不敢大声换气,怕情况更惨。
居然是这个,冬雪的月事来了!苍拓凌立即哑口无言,乖乖应着:“我马上回来。”眼尖地发现一家超市,赶快冲下车,跑进去,在门口立定。抓住收银小姐,“女性用品专柜在哪儿?”
收银小姐满脸惊惧,一位买女性用品的美男子?神色匆忙似想去抢劫——呃,卫生棉或卫生护垫?“在那边。”手一指,身边男子已快步冲过去,压根没在意他俊美的形象与另类的行径在外人眼中有多不相符。
待慌慌张张的苍拓凌在柜前站定,才傻了眼。卫生棉没错,可是,日用的,夜用的,护翼的,加长的,哪种才是?身旁两位年轻小姐满脸怪异地看着这位瞪着卫生棉青筋暴跳的男人,真是好可怕!而苍拓凌早将自己的处境给忘得一干二净,一心只有冬雪的焦急,干脆每种抓起两包,急急付了款,跳上车去,留下店中目瞪口呆的人群。
赶回公寓内,直奔卫生间,却发现冬雪不在里面,“冬雪?雪?”脚步不停,一边唤着,一边冲向她的卧室。不在卫生间里呆着,在卧房干什么。不待冬雪应声,苍拓凌直接推开门去,顿时傻眼,床上片片红渍,触目惊心。冬雪蜷成一团,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上隐约见到颗颗冷汗,身子不时地抽搐着。刚刚还有劲喊着,现在怎么这样了?!“雪,雪……”赶快扶起她,急切地轻摇着,拍拍她的脸,让她清醒一些。
知道他回来了。“别摇了,啊——”下腹内又是一阵撕扯,丝丝吸着气,动都不敢动一下,待疼痛稍缓,便想在他搀扶下挣扎着到卫生间去。
搂着冬雪,紧张地憋着气看她难过的模样,心中一阵翻搅,怕她一口气喘不过来会昏过去。苍拓凌担忧地发现她脸色越来越苍白,“要去医院吗?”发觉她想起身,赶忙打横抱起她。
“没用的,每次都这样——啊,拓凌,放我下来,好脏的——”有气无力地应着话,又使劲推他。她现在这个样子好狼狈,他会怎么看她?
不管裙上是鲜红的**,不管是否粘染上手臂、衣服,苍拓凌有力地将冬雪搂到怀中,不许她挣扎。不管她抗议,抓过卫生棉,打开卫生间的门,他还想进去继续帮忙。冬雪一副体力不支随时会倒地的样子,他不放心她一个人在里面。
“出去——”苍白的脸色有了丝异样的淡红,耳朵根子是浅浅的粉色,冬雪垂着头,不愿多说。他已分享了她的部分隐私,如连这种私密事他都还要插手,那她真是没脸做人了。
明了冬雪必然会有的矜持,苍拓凌也不坚持,小心地放下她,担心地看着她扶墙虚弱地站定。罗裙点点红梅,映着雪白的娇柔容貌,竟是万分让人不舍与怜惜,明知是不可能,他仍开口,作再一次的确定,“雪——”
而她的回答是小手扯着他的手臂无力却坚决地向门外推,意思已再明显不过。
终于不再坚持,苍拓凌准备出去:“冲个热水澡,会舒服一些,我去拿套衣服就过来,然后在门外等着,有什么事立刻叫我……”同时打开了热水开关,调好适中的水温,才不甚放心地走出去,关上门,“我马上就回来,有事一定要叫我。”有些鸡婆地再重复了一遍,怕冬雪没听进去。
浅浅的笑浮上丽容,感动于他的细心,冬雪褪下脏污的衣服,撑着墙,让热水从头淋下,清爽的感觉总算回来一些。心头的暖意加上身体的温热,使肚子疼得不再那么厉害。
“雪——”敲门声有礼地响起,是苍拓凌回来了,“衣服怎么送进来?要我放在门口你出来穿吗?”那样不会着凉吗?抱着衣服苍拓凌不知该怎么办。
怎么送?他送进来?当然不可能。但,她走出去?能行吗?因不知如何回答,冬雪一时无语。“雪?!”这次声音大了些,苍拓凌有些犯急,怎么只有水声而没回答声?虽焦急也不好造次。实在明白自己撑不过这几步路,她正欲开口回答“你就放——”被再次更高声的询问声“雪——”心急的扭动门把的声音及哗哗水声给彻底盖住,未完的语句一时卡在喉间,上不去下不来。
呆呆地忘了刚刚回答完后准备背过身不去看他的冬雪,傻傻地侧身看着同样错愕的苍拓凌,忘了接下去的反应。
因蒸水而使白雾充斥着浴室,腾腾热气间,隔着绵绵水帘,冬雪完全超出他预料外,完好无损如优雅女神和害羞小鹿的混合体般侧倚着墙壁。雪白的肌肤因水的冲刷而泛着润泽的粉色,水丝打在她身上,又顽皮地弹开,像天使般吻着她美好的颊、肩、臂,以及……苍拓凌呼吸热情而又急促起来,眼光愣在她完美的浑圆上一时离不开,两朵红梅骄傲地挺立着,艳丽的红泽让人想一口吞入腹中以解饥渴。想起他曾拂过的每一条曲线,想起他曾吻过的每一寸肌肤,想起她无措却欢愉的反应,无数美好的记忆一下子冲入脑中,挥之不去。
下身一阵肿胀,伴杂着隐隐难忍的疼痛,欲望在呼喊着纾解,苍拓凌却让大脑作出相反的反应,“衣服我放在这儿,早点穿上别着凉,旁边是卫生棉——”不能碰,不能碰,冬雪会以为你是什么?趁虚而入的伪君子?离开,快些离开,门就在左边——
脚步快速地移动起来,但是目标却远离大门而直奔向快脑冲血的冬雪,不,他想抱她!
说不清是想拒绝还是想接受,他的吻已如雨点般击来,每一个她敏感的角落,每一个令她呼吸急促的地方,都被他热情地搓揉着,恣意吮着。从喷头而出的水悉数打在他的身上,湿了衬衫,湿了西裤,湿了那迷醉的男性脸庞。他埋在她胸口,如狂风过境般肆虐着,湿透的发刷着她敏感的皮肤,和他的吻一样,激起她狂野的反应。摩擦的快感不是皮肤的滑腻带来的,而是衣衫的粗糙。它因了他火热的动作磨蹭着她的娇柔,令她全身红潮片片泛滥。
无力地被他强撑着,冬雪想起自己的不净而妄图反抗,却无力逃脱下腹莫名想纾解的喜悦感受,只得拼命摇着头,喃喃着:“放手,拓凌,我现在,好脏——”但十指,却插入他丰厚的发,拉近他,不避讳他的激烈。
病人!冬雪现在算是个病人!她现在非常虚弱!尽管男性象征已隔着单薄的西裤抵在她的私密处蓄势待发,仅有一丝理智却拼命告诫自己:放手放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压抑着苦苦呻吟,松了手,转而死搂住冬雪,查觉她的不安动弹,闷闷地低声警告:“不要乱动,否则不管你是否安好我都会要了你!”
滴答滴答的水珠溅着,跳跃着,仿佛都应声和着:“离开、离开、离开。”
压制住脑中旖旎的幻想,待气息稍缓,他才赶紧小心地让冬雪扶墙站好,垂着头,双眼没勇气看冬雪可能会是责怪与愤怒表情的脸,“对不起……我出去了,你小心点。”
垂落的湿发落在他额前,让他看来有些孩子气,冬雪才想伸手拂顺他的发,却让他一下子推出了怀抱。看他冲出浴室。落荒而逃的背影写着一遍又一遍的三个字:对不起。忽然间失了炽热的源泉,冬雪一下子双手环住自己,脸上是羞涩与毫无畏惧的笑。这时她才明白自己的心情,就算他刚才真的控制不住而要了她,她也不会后悔。他,毕竟是她那么深深爱着的人啊!
甜蜜的笑容在扩大,照亮了苍白的病容,而苍惶跑出门去的苍拓凌没有机会看到冬雪的眼中全是满满地写着回答:“我不后悔,真的。”
虽然数分钟后无可避免地再次相见少不了有些尴尬,但冬雪捂着腹,颤巍巍地扶着墙想学正常人努力迈出步子前进的羸弱模样终究打破了屏障。苍拓凌抱着满怀沾脏的床单、凉被,怕冬雪怪罪他唐突的担忧此刻全抛在看到她逞强的心疼后,有些气恼她不爱惜身体地怒喝,倒也透露着深深的关怀:“你在做什么!站在那儿,别动。”他只是去拿脏物准备洗,转眼回来就看到这种情景。
预设两人会静默一阵的冬雪,想都没想到他出口的第一句却是这个。果然听话地乖乖站好,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看他麻利地将洗衣机打开,扔进床单、凉被,转而扯着胸前的纽扣,扒下湿漉漉地服贴在他身上的衬衣,同样塞进洗衣机中,染晕开留在衬衣上的血渍,像盛开的朵朵血梅,衬着衬衣的雪白,分外撩人。
莫明其妙地红了脸,冬雪的目光从衬衣上顺势移到苍拓凌健壮的上半身。他有着线条分明的肌肉,却不夸张,相反只会将衣服撑得更有型,说明他是个注重运动的人。比起她一身娇滑雪嫩的肌肤,他是如所有男性般干净粗糙,但也有着室内工作者特有的白净。在他转过身,走过来时,运动着的裸露的上半身美感更足。
不自觉吞吞口水,目光痴聚在他的胸肌上,没有发觉他已走近,脑中只有想摸摸看的念头,待她发现她的身体突然一下子靠近她,面颊“亲吻”上他的胸肌时,红霞立聚,并慢半拍地发现她正被他抱起向他的卧房走去。这个人,好像很喜欢抱她。
“做,做什么……”紧张地再次咽咽口水,实在不能怪她想象力太丰富,刚刚在浴室的激情画面还没有消化完,她现在脑中又全是他的壮硕胸肌,目前又正前往他卧室的途中,她这么反应是很自然的,“要继续吗?”真是不怕死啊!
丝毫不觉自己问了个多傻的问题,直到发觉苍拓凌眼中突升的炽热火焰时才知道不对劲。方才他是霸道却也温柔的,欲望至少隐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心灵之窗的眼睛,可没有泄露出来,而且,他房内床头柜上有杯正冒着热气的牛奶,甜郁的浓香充满室内每一个角落,这说明,他根本无心再继续对她作出越轨行为,而只是纯粹在关心她,直到她的话点燃了火焰。
可醒悟过来的呆呆美人想凭傻笑是蒙混过不了关的。苍拓凌俯首一个吻点住她惹祸的唇,轻轻地,就这么一下,惩罚而已,意犹未尽地,没有预想中的火热。他端起牛奶放到她手中,命令:“喝。”接着走向衣柜,找出一套衣服。
还以为他会再烧场大火,燃遍她全身,最后却只有这浅浅一啄。冬雪无比失望地啜了口牛奶,让润滑的滋味由口入腹,温暖她。查觉他要出去,想都没想地开口问:“你去哪?”
向来对她只有温和或热情或宠溺表情的脸上这次是皮皮邪邪地一笑:“还没成为我老婆就这么快管我了?”扬扬手中的衣服,“要我当众表演脱衣秀吗,亲爱的小娘子?”
微愠他的轻佻,暗骂自己的情急,缩上腿,盘坐在床上,冬雪双手捧着保温杯,垂下头,细细地小口啜着牛奶,不知如何反应也不敢抬头理他。
苍拓凌笑着她单纯的反应,踏出门去。再待下去他就真的不能保证止于刚才那轻轻一吻了,而是确如冬雪所说,将她压向床去……
刚换好衣服就被厅内电话铃声给拉去,是从医院来的。
“昊然,什么事?”
“火霆回来了,同时还带了一个人来,塞洛斯J。”
突然间忘了怎么去呼吸,脑中就中断思维。在他背着冬雪寻找名医,面对过众多名医诊断后的摇头叹气后,要他接受如此一位权威专家的诊断,心中的不安不言而喻。
轻轻的笑从电话那头传来,仿若感同身受。昊然明白他的静窒:“有50%的希望。”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下电话的,不知道是如何踏入卧房的,带着那不算好不算坏的消息痴望那明丽温婉的容颜,所有的希望上上下下飞跃在胸口,心,乱得如麻。
“拓凌?”
跪坐上床,从背后用臂环住冬雪的纤腰,头颈搁在她的耳后。他爱她,很爱很爱,愿意拿生命去交换地爱她。许久以来的失去,让他在拥有她时小心翼翼。这一世,他多希望能与她长相守,再不分离,回敬命运的戏弄,可是,造物弄人,只能以这种形式吗?他父亲的内疚,冬雪父亲的痛苦,他朋友的同情,他没法不去面对。但手术成功的希望只有50%,成功,固然是好,失败,就再也没有希望……“雪,你好些没有?”
“好多了,我的第一天刚开始时就是这样,来势汹汹,过了大半天就缓和下来了。”真难相信她能这么向他倾诉多年的烦恼。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医院吗?”
“去医院?”冬雪没说话,之前去过医院几次,她实在不忍看到父亲苍老悲戚的身影,接受不了惟一亲人看不到她的事实,在两次声嘶力竭地哭倒在苍拓凌怀中后,他不提再去医院的事,她也不愿再去面对这残忍的一切。说她驼鸟也好,当幽灵的每一天,她都愿这样与拓凌厮守,既使,她也矛盾……“可以去,但为什么?”
苍拓凌决定让冬雪自己决定未来,他不是她,不能代她选择她自己的人生。
“康平”综合医院。
优雅精致的会客室内,坐着三位气质各异的男人。冷然超脱的昊然,俊美邪气的火霆,及淡笑的塞洛斯,他是世界顶级外科手术专家,尤其擅长脑部手术。
苍拓凌踏入会客室内,没急着和老友打招呼,只是默然打量这位昊然提及的外科界精英人物。精致白净的脸庞,有双深邃的漆眸,挺直的鼻梁,轻抿的薄唇。唇边隐约两个浅浅的酒窝,添加了他干净的气质。笑容轻灵,细看之下,却没让笑意直达眼底。长发及腰,但规矩地束于脑后。体态颀长,悠然立于窗旁。从撑起外套的衣架子及沉缓吐纳来看,也该是个不露身手的练家子。
“幸会。”伸出手,苍拓凌状似友好。这个男子看似无害,却有着令人捉摸不定的飘渺气质,他不愿却也不得不防。
“幸会。”一只修长而修整洁净的手有力回握,“您就是苍拓凌先生。”
“是,内人的病就拜托你了。”平静无波的话语,听不出喜怒,也听不出是真心或是假意。
“我会全力以赴的。”又一个浅笑,含意不明。
“一通屁话……”四肢瘫散在真皮沙发上,已从昊然口中知晓来龙去脉的火霆对上苍拓凌扫来的目光慵懒一笑,深深酒窝立现。那家伙明明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却有着一个明明白白外国人的名字。他不爽他。
奇怪,火霆是个个性分明的人,喜欢的人就是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直来直去,不爱拐弯抹脚。看样子,他似乎很讨厌塞洛斯,但人是他请回来的啊?!苍拓凌思索着,不知其中有何问题,“内人的病只有50%的希望吗?”
“目前是。”他似乎不是个爱多说话的人。
“目前?你的意思是——”
“所有的诊断只是初步的,具体的情况我还需更进一步观察,这点希望苍先生能理解。”
如果他没记错,塞洛斯是个随心所欲从不在意他人感受的人,他何曾用过这种征求的口气说过话?“当然,你是医生,我是会尊从你的意见的。”
昊然静静听着二人毫无味道的谈话,思索着塞洛斯的异常,和苍拓凌一样想着其中的原由,而火霆则有些受不了地死命搓着胳膊,这两个人的谈话简直不像他们本人会说的,又做作又肉麻。
怪异的气氛持续着,直到苍拓凌喊停。
“时间不早了,也麻烦你这么久,送你先去休息吧。”苍拓凌站起身,不愿再多讲。这个男人实在难缠。
“好的,刚刚下飞机就直奔这来,我也确实有点累了。”揉揉额角,塞洛斯也略显疲态地笑。
四人相继离开会客室,沿着长廊向电梯走去,但途经冬雪所在的病房时,塞洛斯转头望了眼挂着名牌的房门,一直平静的眼突然升起一股笑意,不仅他停下脚步,连苍拓凌、昊然、火霆也停了步。
“有什么事吗?”苍拓凌直觉不对劲。他对冬雪在车上讲明了情况,冬雪却不愿进去见塞洛斯,只说听他的安排。所以他暂且将她置于她的病房内,让她等他回来接她。
伸手打开病房门,塞洛斯同时也踏入房内。绕过彩绘屏障:“噢,我忘了刚才火先生有没有给莲花加上水了,若没有水,这娇嫩的花是会很快枯萎的。”
他的动作相当快,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进入。他们三人立时跟上,除了苍拓凌,其余二人也愈来愈觉得这个男人有点不对劲了。
“莲花?”苍拓凌不明白。
“早叫你不要送什么劳什子花,现在就不会这么 嗦了。”嘴上是抱怨,火霆心里头却提高警觉。
而所有人的言语全都在看到眼前的美景时悉数终止,早先进入房内的冬雪站在窗边的花瓶旁,弯着腰,低着头,转首回望,这个姿势可想见先前她正在嗅着花香,如今却被人打断。阳光丝丝洒入,映得冬雪白玉般的面庞泛着柔和的金黄,长长的发丝有的垂下,有的卷在肩上,有的随着点点的风轻轻摆荡着。宽松的连身长裙蓬松纤薄,衬得她像个娇弱的金色洋娃娃。轻松而欢愉的笑毫无防备地写在脸上,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但所有人中似乎不包括塞洛斯。“嗯,好像加了水。”走过去,塞洛斯伸手探入瓶内,与冬雪正握着花茎的手碰个正着,状似无意,却又似有意。而他清澈的眼更是在看向花时,也像是发觉她似的看她。
是她的错觉吗,她怎么觉得他看到她了呢。冬雪飞快地收回手,往后退了两步。他对她没有排斥感,而且,他的手,他的眼,好烫……不对劲。“我就说了有水嘛!”鬼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的呢。火霆一把捞过塞洛斯,“走吧,还要带你去饭店呢。时间不早了。”唉,小嫂子还是像前世那么好看,可惜事态紧急,容不得他多看。
昊然更是早早打开了房门,等待他俩走出来。
而这一切的急切,仅仅是因为苍拓凌微眯的眼。这代表着,他现在很不满。塞洛斯的唐突很有可能吓着了毫无防备的冬雪。
三人与苍拓凌擦身而过了,塞洛斯在将踏出门时更是似有似无地投来暗藏的一笑。
房门合上了,留下满心疑问要解决的苍拓凌与脆弱的冰晶美人。
走上前两步,苍拓凌展开手,什么都没说,冬雪则明了地一头扑入他怀中,将手放入他掌中,任他轻拂。
昊然是冰冷的,那个触碰她手的人是发烫的,只有她的拓凌,永远是温暖的。
“他是谁?”倚在他怀中,侧眸看着床上的自己,轻轻地问着:“塞洛斯吗?”
“你认识?”
“他那么有名,只要是外科界的没人不认识。”他好像变粗心了。
“噢,我忘了你是个医生。”语调挺不以为意的。
冬雪一下子被他不以为然的轻松语调给逗乐了。这个男人,近来常常以逗她为乐。轻捶一下,以示惩罚:“他怎么说?”这一句,问得有点小心翼翼。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一起去见他,而要在这儿呆着,等我回来问我呢?”先把这个问题问清楚再说。
“我不敢。”
“不敢什么,见他吗?他又不是三头六臂——”
“不敢知道手术能否成功的消息!”急冲冲地打断苍拓凌的胡言乱语,一口气说出心中所恐惧的。
苍拓凌心中有期待也有担忧,在他的逼问下,她的答案会是如他所料的吗?她能给他一颗定心丸吗?他的一切说明了他对她的爱,但她除了承认过他是她的梦中人外,就没说过爱他之类的话,虽然她的接受表明她是在乎他的,甚至是很在乎的,但是,他想听到她亲口的承认。
“手术成功了你就可以重新成为万人尊敬的著名外科医生。”
“手术成功了固然是好,父亲就不会那么难过——”也能够和你在一起而没有阻碍,“手术一旦失败,那比让父亲看着我活生生躺在病床上不醒更要痛苦万千倍。”深深吸口气,努力地排除脑中所构筑的想象。可安慰了自己,却骗不了自己的心。鼻子酸涩无比,似有泪下来。他怎么能知她心中所虑,那样的她就再也不能见他的笑,他的忧,他的温柔,他的温暖……也许许多年后,他会拥着她生命中的另一份爱,向她诉说她的故事。若真有这么一天,她不怪他的,但心啊,怎么这么痛呢?她已经发呆了许久,他也等了许久,久到他的心已快要变冷。他还是打动不了她的心吗?他的满腔爱意只是一厢情愿地付出吗?那她的甜蜜的笑,小心的回应,她不避讳的肌肤相亲只是男女间最单纯的性吸引力吗?而不是他自以为是的“爱”?
“你若不爱我,就不该给我希望,让我以为这段日子以来你的表现可以解释为你在接受我!”低吼出来吧,要伤就一次让他伤个够。
原来他的突然转变是为这个,是他的不确定,是她的不勇敢,让他瞬间痛成这样。“傻瓜……”忧愁的心转了晴,苦涩的唇咧了笑。这个呆子,她只怕他不要她,他怎么担心她会不爱他呢。或是她的表现不够明显,让他乱了心?
“什么?”没听清她刚才说的。明明决定抽手,却怎么也放不下她的一切。大脑,嘴巴背叛了他。勾上他的脖子,脚步往前迈了一步,贴上他的身,澈亮的眼一眨也不眨地直盯着他的:“我以为你懂的,谁知你是个大呆瓜。”
换了苍拓凌痴痴呆呆兼不明不白,不过心中却因冬雪奇异的神态而有种强烈的预感——接下来的话让他欢欣鼓舞,也许还是一辈子。
“我想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我爱你。”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