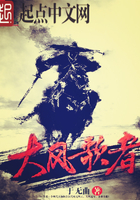“来者何人?”
“只是路过,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带有兵刃?”
昨晚与曹淮雪一战打烂了藏剑的琴盒,一觉醒来迷迷糊糊的又完全忘记了这事。张楚不欲动武,正琢磨着该如何作答,那将军却大手一挥,守卫把这二人团团围住。
“可有朝廷公文?”将军又问道。
张楚仍是不答,骑在马上皱起了眉头,看着这一圈的守卫。德子自然清楚公子心里想的什么,可光天化日之下诛杀朝廷将士,这事无论怎么说也太大了。
张楚解下背后的长剑,嘴角一挑:“你说的可是这个?”
好一声龙吟。长剑出鞘,张楚轻描淡写的抖了个剑花,仍是打不定主意。杀了守卫,那可就真是亡命天涯了。不杀,眼下又没有脱身之计。
“拿下!”将军口中一喝,显然是不欲纠缠。
“慢着!我们有腰牌!”德子大声喊道。正要抽剑而出的张楚惊疑的瞪大了眼睛盯着德子,没有说话。
守卫也立在原地,回头看向自己的将军。那将军眉头一皱:“什么腰牌?”
德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打开后里面有三百两银票和一块暗铜色腰牌。
“我家公子乃福建沿海聚沙帮三堂主!有福建观察使亲自颁下的腰牌为证,故而持有兵刃!”
一位守军接过腰牌递给将军,那将军翻来覆去的观看,又说道:“为何不早拿出来?”
德子言辞凿凿的说道:“我家公子素来低调,况且此行有要务在身,不愿暴露行踪,多有得罪。”
“去,把师爷喊来。”
张楚莫名其妙的看着德子,他并不知道有这块腰牌。福建聚沙帮他更是没有听过,什么时候自己倒成了堂主了?还是朝廷的堂主?可他只是心底狐疑,面容不改。那将军不再问话,也不放行。一会师爷赶到,接过腰牌仔细研究起来。
“禀将军,此腰牌却乃大内工艺,民间是仿不出来的。”说着,便把腰牌递还给将军。
“那福建聚沙帮是什么来头?”
“聚沙帮乃是福建沿海三十一村庄联合起来抗击日本浪人的帮派。朝廷无力为日本国分心,福建沿海的平安只能靠他们自己维持,故而颁下腰牌,允许习武。”
“哼,什么日本浪人,不就是倭寇嘛!”说着把腰牌扔个手下兵卫:“二位多有得罪!近来颇不太平,二人还是小心为妙,这里可不是福建!”
将军马不停蹄的走了,守卫也跟着他撤了一大半。即便是这样,邢州城的城门口也可说得上是重兵把守。
“公子,看来咱俩还没被朝廷通缉。”德子侥幸的笑着:“可这邢州城怎么这么多兵?”
张楚不理这茬:“你那腰牌是怎么回事?”
德子抓抓脑袋,说道:“福建沿海常被倭寇掠夺。老爷十三年前回岛时便教了我爹一些拳脚,叫我爹把大伙集中起来联合抵抗,时间久了便形成了聚沙帮。临行前我爹给了我这块腰牌和三百两银票,行走江湖以备不时之需。我怕公子不喜欢有朝廷背景,就一直没敢告诉你。”
“早知如此,我还背那劳什子琴盒做什么,弄的别人都以为是我文人雅客呢!”
“公子你不生气?”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又不是你聚沙帮的人,再者说了,就算我是,那也是朝廷认我,我不认他,与我何干?”
说话间方才城门口那将军带着大队人马疾驰而过,去势汹涌。
“今天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张楚小说说着。
主仆二人又见两个官兵手拿黄纸,一路小跑着贴在城墙上面,引得一群人围了上来。二人牵马走向城墙,想瞧个热闹。
德子边走边问:“公子,曹淮雪会不会在这城里?”
“你想她了?”
德子笑道:“公子,我看是你想她了吧。”
“我确实在想一个人,但不是她。”张楚故作神秘的说道,却又不肯再说。无论德子怎么追问他都只是笑笑,仿佛很享受德子好奇着急的样子。被追问久了又实在是搪塞不住,转移话题似的说道:“曹淮雪恨我入骨,她早就应当通知官府派兵捉我来啊,怎么不见动静?”
“那你还敢进城,这岂不是瓮中捉鳖了么。”德子脱口而出,自己倒是先乐了。
“我也是一时大意,可现在着实是有些奇怪。”张楚敷衍着德子,心中暗忖:杀害洛水营都统一事找了自己这样的江湖人士,为的是隐秘。现在事成,他们自然有杀我之心,可绝不会大张旗鼓的派人来捉,而是暗杀,才能避免节外生枝。
这也是张楚进城的原因,闹市之中,想要暗杀自然是不易。可叫张楚奇怪的是曹淮雪,难道是追过头了?
张楚摇头苦笑,管她呢。
只听人群中有人叹到:“多事之秋啊,多事之秋。”言语甚是沧桑无奈。张楚这才把注意力放到告示上,黄纸黑字,盖着朱砂大印,竟是篇檄文,声讨的是镇国公卫正岭。洋洋洒洒数百字,言其忤逆,吾皇念其军功一忍再忍。言其谋反,吾皇仁厚,不忍相信。如今证据确凿,卫贼又拥兵自重,暗杀军中大将,以图掩饰。吾皇挥泪,只得出师,以保漠北之平安。
“镇国公三朝元老,竟是这般下场。”德子叹道,引来周围一阵附和。张楚其他的不知道,但这暗杀军中大将一条,指的应当是杜修之死,强加在卫正岭的头上。
“公子,倒是件好事。”德子小声说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想那曹淮雪应该是接到军令回营去了。”
张楚的脑海中浮现出那日在洛阳城李府黑屋中与他对话之人。张楚也能视物,看到黑屋中一人面对着他,一人背对着他。想来自己是为镇国公这事推波助澜了一把,幕后之人应当是背对自己之人,李府也应当是他的府邸,不知究竟是何方神圣。
主仆终究还是没能跑过乌云,邢州城的阳光被染成了灰色,沉入人心。其实漠北远在几千里之外,事不关邢州。可阴沉的天气终归让人提不起精神,仿佛在为国家担忧。乌云密布,厚积薄发,眼看是场大雨。主仆二人急忙找了客栈,豆大的雨珠开始砸下。电光一闪而过,轰隆的雷鸣就像天宫神兽发威的怒吼,沉闷而带有威慑。大雨终于瓢泼而下,也不知此时是什么时辰,人们都早早的睡了。
依然是住在紧挨马厩的房间,屋子里只亮着一豆烛火。张楚盘腿而坐,似乎已经入定。无精打采的店小二送来晚饭,德子百无聊赖刚要动筷,听到雷声响起,窗外的马儿嘶吼不止。德子以为是马儿受惊,又听到马蹄铁哒哒的踏着泥泞。张楚猛然睁开双眼,德子打开窗户,风雨直吹脸颊,模糊的看到有一人飞马而走。
“骑的是你的龙驹!”张楚出现在德子身旁,忽然说道。
“什么?!”
德子话音刚落,张楚持剑跳到马厩。放眼望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德子随后跳下,奈何这倾盆大雨,追是追不上了。
一队铁骑踏雨而过,为首的正是守城的将军。
“将军!我的马被人偷了!”德子一把拽住眼前的缰绳大声嚷到。即便如此,这声音在这雨夜也十分渺小。
“你起的是什么马?”将军也同样大声的喊着。
“龙驹!千里龙驹!”
“******,赶紧追!跑了曹淮雪,全都吃不了兜着走!”将军提起缰绳狠一抽马鞭,马儿疾驰而过,溅了德子满身是水。
锋利的剑刃似乎把坠落的雨珠都一斩而断。剑光一闪,将军惊喊着跌落马下,他的坐骑已经失了后腿。其余将士一阵慌乱,还没等他们看清什么,剑光如电光一般接连而过,猩红色的鲜血骤然喷出,混着无情的雨水摔落在地。
张楚的剑尖抵在将军的脖颈,他想问些什么,又发现实在没什么好问。那也不必留下活口了,一剑划过,还未等这将军展现铁骨铮铮或是软弱怕死,便已经一命呜呼。
“公子?你是想救曹淮雪?”
张楚不置可否,随便跨上了一匹战马:“德子,你骑我的红马!”张楚大声喊道。
“去哪?”德子一边上马一边紧张的问着。
可张楚已经驾着惊慌的马儿迎着雨水而去,在雨夜中,只留给德子一个潇洒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