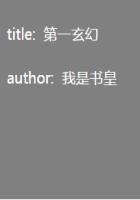黄掌柜大概是熬了一晚,整张脸都肿的,看人的眼神有些闪烁。
“黄掌柜,早安。”夏至和夏青一起行礼,礼多人不怪嘛。
“……”黄掌柜没有回答,连头都没点一下。
夏青刚想问什么,夏至一个眼色制止他。
在夏至看来,黄掌柜既然来找,事情一定有了结果;看他这个样子,结果大概不尽如人意。
就像他说的,结果好一些,就是净赔五匹绸缎;看他这脸色,莫非客人要求赔所有?可是,如果是赔所有,黄掌柜应该更疯狂一些,赶紧筹钱款去啊。
无论如何,黄掌柜都不应该是这副样子。
既然横竖猜不出结果,所以,夏至静静坐着,等他开口就好。
钱掌柜自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自然好奇黄掌柜为何这么古怪,过来招呼:“黄掌柜,今儿来这么早,进过早点了吗?”
“小二,照黄掌柜平日的喜好,来一份早点。赶紧的。”
“省得了。”小二颠颠地去了后厨。
不一会儿,一份精致的搭配好的早点就呈到了黄掌柜面前。
黄掌柜这下像重启了一样,两眼放光地盯着夏至。
这变化太快太突然!
若不是夏至了解也打听过黄掌柜的为人,一定以为遇到大色狼了。
“夏小娘子,我熬了一宿没合眼,这么早就在这儿等着,你怎么什么都不问呢?”黄掌柜的眼神都不一样。
“黄掌柜,您想说自然会说的。”夏至晾他。
“你就不能问一下吗?”黄掌柜很不高兴,又暗藏喜悦。
“黄掌柜,您就不能直说吗?”夏至有些哭笑不得,多大的人了还这么玩?
“走,随我去染坊,”黄掌柜不管不顾,一手拉一个,就往门外走,临了撂下一句,“早点的钱记在我帐上。”
夏家姐弟互看一眼,看这样子,多半是好事,去就去呗,谁怕谁?
上了马车,黄掌柜不停地叹气:“没想到啊,唉,没想到啊……”
夏至终于忍不住了:“黄掌柜,您直说成不成?!您昨儿个也说,好一点儿,净赔五匹料子;最差就是全赔。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句话呀!”
“还有,最重要的是,昨儿个没谈工钱先干活儿,这个该怎么算呢?”
黄掌柜又回复两眼放光的状态,热情洋溢的眼神,让人渗得慌。
夏至翻了一个大白眼:“黄掌柜,拜托您有点正形好么?您好歹是经营而且把祖业发扬光大的掌柜。到底怎么样了,赶紧说。不说,我们就回去了。”
黄掌柜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文契,递给夏至:“快看,快看。”
夏至也不推辞,接过来一看,立刻直了眼睛。额滴神啊!这……绝对是歪打正着,错有错招啊!
文契里写道,另送五匹绸缎染成粉红色交货;订五匹云纹绸缎,若被更大的主顾看中,则追加五十匹大单。
这才是大买卖啊!
夏至含着笑意,问:“黄掌柜,咱们算算工钱呗。”
黄掌柜思来想去,说道:“夏小娘子,染坊的大师傅例银五两,起早贪黑,忙得脚不点地。我也可以请你当大师傅,昨儿个的工钱算五两,怎么样?”
夏至一听乐了:“黄掌柜,昨儿个的五两纹银拿来。”
黄掌柜立刻奉上银两。
夏至掂了掂,然后对夏青说:“阿弟,咱俩走。”
“哎!”黄掌柜急忙拦住他们,“夏小娘子,你别走啊。一切都好商量!”
夏至又转回来:“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好价钱,工钱也是一样。我先声明,第一,我不会印染,也不打算当学徒,也不想当大师傅。但是,经过我的水洗,布料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是。”黄掌柜应了一下。
“我不要你平日给工钱养人,只做特定买卖的水洗,您按量结算就可以了。若是又有污了色的,另外算水洗工钱。我喜欢多劳多得,行不行?”
“行!”黄掌柜点点头。
“黄掌柜,洗衣铺子按布料算,我也这样。水洗一匹绸缎,一两银子;水洗一匹丝帛,八百文;如果还有什么金丝银绣的特别料子,就另外算。”
黄掌柜算了一下,心疼牙疼肉疼,不愿意答应。
夏至自然明白,她的价钱真心不便宜,可是,谁让“物以稀为贵”呢?!她有金手指,就是这么牛掰!
“黄掌柜,我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若是买卖赶得特别急,还剩四匹污透了料子,我今儿就替您水洗出来。您爱算多少都成。”
“之后,您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试料,也有时间另寻他人。我等您的答复。”夏至就是这么爽快的美少女,嘿嘿。
黄掌柜听了半晌没说话,之后才幽幽地说了一句:“夏小娘子,你真的只有十三吗?”
“是呀,如假包换。”夏至笑得坏坏的,如果黄掌柜有其他人选或者法子,他根本不会来找自己,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下了马车,夏至说到做到,按照昨儿个的要求,不是昨日的流程,一股作气把剩下的污料都水洗出来。
短短两个时辰,染坊的晒架上再次晾满,院里院外都像落了彩霞一样。
临走时,夏至和夏青笑眯眯地挥手:“黄掌柜,您好好考虑哟。”
黄掌柜站在染坊的大门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两孩子哪有半点山里人的样子,聪明得让人牙根痒痒,又让人牙根痒痒地喜欢。
他之前所以熬了整晚,其实是他去找了下单的客人,客人也拿不定主意,也是连夜去找了上头的客人。辗转整晚,辛苦波奔。
最后,他听到了客人转达的最高客人的原话:“粉如丝缕,灰若云彩,交缠绵长,此等绸缎,我做皇商多年,也是第一次见到。此色可曾命名?”
“回乔公子的话,还没有。”
“就叫……夏染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