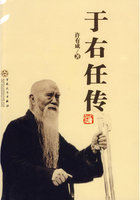莫小则痛失亲人,五内俱焚。他一番追忆引的花月和呼延秀垂泪,关婷刚才被支湃挤兑了几句,脸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听了莫小则的话,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过了,她拉起莫小则的手:“相公,跟我回军营吧,我们一起报仇。”
莫小则又甩开:“不用了,你走吧。”
关婷一愣:“你让我去哪?”
“爱去哪去哪!”莫小则脑子里一片乱。
关婷又悲又气。
莫小则对花月拱了拱手:“姑娘,你也上楼去吧,让我自己静一会儿。”
花月在丫鬟的陪伴下,一步三回头的上了楼。
关婷爆发了:“姓莫的,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你竟敢赶我走?好,那我就走,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去请我,我再也不回来了!”
说着,跺脚转身就走。呼延秀一把拽住她:“少奶奶,刚才公子不是那意思,你别误会!”
关婷看了莫小则一眼:“我看他就是那个意思,我不在这儿给他添乱了!”
其实,以呼延秀的力气,根本拉不住关婷,关婷就在等着莫小则或者支湃说句话,服个软,给个台阶。
可莫小则根本不接茬。关婷负气出了门,盔甲甲叶子的声音越来越远。莫小则一动不动。
关婷在院里回头看了看,没有任何人出面来劝自己,她上了马,慢慢的往外走,忽然背后有跑出来追赶的脚步,关婷心里暗喜。
回头一看,是呼延秀。
“少奶奶,现在公子悲伤过度,你就别太介意了。”
关婷看了看屋内:“姑娘,我走了,或许这就是我命里该着的,你好生伺候莫公子,有机缘,你俩倒是挺合适的。”
呼延秀晃悠着缰绳:“快下来吧,你说的对,命里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你生来就是带兵打仗提刀策马,我生来就是掌钳淬火敲敲打打。我是公子买来伺候莫夫人的,你可别瞎琢磨了。”
关婷无奈的笑了笑,她心里也是很犹豫,回屋吧,支湃又该冷嘲热讽了,自己面子上挂不住,回大营吧,新婚之夜就被抛弃,无法面对众将士。
这时,楼上悠悠古琴奏起,花月的歌声接着飘了出来:
道不尽声声珍重,默默地祝福平安。
人间事常难遂人愿,且看明月又有几回圆。
远去矣,远去矣,从今后梦萦魂牵。
听了这歌声,关婷下了决心似的拽过缰绳:“秀儿,我走了,他要是想找我,就去军营。”
伴随着一声打马的娇喝声,一骑雪白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沉沉的夜幕里,呼延秀裹紧了棉袄的领子回了屋。
呼延秀进了屋,责怪的训支湃:“你说你,人新婚的娘子,吃点醋撒了娇也就算了,你跟着瞎起哄,现在好了,人走了!”
“走就走,三条腿的蛤蟆寻不见,漂亮的姑娘满街转,她走了,这不是还有你呢嘛,她走了更好,你俩入了洞房得了!”支湃满不在乎的回答。
呼延秀羞的用指甲掐住支湃的手背,支湃龇牙咧嘴:“你要是不乐意,楼上还有一个呢!我去请,何处黄土不埋人,何处房子不是洞房啊!”
呼延秀把支湃按住:“你消停点吧。”
呼延秀把茶杯递给莫小则:“公子,莫夫人的事儿让你乱了方寸,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的,首先,莫夫人要是真走了,你就不活了?再者说,也未见得莫夫人就死了啊。”
刚才还一脸茫然的莫小则,听了这话,就跟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握住呼延秀的手:“此话怎样?”
呼延秀挣了一挣没挣脱开:“人死之后,心愿未了,鬼魂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可是,刚才我在赵府,根本就没看见莫夫人的魂灵。”
支湃一脸疑惑的问:“你,你真的能看见魂灵?”
呼延秀点点头。
莫小则忽的站起身:“对呀,我怎么忘了这茬了,即便是我娘真死了,七日之内,她的魂灵也能随便附在谁的身上来见我啊!”
“这说明什么?要么是莫夫人根本就没死,要么就是回破庙等你了。”呼延秀分析的头头是道。
莫小则狂喜,忍不住的狠狠的在呼延秀的额头上亲了一口,呼延秀直臊的手脚没处放,却又不愿拂拭去额头上的口水。
支湃在一旁也是来了精神:“呼延秀你这丫头是故意的吧,怎么不早说呢?”
“我当时也是伤心难过的没想到,刚才你和关少奶奶斗嘴,说做鬼也缠着她,我才想起来的。”
莫小则四外看了看:“关婷呢?”
支湃和呼延秀都没说话,这问题没法回答。
莫小则三人向花月辞行,连夜赶往破庙。花月满脸戚戚然的倚在门口,直到马蹄声消失了,还久久不愿回屋。
三人打马到了破庙,天已经接近黎明,只见破庙已经是一片废墟,前边咱们说过了,这是被赵府的人给烧了。莫小则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娘,你在哪?”
回声在山谷里的盘旋。
支湃看了半天也没个人影:“秀,鬼魂是什么样的?飘在半空,吐着舌头?”
呼延秀四下看了看:“没有。”
莫小则反而更开心了:“那我娘就是还活着。不在赵府,不在破庙,还能在哪里呢?”
“莫夫人和我说过,你们来到泫城一共也就去过这么三个地方,这俩地儿没有,恐怕也就是在扒鸡店了。”
莫小则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把十三婶家忘了呢。”
三个人又打马直奔郑家扒鸡店。路过西街朋远楼,一群伙计正在痛打一个少年,少年蜷缩着身子抱着脑袋一声不吭,伙计和厨子们手里拿着棍棒菜刀,边踢打边骂:
“他妈的,你个洋毛子敢来这儿吃霸王餐,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翻过身来打!”
“泫城就是被你们这些妖教祸害惨了,你还敢来传教,打他,打他!”
支湃一看,这少年太可怜了,屁股被打的跟毛血旺似的,脸被踹的像打了马赛克。
莫小则也看不下去了:“都住手吧,打出人命你们哪个担着啊?”
为首的伙计回头一看:“新郎官,你好好的去接新娘,这儿没你的事儿!我们不打他,一会儿掌柜的回来了,就该把我们往死里打了!”
莫小则下了马,伸手相拦:“差不多得了,还真要下死手啊?”
伙计一指地上的小伙:“这西洋人,进了我们店,要了一桌酒席,那可是五两银子的上等酒席啊!他就吃完了抹抹嘴不给钱,还他娘的传教,说我们都是罪人,要赎罪!”
莫小则等人这才看清,地上的果真是个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珠子。这黄毛儿吐着嘴里的血沫子,朝伙计伸出中指:“法克油!”
支湃一听:“哎呦我去,这词儿我太熟悉了。”
“什么油也不行!”伙计还想踢,被莫小则拽住了。
小则从怀里掏出10两银子扔给伙计:“五两的酒席钱,二两你们消消气,剩下的三两带他去医馆瞧瞧伤,你们要是再动手,咱就去官府说道说道。”
“这话儿是怎么说的,谢谢新郎爷了,那洋人,今儿算你运气好,遇上好人了,赶紧起来!”伙计们开始搀扶黄毛小伙。
旁边有一位围观的道士高颂一声:“无量天尊,施主好修行!贫道略通医术,虽只是江湖游医,但这点伤我还能医治,且容我一试。”
莫小则赶紧施礼:“道长慈悲!”
三人继续赶往了郑家扒鸡店,没进店就见门窗已被砸,进去一看,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碗碟杯盏散落在地,莫小则喊了一声:“十三婶儿……”
楼上有人探头一看,拍打着胸脯下了楼梯:“孩儿啊,你怎么还敢回来啊,赵府的人要抓你呢!你快跑!”
莫小则鼻子一酸:“十三婶,让您跟着受连累了,赵家已经被抄了,恶人也送了官了,您放心吧。”
十三婶双手合十:“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这可太好了,刚才听到外边马蹄声急,吓得我们赶紧跑楼上去了。”
支湃把桌椅摆了摆:“这都是赵府那些杂碎们干的好事儿吧?”
十三婶从腰间掏出抹布,擦了擦凳子:“坐坐坐,不碍事的,你们不懂,我们是做扒鸡的,那锅老汤没被砸,日子就能过,那可是几十年的汤了,我去给你们卤几只鸡吃,不过就是没有酒了,都被砸了。哎呦喂,这,这不是秀吗?你这丫头片子,进屋来也不和婶打招呼,你看看你,几天不见又水灵了!”
十三婶乐观热情的态度感染了众人,秀拉着十三婶的手说长说短。楼梯声响,十三叔下了楼,支湃迎上去:“叔,您那有烟叶子吧?”
老头掏出一个荷包,支湃赶紧用烟斗挖了一勺,点着了美美的抽了一口。
十三婶走过去,嘀咕了两句,十三叔从衣袖里摸出一样东西给了十三婶。十三婶走过来用食指点了呼延秀的脑袋:“死丫头,结婚了也不请婶喝杯喜酒,来,这一钱银子拿着,就当是婶随喜了,别嫌少啊。”
呼延秀连连推让。
十三婶急了:“你这丫头,跟婶还见外啊,你看看那汤锅,那还是你爹给我们铸的呢!”
“婶,我,我没成亲。”
“还骗我,莫公子穿的那衣服我能看不出?”
莫小则看了看自己的新郎打扮笑了笑。
“十三婶,我,我没嫁给莫公子。”
“啊?难不成,你,你嫁给他了?”十三婶偷偷的指了指支湃,“那孩子可不着调啊!”
支湃吐了一口烟:“我耳头没聋啊!”
久不言声的十三叔闷声说了句:“你这老婆子什么眼神啊,你没看丫头没开脸儿呢吗?”
十三婶仔细一看:“可不是嘛!那你也拿着。”
呼延秀只好把那一钱银子收下了。
莫小则问:“婶,我娘来过你店里吗?”
“没有啊,你和你娘走散了?”
听了十三婶的回答,莫小则如万丈悬崖一脚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