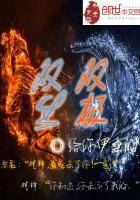崇尧在潞州住了数日,想念舜王坪,便向思礼说想回舜王坪,来年春暖再相约进兵泽州。思礼道:“崇尧兄想念兄弟们,亦在情理之中。”当下应允,并拨钱饷三千贯,粮草两千石与他回去过冬。思礼备言潞州正用人之际,教留下几个得力手下相帮。崇尧就教欧阳,中流同张行夫妻留下助他整顿潞州军政,遂同张雁,太清率一千兵士载了钱粮取道回了舜王坪。殿英想来,却教张雁止了,说他该回太行防守。思礼也拨给钱粮教他自去安置。于路无话,崇尧等回到舜王坪,萧宝应闻报,领着黄尚基,韩朝玉,李得晗,温石柱,盖简良,火盈盈,李香怡等部众下山十里相迎。直至中军大寨忠义堂上,叙了寒温,坐了。
崇尧将潞州鏖战,先败后胜的事说了。宝应亦说听说崇尧兵败,生死未卜,尚基,得晗,盈盈等人执意领兵下山,想去增援,还是宝应等人以舜王坪存亡利害再三阻挠,这才留住他们。薛嵩来犯,使得舜王坪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崇尧道:“多亏了二哥有远见,处事沉稳。不然我等没有立足之地了。”尚基道:“八弟,我们听说你被路登云一伙拿去,却是怎的脱险?”崇尧便将张行夫妻设计相救的事说了。
是日,宝应命人大摆宴席,为崇尧等人接风洗尘。香怡问张雁,她的哥哥何以没有一起来。张雁遂说:“你哥哥回太行山安置部属了,说过了年就来。”香怡闻言,好生懊恼。这些日子以来盈盈喜欢她秀雅文静,颇跟她合得来。每每约她说笑解闷,饮酒聊天,消遣时光,方才不甚寂寞。这番听了张雁的话,将信将疑,心想:“张雁究竟要将我怎的。”崇尧瞥见香怡落寞,盈盈一蹦一跳的带她去了,想起殿英等人的话来,思量道:“殿英他们说十二弟甚是喜欢盈盈,只不知盈盈意下如何。”当日尽欢而散。翌日,崇尧便找盈盈,说道:“盈盈,你跟十二弟到底是怎么回事?”盈盈见问,慌道:“听谁说的,我们没什么?”崇尧道:“支队的兄弟都这么说来,十二弟喜欢你,你对他到底是有没有好感。实对我说,不许隐瞒。”
盈盈爱着崇尧,却见他要将她送给昱人,分明是兄弟情重,顿时心头就像是被根针扎了一下,泪水夺眶流淌下来,愤忿的说:“我的事不用你管。”崇尧诧异道:“我问你话,怎的到哭起来了。”盈盈哽咽地说道:“我不喜欢他,你叫他死了这条心。”崇尧道:“这样的话,我就见到他时依你的话说了。”盈盈转思转痛,想道:“反正你心里没我,我也不留在你跟前碍眼,教你当礼物送来送去。”见他要走,遂说:“我明日就走。”崇尧一呆,回身道:“走,上哪去?”盈盈道:“回家,回沁州老家。”崇尧道:“数九寒天,匪寇横行,你一人怎好上路?”盈盈道:“你不待见我,留在这算什么意思?我的事以后不用你管。”崇尧道:“怎说这话?谁不待见你了,我将你当亲妹妹待。”
盈盈打断他的话,说道:“我不要做你的妹妹。”崇尧愈是糊涂了,说道:“这是什么话?”盈盈转身,目光紧紧盯着他,泪珠闪闪,一字一顿地说:“我爱你,你就看不出来么?”崇尧一怔,如受电击,惊道:“莫乱说。不,你不喜欢十二弟,也不要编这瞎话。”盈盈话已出口,覆水难收,索性要他个答复,说道:“你不是只要娶张姐姐麽?我做小还不成麽?”崇尧道声:“胡闹。孩子家净说胡话。”气的夺门而走。盈盈僵在当地,望着他的背影,伤心的泪水又一次流淌下来。哭了一场,恨极了张雁,气道:“我跟崇尧哥哥相识在先,凭什么教你抢了去。张雁,我跟你没完。”两下闹得不欢而散。
张雁见崇尧气咻咻的回来,问道:“谁惹你生气了?”崇尧道:“你莫管。”张雁笑道:“你去找盈盈妹妹了。”崇尧不答。张雁愈是肯定了,说道:“盈盈妹妹小孩子性子,犯不着生她的气。”崇尧道:“你也听说了十二弟喜欢盈盈,是么?”张雁道:“这个很多人知道,背后说什么的都有。我不想你为此烦心,所以一直没对你说。倒是看盈盈妹妹似乎不喜欢你那个师弟,不知咋想的。”崇尧注视着她的眼睛,仿佛看出些什么,气恼道:“你还瞒我。”张雁道:“我瞒你什么了?”崇尧难以开口,只是说:“抽空你去开导开导她,叫她别犯傻。影响不好。”张雁料到了几分,说道:“那是她自己的想法,别人也开导不了她。我的话她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崇尧道:“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张雁道:“不是没有。要她断了此念想,除非她自己放下,钟情于别人了,就不会瞎闹了。”崇尧认为有理,说道:“不知道十二弟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做主。”
张雁道:“盈盈不干,凭你怎么做主,都是惘然。”崇尧道:“她会想明白我的一片苦心的。”又觉她似有嘲讽味道,好是生气,遂说:“让我静一会。”张雁瞥了他一眼道:“黄四哥适才差人来请你去吃酒。”崇尧道:“我知道了。”张雁径自出来,嘟囔道:“一个义妹的终身,愁成你那个样子。”
崇尧乘马径自去找尚基,尚基简良接他进了营寨。酒肴早已备好,尚基道:“八弟,我们兄弟好久没有一块吃酒了,难得相聚。今日不醉不归。”简良道:“是啊。八哥,想想我们在苏州义结金兰,兄弟七人。到如今徐大哥,杨五哥,七弟霍演都跟随郭子仪在关中作战。六哥又追随李光弼将军在太原同叛军鏖战。我们兄弟各奔东西,想要聚在一起,好难哩。”崇尧听了,不胜感伤,说道:“叛军终有覆灭的一天,相聚之期不会太久。”坐下来,说道:“薛嵩乃是叛军中的智将,四哥能够打退他的进攻,着实不易。来,我敬四哥,十三弟一杯。”尚基,简良举杯道:“干了。”三人昂头喝干了。简良又给他们满上,说道:“八哥在潞州一仗打得实在好。王将军还封赏八哥做了泽州兵马使,这是我们兄弟何等的荣耀啊。”崇尧道:“不过是个临时的。打完仗之后,我也不想做官,就跟兄弟们都去过安稳日子。”
尚基道:“只怕徐三哥跟十二弟不是这么想的。”崇尧道:“人各有志,莫管他罢。我们吃酒。”简良道:“八哥,我敬你一杯。我是打从心眼里敬服八哥,当日若不是你同徐三哥,冒死从牢狱中搭救了我。这条命都早没了。”崇尧道:“说这些往事作甚?”简良道:“从那时起,我这条命就是八哥的,只要你一句话,刀山火海,绝不皱一下眉头。”先干为敬,将一杯酒一口喝干。崇尧道声:“十三弟,言重了。”喝了酒。三人忆往昔今,畅谈夙愿,开怀畅饮,直至深夜。尚基,简良东倒西歪,兀自要跟崇尧拼酒。崇尧摇晃的推他们去睡,到了尚基卧房,三个扭成一团,倒在一张床上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次日巳时了。尚基早已去前方查看岗哨了,简良尚未醒。
宝应闻报说路登云一伙同一个贼将行事鬼祟的望西而去,好觉古怪,遂来找崇尧商量。不见崇尧,问起张雁,说是昨日尚基约去吃酒,一晚未归,或许留宿在老缥军营了。宝应差朝玉来传唤。崇尧听得外面呼唤,摸着沉闷的头,踱出来。朝玉便说了探子的信息。崇尧心道:“冰天雪地,他们几个不在洛阳享清福,却跑这远路,定然有鬼。”同朝玉来中军见宝应。宝应道:“安贼视他几个如心腹,不是重大的事不会教他们去做。八弟,你看这个,是不是派一队人去查看究竟?”崇尧道:“安贼不见兔子不撒鹰,我们一定要弄个明白。可是他们轻装前去,脚程很快,已是走了几日,怕是赶他不上。”朝玉道:“还有一种可能,这个不会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罢。”崇尧摇头道:“应该不会。我们舜王坪防守严密,又是隆冬腊月,薛嵩跟安忠志虽然合兵一处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时候进兵,论天时地利都对他们不利。”
宝应道:“八弟想怎么做?”崇尧道:“事不宜迟。我同六哥率领飞鹰队十个骑术精熟的兄弟追赶,星夜兼程,或许能够赶上。我们暗中看他动静,再作区处。”宝应道:“八弟是否想伺机杀了他们几个。”崇尧道:“他们屡屡跟我舜王坪作对,一日不死,祸害无穷。”宝应遂传唤得晗来,吩咐了。得晗立即召来一百多精心锻炼的兄弟,挑选了十个骑**湛,武艺高强的兄弟,悬弓佩剑,结束停当,乘马下山。崇尧,得晗同十个兄弟伪装成叛军,望西急追,一直赶过了潼关。
从贼兵口中得知路登云等一伙人进了长安。崇尧便同得晗等人驻足在城外客栈,见几个贼兵头目吃酒,径自去搭讪,谎称是洛阳来公干的,就问长安可有甚新闻。那几个头目见他几个出手阔绰,还要为他们结账,十分欢喜,说起有一伙武师前日来到长安,很是招摇放肆。将帅都很奉承他们,争相宴请。今日在安守志府邸跟安守志,安守忠等叛将纵酒狂欢。再问他们所谈何事,那几个头目也答不上来,只说:“高嵩将军是皇上心腹,是一起来的。”崇尧,得晗心知就是他们了。
如此捱延两日,登云,山翁等人方才同那个敌将动身登程。崇尧同得晗出城约了兄弟们商量。兄弟们多听的叛军同郭子仪对峙相持不下的事,说道:“我军缺乏战马跟能够冲锋破阵的铁骑,所以攻打叛军屡屡受挫。新皇已经命仆固怀恩和李承穿出使回纥借兵,前方暂且息兵罢战了。”得晗道:“安贼在关中布置了十多万兵马,还有安守忠,李归仁,崔乾等悍将,形势严峻。如果借不来精锐骑兵,来年反攻长安,胜败难料啊。”崇尧道:“毕竟不知道路登云一伙意欲何为。我们不能就这么回舜王坪罢。”得晗道:“当然要去看个究竟了,或许有机会杀了他们。”十数人乘马尾随数日,径直过了叛军控制范围。
路登云一伙行事愈为隐蔽,每到晚间赶路,白日休息。崇尧道:“他们向来天不怕地不怕,怎么到这么谨慎起来。”又问前面是什么去处。得晗道:“好像是大震关了。”崇尧道:“我们赶在他们前面到大震关,禀告长官截住他们。”得晗道:“八弟果决,我们就这么办。”于是一行人乘着登云一伙白日住宿,快马疾行赶在他们前面到了大震关。
黄昏时分,崇尧等人到了城门下,喊道:“快请长官开门,我等有急事禀报。”守军见了他们十数人,装扮不似商贩布衣之辈,怀疑是贼兵探子,便教放箭。崇尧,得晗慌忙拔出刀剑拨开,叫道:“我们是唐兵,望勿见疑。”守兵叫道:“我们郭长官,明令禁止,入夜不得私自放人出入,以防贼兵偷袭。不管你们是不是细作,等到明日来罢。”崇尧道:“我们着实有要事禀报,耽误不得。还请通禀一二,必有重谢。”守兵骂道:“大胆贼人,胆敢赚我城门,不要啰唣,送你上路。”便教放箭。这一番箭如雨下,射的崇尧,得晗跟兄弟们抵挡不迭,叫苦道:“恁麽厉害。”直向后退了一箭之地。
崇尧望着月亮升起,星光点点,说道:“这可不是办法。路登云一伙来了,见到我们,事情就露馅了,还有性命之忧。”得晗道:“我们打他的埋伏。”崇尧道:“就我们这几个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这样,我先进去,见了郭长官,说明身份来意,一定放我们入城。”得晗道:“八弟,小心点。”崇尧别过他们,溜到城墙下,展开轻身功夫,掠上城头。只见那数十个守兵在城楼内向火烧烤,兀自咒骂:“贼兵不看这是啥地方,也敢来贿赂,赚门。待会禀报了长官,拿了这几个贼细作。”一个说:“长官睡了,莫打扰他了。我看他们走了,不会再来了。守在城下,这一晚不冻死他们。”崇尧径自溜下城去,但见城内清冷,街坊寂静,整肃非常。又不知守将府邸在哪个方向,刚走几步,听得脚步声响,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上百兵将。
崇尧倒吃一惊,来不及分辨,便教一索捆翻拿了。几个兵将说道:“这贼好大胆,只身敢来作怪。推他去见郭长官,不扒了他的皮。”一干将官你一推我一?,簇拥着他来见郭长官。进了府衙,直至公堂上。那个长官早闻的报告,穿了官服,高坐堂上,一拍惊堂木,说道:“大胆细作,如何进了我戒备森严的大震关,有何图谋,细细说来。如不从实招承,大刑伺候。”崇尧见那长官威仪庄严,一身正气,好生钦敬,说道:“我不是细作,乃是唐将。”那个长官亦是见崇尧仪表堂堂,敦厚诚实,不似贼兵细作,乍见他这般说,便问:“你说是唐将,却是那里将官,姓甚名谁?到此何干,为甚夤夜潜入关内?”
崇尧道:“我本追随封常清将军,封将军死后,为了保护百姓屯兵舜王坪。近来追随泽潞节度使王思礼将军从征,临时任命为泽州兵马使。前些时日,听报叛军派出路登云,燕山翁等追随安禄山的鹰犬,图谋不轨。我率领几个手下一路尾随至此,料定他们会从关下经过,便来请见长官,意欲借助长官势力将他们擒获。奈何守军不肯放我们入关,无奈之下只身翻上城墙,来见长官。只此是实,绝无虚假。”那长官道:“舜王坪我倒是听说过。守将是谁,你可知道?”崇尧见他盘诘,答道:“吕崇尧。”长官又问:“那你是谁?”崇尧道:“在下便是。”那长官惊道:“他手下有几个兄弟现在在郭大帅帐下效力,作战勇猛,你可识得?”崇尧道:“他们都是我的结拜兄弟。一个是三哥徐镜平,一个是十一弟杨亦踔,还有十四弟霍演。”
那长官欢喜道:“果然是大闹洛阳,刺杀安禄山的吕崇尧。”亲自跑下座来,为他松绑,说道:“下官郭英。有眼无珠,险些害了忠良。”崇尧道:“郭长官驭众有方,治军严整,在下由衷折服。”郭英遂吩咐左右快快开关放人进来。少时,得晗跟十个兄弟都来到官衙相见了。郭英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崇尧道:“这几个人身怀绝技,武艺精熟同我们是死对头。两次打冲锋领着贼将安忠志打上舜王坪,实在不可小觑。”郭英道:“崇尧兄想要我怎么做?”崇尧道:“我想让长官截住他们,在这里将他们剿杀。”得晗道:“他们的本领我也是见识过的,虽说可以仗着人多势众困住他们,可是想要一举剿杀,着实不易。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图谋,还是先搞清楚,挫败了他们阴谋,才是正理。”郭英闻言,已是有了主意,便向崇尧,得晗这般这般,套出他的话来,然后再处说了。崇尧喜道:“妙极。”
却说路登云,燕山翁一伙早已打听清楚,这里不比别处,没有郭英批的通关文书,是不可能过了大震关的。于是决定拜访郭英,虚与委蛇,有了批文,即可过关。入夜,来到关下,诈称是大帅郭子仪派来公干的军爷。城头上的守军闻听,早是得了长官言语,稍加盘诘,即便放他们进关。登云一伙全然不疑有他,直至府衙呈上拜帖。登云说:“我们就这么去见郭英,未免教他瞧出破绽。”高嵩说:“雷大哥倒像是官府中人,不会引起郭英的怀疑。”燕山翁便说:“那就有劳雷老弟一趟了,可莫要露出马脚,坏了大事不是耍子。”雷钧遂说:“各位只在此地静候佳音罢。”遂同高嵩去见郭英,取讨批文。
郭英待到堂官引来高嵩以及雷钧,坐下,茶罢。郭英问道:“郭大帅有甚公干教你等去,可有郭大帅的手谕?”高嵩道:“手谕到没有,只是有一句口谕,事关机密,实在不好说的。”郭英道:“你们是郭大帅的心腹,可知道大帅受过甚人大恩麽?”高嵩道:“新皇封大帅管天下兵马,皇恩浩荡,这不是大恩麽?”郭英道:“本官说的是年轻时候的事。”高嵩,雷钧想来想去,实在不知道郭子仪年轻时候的事,暗暗埋怨没有仔细向别人请教个明白。郭英见他两答不上来,拍案道:“谁人不知大帅曾经受过谪仙人李白的恩惠,偏偏你们不知道,还想哄骗我么?”高嵩慌忙说道:“啊呀,真是。青莲居士李太白就是大帅的大恩人啊。一时没想起来哩。”郭英冷笑罢,喝教左右将他两拿下。雷钧怒道:“谁敢拿我?”左右见他神威凛凛,都吓得止步不前。
高嵩说道:“郭大人,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唐廷兵微将寡,朝不保夕,何不早谋生路。”郭英似有所思的挥挥手,屏退左右,说道:“这么说两位是大燕皇帝派来的使者。”高嵩不知是诈,说道:“正是。我叫高嵩,乃是大燕皇帝帐下的将军。这位是河北铁拳雷钧,武艺高强,天下少有敌手。”郭英佯作钦敬地说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实不相瞒,下官早就厌恶了唐廷尔虞我诈的那一套,赏罚不明,贤愚不辨,致使我只做了个大震关使。二位此来,对我一定有所好处。”高嵩道:“大人既有此心,何愁没有富贵?”郭英便问:“两位要下官做点什么?”高嵩道:“放我们过关。”郭英惊讶道:“过关去做甚?那里可都是唐廷控制的腹地了,一个不慎就会有杀身之祸。你们可以就此回去,打到城下,我自会开关迎降,何须犯险。”
高嵩同雷钧互望一眼,雷钧道:“大人只管批了文书,开关送我们过去,别的莫管了。”郭英道:“也罢。这就给你们放行。”又一想,说道:“今日天晚,天寒地冻,不好走路。二位远来,教下官略尽地主之谊,明日一早放你们过关,不知意下如何?”高嵩高兴道:“盛情难却,那就叨扰了。”郭英便教安排酒肴饭馔。雷钧道:“府外还有我们几个同道,请他们一起来,再好不过了。”郭英道:“哦,还有几位好汉,那就快快叫进来。”差人去传唤。登云,山翁,裴宽,莫南,不渝五个都进来相见了。郭英惊叹道:“各位豪杰大驾光临我这偏远小城,实乃蓬荜生辉啊。”登云,山翁等人见他竭力奉承,热情款待,放松戒备,开怀饮宴。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郭英吐着酒气,咒骂朝廷无道,残害忠良,致使两员纵横西域的名将冤死于宦官边令诚手中,说道:“这样的昏君,谁人肯为他卖命,倒不如反了。”高嵩道:“我等过关去,就是奉了燕皇帝之命,带了诏书劝服陇右,河西将士反唐,事成之后,我主跟他们瓜分唐地。”郭英笑道:“好极,好极。这封诏书在何处啊?”高嵩道:“就在我身边哩。”郭英得了实信,起身谎称解手,到了外厢,便向崇尧,得晗说了。崇尧道:“乘他不备,来个瓮中捉鳖罢。”
郭英点起三百刀斧手,两百惯射的弓马手,将他们房间围个水泄不通。登云等人吃的半酣,猛然觉察到窗外刀光隐隐,叫声:“不好。郭英诓骗我们耶。”高嵩道:“莫错了,郭英坦诚相待,不会杀人。”话刚出口,就见一支箭射了进来,差点射到面上。一干人惊得魂飞魄散,伏倒在地上,叫道:“郭英,你不想要富贵了麽?”郭英答道:“我而今乃是大震关使,已经够富贵了。”呼叫放箭。利箭飕飕直射入房中,钉的满桌子都是。登云怒道:“鸟官,竟敢扯着弥天大谎哄骗我们。”搬起桌子挡住箭雨,破窗而出。莫南,不渝随后紧跟跳了出去同刀斧手厮杀起来。燕山翁见窗外上百弓弩手张弓搭箭对准了房内,心念一动,纵身而起,径自从屋顶突出,站在屋顶用瓦击伤数十名弓弩手。
雷钧,裴宽保护着高嵩夺门而出,撞见了崇尧,得晗。雷钧骂道:“阴魂不散,又是你作祟。早知今日,当日就该一刀杀了你。”崇尧道:“你们恶贯满盈,早该伏法了。”同得晗领着十个飞鹰队兄弟,仗了刀剑击杀他三人。打斗间,得晗抬腿将高嵩踢倒,两个兄弟上前将他绑了,搜出安禄山诏书以及诱降河西,陇右将士的书信。高嵩叫道:“救我,救我。”裴宽见大势已去,走的慢了,还有性命之忧,遂踊身窜上房坡。雷钧教崇尧缠住,脱身不得。得晗教兄弟们放箭,雷钧闪了几下,应接不暇,一个眼慢被射中。山翁欲来解救,却见乱箭如雨射雷钧,连中数箭,目眦欲裂的盯着崇尧,扑地而倒,已然不能活了。山翁道一声:“吕崇尧,这笔账必然要跟你清算。”说罢,转瞬不见。
登云,莫南,不渝三个拼死力战,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府衙,扬长而去。郭英见他们几个能够从这么严密的封锁下脱身,着实惊讶,传命快快追赶。满城兵马追击,到了东门,只见他们杀了守门兵将,开了门溜了出去。赶了一程,追他不上,便收兵回来。崇尧道:“高嵩跟这诱降诏书,书信就由郭长官交付朝廷罢。我们就此一别,他日有缘再会。”望着死了的雷钧,说道:“这个雷钧乃是有名的拳师,一步走错,致有今日。将他厚葬了罢。”郭英道:“此人着实威猛,误交匪类,死于异乡,令人扼腕。来日,我命人将他厚葬便是。”
崇尧遂同得晗领十个飞鹰队兄弟快马急追。赶到天亮,崇尧等人追了上来。原来裴宽腿上负箭,疼痛难忍,马背上颠簸使得腿上箭伤处流血不止。山翁怕他落单,只顾照管他,走的慢了。裴宽听得身后马蹄声急,叫道:“老兄快走,莫管我了。”山翁道:“我们跟他拼了。”调转马头就要截住崇尧厮杀。裴宽拽住他,说道:“雷大哥死了,我有何面目独回老家。我的妹妹心语寄寓洛阳,烦请老兄照顾,待到时局安定了送她回老家,感恩不浅。”山翁道:“一起来便一起回去,莫说丧气话。”裴宽滚落马背,凄然堕泪道:“吕崇尧是一定要我们死而后甘心。路登云他们不仗义,老兄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陪我走到这里,已是难得了。我来抵挡他们一阵,家妹就拜托老兄了。”山翁蹙眉,说道:“裴兄弟说哪里话。也罢,心语就交给我了。”纵马疾驰而去。
崇尧,得晗追到林中,却见裴宽坐在树下,问道:“他们呢?”裴宽道:“他们去搬救兵了,你们还不走?”得晗跳下马背,径自过来,拽住他的胳臂提了起来。裴宽右腿上的箭还没有拔出,鲜血迸流,疼的站立不住,叫道:“有种就杀了我。”得晗道:“来啊,将他吊死,就暴尸在这里,喂狼罢。”崇尧见两个兄弟就张罗绳索要套在他的脖子上,将裴宽吊死,好生不忍,说道:“这个人是个有血性的,不要难为他了。留他一命,或许有用。”教将他腿上的箭拔出,敷了草药,止了血。裴宽道:“我们是死敌,不用你假仁假义救我。”崇尧道:“我知道你是身不由己,迫于无奈才委身事贼。想想你的妹妹,孤苦伶仃,浮萍一般流落异乡。你死了她怎么办?”裴宽眼中纷纷落泪。
得晗虽然不甚高兴,可是也没办法,只得由崇尧。崇尧延医为裴宽用药医治。崇尧认为登云,山翁一伙不会就此善罢,定然在归路上设伏。得晗道:“我们只有绕过了叛军的控制区域,才能到舜王坪。”两人商议一下,决定走洛河到龙门一路,过了黄河然后南下舜王坪。至此一行人冒着鹅毛般大雪,凛冽的寒风,晓行夜宿走了数日。到了洛水,踏冰而过。只听一人笑道:“教我等的好苦。”众人急睁眼看时,叫声苦。燕山翁道:“哥几个分头阻截你们,却教我逮着了。这场功劳,还是我的。”崇尧道:“我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甚要咄咄逼人呢?”山翁道:“说什么仇恨,你我各为其主罢了。”望见裴宽端坐马背之上,还活着,腿上的伤大有好转,说道:“吕崇尧,你也是个汉子。这样吧,你放了他,我放你走。”
崇尧道:“我的兄弟们呢?”山翁道:“一个换一个,哪那么多废话,啰里啰嗦的,不换就算了。你们一个都别想走。”得晗怒道:“休要猖狂。”喝教放箭。十个兄弟张弓搭箭瞄准了山翁。山翁道:“尽管放马过来。”十个飞鹰队兄弟互望一眼,分上中下三路,放箭射将过去。只见那山翁龙腾虎跃,迎着劲风锐利的利箭,双手连抓,居然将十支箭都抓在手中。得晗忙命再放,十个兄弟次第放箭,连珠价似得射去。山翁辗转腾挪,矫健敏捷的躲过多时。十个兄弟身边带的箭就要射完,不自觉都住了手,掌心中都是汗。山翁嘿嘿道:“你们射完了,该轮到我了。”双手并掷,手中那十支羽箭破风而来。崇尧道声:“快闪。”两个兄弟闪的慢了,教羽箭掼胸而过,倒栽下马,一命呜呼。
得晗大恸道:“兄弟。”向着山翁道:“我跟你拼了。”纵马扬刀疾驰过去。另八个兄弟都拔出身边佩剑踏雪冲杀过去。裴宽想要开溜,崇尧一把拉住他的缰绳,说道:“我还没说放你走。”裴宽道:“我走了,你们就脱险了。”崇尧道:“我从不受人威胁。”裴宽道:“我教他罢手。”崇尧道:“他肯么?”裴宽喊道:“燕老兄,住手。”山翁打的兴起,听言抬头,说道:“我打杀他们,就来救你。”裴宽道:“大行门门主大仁大义,不会为难我的。”山翁道:“你好糊涂啊。他们没有脱险还要你做人质,一旦脱险立马翻脸不认人。莫要受他骗了。”裴宽道:“燕老兄,罢手罢。”
山翁哪里听得进他的话,只顾打。得晗跟八个兄弟团团围困,转轮般厮杀,溅起雪花漫舞。山翁虎吼连连,咆哮着,就像是一头饿了几天的狮子,又像是一个八臂金刚,双手抵住九件兵刃,好是神勇。得晗同兄弟们跟他打斗多时,耗得山翁筋疲力尽,吼叫一声道:“你们等着。”踢起一片雪,打翻两个兄弟,夺路而走,跑进了林子中。得晗道:“我们快走,不要等他搬来救兵,走都迟了。”崇尧道:“这两个兄弟尸体,掩埋了罢。”得晗道:“自有地方上料理,顾不得了。”招呼兄弟们上马。刚走不上一箭之地,只听一声:“小贼,不要走。”众人吃一惊,回头望时,只见燕山翁坐在马背之上,手中提着一口九尺余长的宣花大斧,甚是威武。
得晗道:“这厮要与我们厮杀到底了。”崇尧道:“你们带着裴宽先走,我来抵挡一阵。”得晗道:“八弟,小心点。”径自同兄弟们挟持着裴宽去了。崇尧拍马踅回来,说道:“真要赶尽杀绝么?”山翁道:“我要拿你去洛阳。”纵马驰来,抡起大斧便迎头砍落。崇尧坐骑受惊,前蹄扬起,斧头落空,料势不能抗,纵马便走。山翁道:“不要跑。”甩动缰绳,紧紧追赶。崇尧跑不掉,又回马再战。山翁大斧横劈过来,崇尧以刀格架,禁不住震得虎口裂开,刀也落到了雪地中。吓的心惊肉跳,纵马疾驰。山翁纵马提斧追赶,叫道:“跑什么,跑到天边,怕追不上你。”崇尧怕他追上得晗,遂纵马望西直过了洛水。山翁纵马呐喊:“站住。”不顾深浅,只管追,没成想崇尧纵马踏冰过去,已然冰层裂开缝隙。
山翁身重又提了数十斤重的萱花大斧,不提防冰层爆裂,咣啷咚的连人带马跌入洛水河中。崇尧回身望着在河中挣扎扑腾的山翁,恍疑是在做梦。崇尧看着不忍,想要搭救于他,却听得传来马蹄声,莫南道:“咦。吕崇尧你却在这里。”仗剑来杀,又发现了河中的山翁,叫道:“好个吕崇尧,打不过就推人下水,这也忒损了点。山翁,我救你上来。”崇尧纵马度过冰河,驰了一程,回头望见莫南正在搭救山翁,遂放心离去。走到晚间,追上了得晗,将上项事说了。得晗笑道:“这就叫自作自受,可知门主是不该死的。”一行人都笑山翁英雄一世,到此做了个落汤鸡。
到了龙门,投客栈住宿。入夜,听得住客们叫喊:“杀人了,杀人了。”崇尧被喧闹声惊醒,提了刀出了房门,望见客栈住客多跑光了。老板跟伙计都被杀死,血流满地。得晗跟八个兄弟出来看,正见路登云,宫不渝两个闪了出来。崇尧道:“是你们?”登云背上负着旷夫刀,手中提着剑,说道:“倒要看你过不过得了这个龙门。”不渝道:“你害的燕山翁好苦,重病缠身,还得我二师兄端汤喂药。”崇尧道:“你们要杀的人是我,为甚要滥杀无辜?”不渝道:“谁叫他们不老实,不说你住在这里,死了活该。”登云道:“你是自缚请罪,还是要我们动手?”崇尧道:“六哥,你带着兄弟们快走。”得晗道:“要走一起走,我们结拜的时候,说要生死与共的。”崇尧道:“好兄弟。我们一起上。”便教两个兄弟带着裴宽从后窗走。两个兄弟挟持了裴宽径自去了。登云见状,教不渝去追。
崇尧纵身扑来,挥刀截住不渝厮杀。得晗同六个兄弟仗剑来杀登云。一时间客栈刀光剑影,杀气磅薄,打的木屑横飞,碗碟乱跳。登云剑法精妙,飞龙舞凤似得,杀得得晗跟兄弟们手忙脚乱,神魂欲飞。杀了数合,两个兄弟命丧登云剑下。有两个兄弟跳出圈子,张弓搭箭射登云,都教登云眼光锐利,身手矫健的闪过,怒道:“敢放暗箭伤人。”纵身而起,几个起落赶上将他两个杀了。登云便来杀他三个。崇尧打的不渝无还手之力,东奔西走,窜入了厨房,将东西乱砸崇尧,叫道:“大师兄救我。”登云闻言,顾不得杀得晗等人,赶来厮杀。不渝跟登云两个打一个困住崇尧,脱身不得。那两个兄弟想去相助,得晗止住道:“跟我来。”三人便在客栈放起火来,待到登云等人发觉,火势蔓延,已将整个客栈包在烟火之中。
登云惊慌:“贼子要放火烧死我们耶。”舍了崇尧径来杀得晗等人。得晗同两个兄弟跳出火海,在客栈外张弓搭箭伺候,登云被箭射回,几番冲突不出,手臂上吃了一箭,着实疼痛。又听得不渝怪叫不已,折回来杀崇尧,只见整个房间都是火,烟尘弥漫,分不清敌我。崇尧道:“路登云杀我兄弟,我跟你同归于尽。”烟尘中窜将出来,抱住登云扑向火海。登云惶急,倾尽全力将他推开,滚在一边,兀自心惊肉跳。得晗等人喊道:“八弟,快出来啊。”崇尧听得他们呼喊,神志清醒,用刀挑开着火的物件,窜出了熊熊烈火。
登云听得不渝还在凄厉的呼救,急忙跑进去,见他双手捂面着地乱滚,只是喊:“烧死我了,我的脸。”顾不得他伤重伤轻,抱起来就跑,钻出火海。崇尧等人早已不知去向,一座客栈少顷被烧成废墟。登云看着昏死的不渝,脸上被烧伤,不成模样,不禁怒气冲天,嘶声竭力的叫道:“吕崇尧,我跟你没完。”
崇尧,得晗等人与裴宽等人相见了。那两个兄弟见只有他四人回来,知道死了四个兄弟,不胜伤感,都挥拳乱打裴宽,咒骂:“都是为了你,害我们一路被追杀。打死你算了。”崇尧制止道:“打死他,难道就能让他们活过来么?”得晗道:“我们留着他要做什么?”崇尧道:“回到舜王坪再说。”得晗拉过崇尧一边,说道:“八弟向来有主张,究竟留着他有甚用处?实对我说。”崇尧道:“六弟一定要知道个所以然,我就说给你听。这两天忽然想起,十二弟的妹妹被贼兵扣押在了洛阳,我想用他换回十二弟的妹妹。”得晗诧异道:“十二弟的妹妹,怎么会落到叛军手中?”崇尧道:“前不久的事。十二弟的妹妹就是你我的妹妹。我们岂能坐视不救,教十二弟怪怨我们没有尽到做兄弟的本分。”只怕有毁她的名洁,缄口不提她在晋王府的事。
得晗道:“叛军能够答应么?”崇尧道:“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不管怎么说燕山翁跟裴宽相交甚密,不会见死不救,一定会从中斡旋,作成此事。”得晗道:“那么这样,我们且不回舜王坪,就在山下完成此事,不会引起舜王坪将士的阻挠。他们都对裴宽恨之入骨,如果回去宣扬出去,反会坏事。还有我们向叛军送去书信,只称白姑娘是一般士卒的妹妹,叛军不换的话,就会激起山翁等人的不满。那时就有了几分把握。”
一行人来到闻喜,早有人报知县令。县令见他们抓了一员贼兵头目,倒像是大有来头,不敢怠慢,便教他们在馆驿安置,不在话下。崇尧教得晗写封书信,大意就是说恪卿是一个士卒的妹妹,要想教放回裴宽,便要将白恪卿来交换,要他们兄妹团圆。得晗唤过两个兄弟,如此这般的说了,问道:“敢去么?”那两人说道:“死都不怕,还怕送封信?”得晗道:“虽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叛军未必会说理,弄不好就是有去无回。”两人道:“死就死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得晗道声好,吩咐道:“务必交到晋王手上。”两人接过书信,出了馆驿,乘马径自去了。
两人路上遇上了叛军盘查的关卡,好是大胆,直言相告说是舜王坪派来向晋王送呈书信的。路上叛军见他们说话恁麽理直气壮,要见晋王,故而一路没人敢予以阻拦,一路顺风进了洛阳。晋王闻听此事,说道:“难不成舜王坪打不过,要降麽?”似觉不像。又听说了山翁等人惨败回来,高嵩被大震关使擒获,雷钧中计而死,裴宽吃教捉了,宫不渝脸上被烧得毁了容,皇帝震怒,大发雷霆,指责他们办事不力,吓的他们几个躲在家中,不敢出来。遂想道:“难道是为这件事上?”恪卿听得说舜王坪派来使者,想起裴宽一事,到猜想到了几分,六神无主的想道:“吕大哥想要换人,可不是一番痴想。安庆绪如何肯放我走。”心中怀恨,转念又想就这么走了,岂不是便宜了安家。
庆绪见说使者已经到了门外,请求相见,便教进来,故意使张氏兄弟站立两侧,左右站数十个刀斧手。他坐在大殿之上,好像接见大国使节一般庄严气派。两个昂首阔步进来,直至阶前,唱个喏。左右喝道:“见了晋王,还不下跪行礼,恁麽无理。”一个道:“我们是唐兵,你是反寇。我们是传递书信的,不是你们贼寇见了主子就要下跪。”左右叫:“讨打。拉下去。”庆绪喝道:“谁教你们打他了。”左右忙说:“不敢。”庆绪说:“那个叫什么吕崇尧的是吧,是他叫你们来的么?”两个说:“正是。”庆绪道:“他有甚话说?”一个说:“我们不知道,只在信里。”庆绪便教拿上来,张衮走下来,接过书信,递给庆绪。
庆绪打开书信,一目十行的看了,勃然大怒道:“混账,混账。吕崇尧忒大胆,要我的王妃。”张氏兄弟甚是惊异,寻思:“这是怎么说?”殿上那些刀斧手个个纳起闷来,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庆绪见他们神色异样,说道:“哦,他们说裴宽在他们手上,要我的王妃白恪卿去交换,要王妃同他的哥哥团聚。”张骥感觉蹊跷,说道:“王妃的哥哥是谁,信中可曾提到?”庆绪道:“是一个普通士卒,没说名字。”气得脸色铁青,咬牙道:“王妃跟我情投意合,恩爱有加。区区一个裴宽,值得我要用王妃去换。”张衮道:“毕竟裴宽是为王爷父子办事的,忠心耿耿,这么说恐怕寒了大伙的心。”
庆绪怒道:“你舍得拿自己的老婆去换别人的性命么?”张衮道:“殿下也知道我的妻子死了十多年了。”庆绪瞥了他一眼,冷哼一声道:“轰他们出去。”起身便走。那两个兄弟兀自叫嚷:“换是不换啊。”左右乱棍来打,两个忙说:“不用赶我们,自己会走。”出了晋王府。正好遇上山翁,吓了一跳。山翁道:“你们两可是来投书信的。”答道:“正是。”山翁道:“信上怎么说,晋王怎么回覆?”两个将上项事说了,答道:“晋王不肯换人。”山翁骂道:“岂有此理。我们为他安家卖命,眼看着见死不救。珍惜一个女人,取败之道。雷钧死的不值啊。”教他两暂且住下,便来见庆绪。
庆绪来到后堂,恪卿问起来,便如实说了。恪卿闻言,啜泣道:“妾身自从成了殿下的女人,就没想着要离开。俗话说一女不适二夫,若要我离开殿下,除非一死。”庆绪道:“可是你哥哥在舜王坪上哩,你不想他。”恪卿道:“想他作甚。他是他我是我,我总是不能跟他过日子吧。殿下是我的丈夫,我哪儿也不去。”庆绪好是感动,抱住她说道:“我也舍不得你。就教吕崇尧杀了裴宽,不算什么,谁要敢再多嘴,本王绝不饶他。”恪卿本是才女,遭此磨难,着实痛恨庆绪,毁了她的一生,遂展生平才情吹弹歌舞,论诗谈文,博取庆绪好感,枕席之间曲意逢迎,倾身伺候,哄得庆绪爱她如同珍宝,言听计从,倒把正室王妃抛撇在一边,好像被打入冷宫一般。故而要庆绪将她换人,那是一百个不愿意。恪卿道:“我好怕有一天连你也保不了我。”庆绪一怔道:“为甚这么说?谁有这个胆子害你?”
恪卿泣道:“你的父皇前些日子追查将官有没有美色进贡,大发脾气,杀了几个贴身宫女呢。我原本是将官敬献你父皇的,被殿下中途截下,带到晋王府。这件事一旦东窗事发,殿下是他的儿子,或许不会治罪,可是妾身怕是要去伺候你的父皇,妾身是宁死不从,也要保全贞洁。一死倒也罢了,殿下这张脸可往哪放啊?”庆绪变色道:“他敢。”恪卿拭泪道:“你果真不怕么?”庆绪神情恍惚的坐下,想着近来的事,寻思:“父皇宠幸段氏,生下庆恩,早就想废了我,立庆恩为太子。严庄教我早做打算,事到如今,豁出去了。不是他就是我。”咬牙切齿地喃喃道:“这个老不死的。”
恪卿见他眼神中露出凶光,似已拿定了主意,暗暗欢喜:“早就听说他不受安禄山待见。叛军势力蔓延,大有扩张之势,如果此时教他父子相残,定然会使得他们内部分崩离析,锐气受挫。唐兵反击的时候就到了。”庆绪抚着她的头道:“我不会让你回到父皇身边的。你是我的,谁也休想动你一根手指头。”倏听外面张氏兄弟说道:“燕山翁求见晋王。”庆绪道:“爱妃,我去去就来。”出来见山翁跪在地上,说道:“老师是大燕国的勇士,为甚行此大礼?”
山翁道:“老夫恳请殿下将她交给使者,我同他们一道去好歹换回裴宽,为殿下效忠,万死不辞。”庆绪不听则以,一听这话,怒火中烧,抬脚将他踹翻,骂道:“老匹夫,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再说一句,就将你斩了。”山翁道:“殿下息怒。裴宽追随皇上十年,劳苦功高,雷钧身死异乡。若是殿下舍不得一个女子,而使裴宽死在唐兵手上,将士们会寒心的。”张氏兄弟亦说恪卿原乃是将官进献皇上的,不合将她抢来,尊为王妃。为此事恐怕好事者抓住把柄,造谣生事,传到皇帝耳中,为祸不小。庆绪便说:“王妃的哥哥尚在唐营,只看王妃愿也不愿?”唤来恪卿。恪卿便跪下,泪流满面的说:“要我去唐营受辱,到不如就此死在殿下面前,以谢殿下恩情。”就要撞墙自尽。慌得庆绪将她拦住,说道:“本王知道你深爱着我,跟你闹着玩,就当真了。我不会用你去换人的。”
恪卿就骂山翁,说道:“你要救你的兄弟,成全你仗义的名声。却要教殿下背负一个始乱终弃的骂名,教人耻笑为了救人,无计可施用女人交换。传扬出去,殿下何以君临天下?”连哭带骂,吓的山翁跪着不敢抬头,兀自落泪:“老匹夫,没能耐救人,就打我的主意。殿下绝不受你等狗奴才蛊惑。”庆绪道:“可听到了。你有本事自己救人去,别来羞辱我的爱妃,惹她生气。去罢。”山翁受了一顿辱骂,好生羞惭气愤,起身就走。张氏兄弟自觉没趣,悄悄退了出去。庆绪做好做歉,百般哄劝,恪卿方始住了哭。恪卿说:“为甚不把这个老狗千刀万剐?”庆绪道:“他还有用,杀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