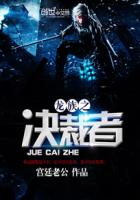一叶扁舟几经飘转,消息很明确,这富陵湖的水贼比前几日少了八成,除了部分是被徐县官军剿灭,剩下的都死于内讧。
曾有人见到数十艘蒙冲夺了一艘楼船上面满载的货物,连带着船跟人,一起带走,消失在水平面上。
没人知晓这支水贼的来历,只觉得船头站立的人眼熟,大抵是富陵湖水贼的一支。
花费掉了祖茂分润的铜钱,书童不甘心就这样终结,不想让主人看到自己无能的一面。
他依旧在寻找,在富陵湖上寻找着那支水贼的下落。
自嘉平月至今,细细数来不过三十七日,今天是二月初六,春天即将到来,野鸭在湖面摇曳,见了被称作“扁舟”的小船,便振翅而非,它的声音远远没有它的肉美味,一点也不动听。
大约时午时,船夫耐烦又不耐烦的坐在船舷上,丝毫不介意冰冷的湖水拍在脚上。
书童等着,那面是敌非友,亦或者是友非敌的旗子被湖风吹得猎猎,伴着湖水拍击声,一时倒不算无趣。
船夫年约三十岁,皮肤黝黑,身材精壮,戴着一顶草帽,穿着蓑衣,上船时他指着一旁那套一模一样的行头,一边絮叨:“那个……你给的钱只够两天出行的费用了,不如休息一下,我爹爹说最近几日恐怕有大雨,诺,让我给你准备的。”
船夫不识字,却也知道这人定然不是做什么好事,直到他主人出了自己无法拒绝的价钱之后,方才同意这差事。这几年,光靠打渔,日渐艰难。
大多数人眼界都在身边,长远的想法大多寄托在子嗣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说话大抵是对自己希冀生活的另类追求。
让他奇怪的是,他的主人今天没来。
就着栗米,书童填了填肚子。与庶民不同,这个时代的上层人士,已经实行三餐,而非寻常人家的二餐。
游鱼从脚下摇摇晃晃的离去,渔夫看了见,知道这是鲫鱼。
若是盛夏,一个猛子扎进去,一手一条,他是富陵湖排得上号的渔夫,水性一流。
这时候,他顾忌已久的乌云压了过来,一朵连着一朵,没有惊雷响起,淅沥沥的雨点打在水面,船身,蓑衣上,那面是友非敌的旗帜上。
湖面上的水汽开始聚集,形成的雾气一点点扩张,吞噬白色。
书童沮丧,心想一天就这样浪费,卷起袖子,茫然的望着雨丝。
连绵不绝的雨有远有近,被风带着,翩翩飞舞。
这远远不是阳春三月的徐徐春风,那般温和,冰冷的雨丝,冷冽的湖风,还不是哭泣的时候。
忽的,有人呼道:“在这儿!”
船桨拍打湖水的声音清晰多了,黑色的蒙冲穿出湖雾,上面站着二三持刀汉子。
他们如同船夫所料,径直跳了上小船,长刀一横,诡异的打量下船上的帛,上书的字他被特意关照,恶补一番,觉得这是他要找的船。
为首一人横刀立马,将草帽推高,湿漉漉的脸上恢复平静,一边等待,一边说:“是敌非友,好大的口气!”
船夫后退一步,撇清关系,冷眼旁观这一切。
在富陵湖上讨生活的,跟水贼距离不远,简单说,水贼是渔民,船夫的另一种身份。
他们平日间胆小如鼠,并不起眼,需要时一柄环首刀,就能在水上厮杀,悍勇至极。
他见多了这些,凭着几分名气,自诩能保自己全身而退,至于雇主,人傻钱多。
书童纠正是是友非敌,而非是敌非友的时候,环首刀抵住他的喉咙,干笑之后,他举起了手。
“叫什么?”
“刘九。”
“哪儿人?”
“东海国人。”
为首的人微讶:“东海国相距千里,何以至此?”
书童答:“随主人前来,特来求见富陵湖主。”
“富陵湖主,也不怕闪了舌头。你将其找来,某家倒是要见见这富陵湖主。”
书童松了口气,看着他挪到身前环首刀,导入正题:“相传近日舟船纵横湖面,击溃数股水贼,称为富陵湖主也不失分。只是阁下行事过于大意,以至于徐县都有了消息,这可不妙。”
为首的人一怔,哭笑不得,一时猜不到这人为何而来。这般指点的话……怕是所想甚多。
“多谢”他抱拳致意,呼道:“给我拿下!”
不知何时围上来的蒙冲跳下几个大汉,一左一右,将其带上蒙冲,消失在水雾当中。
船夫凌乱的在风中归来,不曾想那些人一言不发,蓑衣斗笠草帽加身,看不到模样,凭着声音,不熟,大抵是富陵湖周遭的人,或是广陵人也不定。
船在风雨中方归,靠近码头时,临时有事的主顾站在哪儿,等了很久。
簦尚未发展成伞,后辈的佼佼者油纸伞还在未来沉睡,大概八九百年之后,油纸伞方才诞生。
作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逼,刘平看着雨滴滑落,烟雾缭绕,更加不耐烦。
他不是一个能够平心静气的人,今日祖茂从下邳归来,带着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坏的消息——太平道谋反。
太平道身份特殊,暴乱的伊始,下邳也出现太平道徒,迅速被剪除。
奈何徐州富庶,去岁大旱也没伤筋动骨,比其他州更为稳定,乱的只有琅琊国,东海国都没有乱。
祖茂得了消息,一脸兴奋的把环首刀拍在桌子上,“子才,这番恐怕有打仗可以打了。”
心思动了的刘平不太懂武人,知晓黄巾之乱是机会,却不愿意掺和。
于是乎,祖茂高谈阔论也没感染刘平,他一个劲的糊弄,赞赏。嘴巴有多甜,心里就有多不耐烦。
祖茂或许是察觉了这一点,说了很久之后,闭上了自己的嘴,送走了刘平。
刘平做事天马行空,未必可行,也未必不可行。
这便是人生。
他对主公孙坚说了很多,都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即便程德谋说了好话,而非以前那般针对,不喜。
程德谋做事还算公允,大是大非上,不会乱来。
轻叹一声,他刚才不曾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