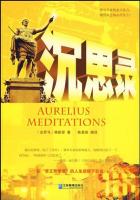半个月后,赴平阳府公干的雍亲王回府,路上孙延龄酌情向他禀告了这三个月府里的大小情况还有王妃的病况。
“把树给本王种回去!兰氏教子不当禁足三个月。”
孙延龄应了一声。他就知道,还好他已经偷偷把那株梅树给留下了。
得了禁足消息的兰氏却是瘫痪在地,那不是连过年都见不到王爷的面了,都怪这蠢儿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她忍不住捶地大哭。
赵祯步伐迈得越来越大,他不信她撑不下这一关。踏入正院,迎接他的却是丫鬟面上的悲戚惶恐,院子里站着的人反应过来是王爷回府了,刷拉拉的跪下问安。
“王爷吉祥。”六安和绿萼跪在正厅。
满室的凄苦药味冲淡了他身上携带而来的凌冽寒风,却也不由得让赵祯脚下迟疑,他突然有些怕见到她。就如承昭死的时候,他怕见她泪如雨下的模样。那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啊,是他唯一且寄予厚望的嫡子,从他出生长至七岁,所有启蒙是他一笔一划教的。
身为女子能由着心绪哭泣,她难过,他何尝不心疼?可他身为雍亲王府的主人,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怎么能倒下?他的心太大,装得事情太多。孙延龄劝他,他们如今还年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他也这样安慰自己,同样说给妻子听,她一向贤惠聪敏,定然是明白的。可她的反应却是他没有料到的,一向温谦柔谨的王妃声嘶力竭的质问。
承昭死后不到一月,东院晏侧妃在宫宴上晕倒被查出已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她知道后,在承昭的屋子里坐了一夜出来后她再也不曾单独同他说过一句话,更不曾当着他的面流过一滴泪。
他至今都还记得她凄厉又绝望的面孔,“那是我唯一的儿子,却不是王爷您唯一的儿子。”
就在两人气氛尴尬相处着的时候,父皇下了圣旨派他和六弟前往平阳府郡查访州府刺史联手在江南道一手遮天的事情。他想着等他从平阳回来,两人再好好谈谈,可是却不想面对的是她病沉沉的躺在病床,只剩下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着她还吊着一口气。
赵祯坐在床边,探了探沈瑾的额头,又摸摸她的手,然后重新捻好锦被,“叫太医进来。”
“是。”
雍亲王妃病重,英亲王远赴公干,皇帝自不会亏待了他这个儿子儿媳,派了太医院医术最好的太医驻守雍亲王府,以示恩宠。得知雍亲王传唤,很快就来了。
“微臣见过英亲王。”
“李太医,本王允你上前给王妃号脉,你准确告诉本王,王妃的状况到底如何?能不能好?”雍亲王向来冷肃,少年老成,成亲后入官场一步步历练下来,做的都是实事,在一干朝臣中威严甚重。
李太医觉得压力甚大,由着雍亲王将王妃的手从锦被中拿出,他弓腰上前诊脉,半响后才收回,斟酌着词回答,“王妃自从小世子夭折后便忧思成疾,肝脾之气淤结,不得开解,后又感染风寒,导致寒气入体,气血两亏,若好生将养倒不得碍,可那日所吐的心头血却成了王妃的致命一击,心血为心所主之血,来源于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在心气的推动下,流注全身,发挥营养和滋润作用,亦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
“说人话!”
“微臣惶恐,如今是王妃自己没有醒过来的意识,或者说是王妃不想……”醒。李太医在雍亲王的压迫下,头越来越低,后面的那个字更是直接咬在了口中。
“若本王一定要让她醒呢?”
“针灸。”李太医不喘气的吐出了下面的话,“但微臣需在百会,极泉穴,太渊,气海,曲泉,涌泉之处施针。”说完后,他都不敢看雍亲王的脸。
百会在头,极泉穴在腋窝,太渊穴在手,气海在下腹,曲泉在膝盖内侧,涌泉穴在脚底。
赵祯摩挲着沈瑾的手,沉吟半响,“施针后对王妃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李太医有些不敢相信雍亲王的决定,抬头偷觑,发现这位朝堂上的冷面亲王此刻面上流露着少见的温情,他在心中默默较量了一番,更为恭敬的回话,“气血通行,反倒有利于王妃身体的恢复。”
“那就准备施针。”
“那微臣这就回府中取针。”
“你留着。”赵祯扬声唤了孙延龄进来,“跟李太医的小厮去李府取样东西来。”
“是。”
“本王会亲自看着李太医施针,但此事还望李太医烂在心中。”赵祯动作轻缓的为沈瑾捻了捻被角,语气明明是那般的漫不经心却让人不明觉厉。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