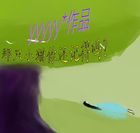四、
8月2日晴转暴雨 31℃
华源公司终于调来叉车,将三台机器运到车间的后门外。开箱后三台机器全都进了水。两台外包装损坏严重的机器,箱内倒是没有积水,但所有金属的已加工表面遇水后锈蚀严重。clean机包装箱顶板严重损坏,箱内积水达半米深。机器泡在水中的部分;外表面油漆变色,传动部分锈蚀咬死,电控箱有一半泡在雨水中。困难比朱清民预计的大得多。为了把最高的机器waste运进车间,华源陈厂长调来建筑工人,先把车间后门的门洞加高(折掉一部分),然后才把机器用叉车推进车间。由于辅助车间空间高度的限制,叉车不可能在车间内将waste机送到安装位置上。朱清民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用钢管将机器慢慢地滚送到位……。对工作中的困难,他有信心、有办法克服,但是,面对来自其他纺机厂或华源公司众多人的嘲笑、蔑视和质问,朱清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他听到最多的话是:“你们厂的机器还真像出土文物,你这个总工程师是怎么当的?……”面对同行的产品质量,朱亲民的确有无地自容的感觉。让他憋屈的是:他也无法向人解释,为什么自家的产品质量这么次!为保护自己最后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我不是总工程师!”但是,在炫耀自己贬低别人的人性嗜好面前,他的解释或否论,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朱清民在心里骂厂长、骂装配工人、骂该死的包装箱……。
8月3日阴 27℃
今天是该国的独立日,街上挂满了橙、白、绿三色旗。令朱清民不解的是,三色国旗有的横着挂,有的竖着挂,尺寸大小也十分随意,不像中国国旗有统一标准。黑人放假一天,没人来帮忙,朱清民倒无所谓。机器进了车间,工作计划由他自己掌握。一个人能够调整隔距、连接传动部分、给减速器加油;还可以将机器上的电气设备与电控柜连接起来。但是,三台机器开箱后,一寸电线都没有找到,为此,朱亲民内心着急,还不敢声张。早在袁队长到纺机厂检查产品质量时,就反复交待:“非洲条件有限,各种零配件、易损件、包括电器元件和电源线要多带一些,防备到非洲后不够用……”可是,厂里根本没钱购买。除了把一段试车用的旧电缆线放进了包装箱,什么零配件、控制线一概没带。再说,范平安一直在闹,朱亲民根本没打算来非洲,当时,也不可能主动监督执行袁队长的要求。现在,三台机器急需要需要电线安装,各种不同颜色的控制线、电源线加起来有一百多米,到哪里去找?其它厂家基本遵照袁队长的要求,带起了自己要用的东西。特别是郑纺机,自带的工具、五金件、电气元件、电线电缆、专用量具,把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堆得满满实在;从砂布、毛刷、万用表,到电钻、电锤、切割机,连调校机器水平用的专用‘楔铁’就运来一整箱,多达几十公斤。总之,应有尽有,可以开一个五金电器商店。与大厂比朱亲民感觉相形见绌,难怪大厂瞧不起小厂!前天,机器落位需要垫稳,随后还需要校水平。实在没办法,朱清民找郑纺机讨了一大堆厚、薄不等的‘楔铁’现在又讨电线?人家自己还没有开始使用呢,不可自讨没趣!
8月4日雨 28℃
上海师傅早纺机集团安装队两个月到达NIAMAY。罗师傅是上海人,他继承了上海工人特有的责任心。下大雨时,罗师傅当心grinding机包装箱进水受潮,主动联系叉车将机器移到车间内。难怪后来朱清民在露天地里找不到那箱设备。罗师傅为人坦率,第一次与朱清民见面,说话就直来直去:“朱工,别看人家叫我罗工,罗工的。其实,我就是一名普通工人。原来在厂里,我只管干活,调整机器、上工装夹具都归别人管。这次厂里裁人下岗,我才报名到非洲来。你是工程师,技术问题全指望你了,你可要帮帮我。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你尽管开口。”朱清民乐意和这种人打交道,他也喜欢直来直去。
得益于罗师傅的责任心,grinding机开箱后,机器保存完好。这台机器的电控箱安装在机身上,只需要把电源接上就行。罗师傅找来负责送电的上海师傅冯工。冯工与罗师傅是两种类型的人,为人刁钻,但对女士十分殷勤,对男士则吹毛求疵;一会儿说吸尘器与主机不能供一个配电箱,一会儿又说电缆线应该自带,反正就是不肯接电源。冯工离开后,罗师傅爽快地对朱清民说:“你不用着急,这事我帮你解决。”随后将带朱清民来到华源仓库,找保管员田师傅。按说在仓库领东西,需要华源公司的陈厂长签字。不过,罗师傅知道田师傅也是H省人,走进仓库,就把关系拉上了:“田师傅,阿拉今天给侬带来一位老乡,朱清民,朱工。”把朱清民推介给田师傅。田师傅是华源公司首批招聘到NIAMAY的员工,在国外时间长了,人的性格会变,变得看重乡情。田师傅伸出手来与朱清民紧紧握在一起:“H省的?”朱清民:“H省JS市。”田师傅:“我是省城人,下乡后招工到合肥工作……是华源公司最开始派到非洲来的员工。”听说朱清民刚到非洲不久,田师傅马上向他打听国内情况。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电视节目少,广播电台少,即使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全是听不懂的语言。所以,在这里呆的时间越长,越关心国内的情况。朱清民倾其所有,把自己出国前的见闻全向田师傅作了介绍。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经过一番闲聊,彼此之间很快由陌生变熟悉。田师傅也喜欢直来直去:“你们今天来,肯定有事找我,说吧什么事?只要我办得到。”罗师傅抢先答话:“阿拉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10米2.5截面的电缆线。”田师傅二话没说就拿出一卷2.5个截面的电缆线来剪下10米。朱清民在领料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马上感觉到田师傅就是他的救星!
从此以后,只要有空,朱清民就会到这位老乡的仓库里坐一会,诉诉苦聊聊天。田师傅喜欢听国内新闻,朱清民带有一个收音机,在寝室内架起一根长天线。把方向调准后,每天晚上10.30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然后,再将听来的新闻转告田师傅。如果用‘醉翁之意不在于酒’揶揄朱清民有些残忍,为了JS市纺机厂,他也很无奈。三台机器,需要预埋1.5和2.5截面的电线,共计一百多米。现在,田师傅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但是,朱清民还是很难启齿,当心为难人家。不过,不找他又能找谁呢?最后,朱清民还是硬着头皮找田师傅开了口。后者的确有些为难,但还是答应下来;让朱清民把规格、颜色和数量写好,要他缓两天再去拿。两天后,朱清民来到田师傅的仓库,后者已经将电线按规格和数量打包在一个编织袋内。趁吃饭人少,让朱清民赶紧提走。
8月 7日多云 31℃
grinding机的电源线领来几天了,冯工仍然不肯连线通电。理由是,吸尘器不应该与主机使用同一个配电箱。朱清民再三解释,这台设备几十年来就是这么用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但冯工强调理论上不充许!朱清民当心把事情搞僵,不敢与他正面发生冲突。正在为难之际,安徽设计院专业电器设计师张高工来到现场。朱清民并不认识他,但冯工与他很熟,而且显得很尊重他的样子:“张高工,您来得正好,这台机器的主机与吸尘器共一个配电箱,我认为不合理。可他说这种机型几十年来就是这么用的,没有出过问题。电器设计您是权威,您看行不行,我听您的。”看到冯工与这个张高工这么熟悉,朱清民有些警惕。他赶忙拿出机器的电器原理图,很恭敬地对张工解释:“您看吸尘器的专用插座并联在配电箱主令开关的电源后面,与主机的控制线路完全不相干,而且功率只有0.75KW。这台老产品,我们已经卖出去几千台,从来没听说吸尘器出问题。”张工仔细地看了电器原理图后,对冯工说:“从电器原理图看,设计是合理的,你就按制造厂的资料验收吧。”冯工还想说什么,张工好像有急事,已经转身离开。冯工也打算一走了之,朱清民连忙阻拦道:“你先别走,既然张工认可了,你就帮忙把电通了吧?”冯工狡黠地:“通电?我又没有阻止你,自己去接线吧。”说完话,又要走。朱清民当然可以自己接电源,但是,明明归他干的事为什么要我干?再说这冯工就不是什么好鸟,等你真把线接了,他会说你私自连接电源,影响电网工作。想到此,朱清民有意甘拜下风:“冯工,我不是电工,我不会接线!”冯工正要赌气离开,听到朱清民的话,立刻停下来:“哦,你不懂电器是不是?你不懂我可以帮你接线。”他故意把声音说得很大,让还没有走远的张工听到。朱清民从来不要虚面子,只要你肯接线,不懂就不懂无所谓。好不容易接通了电源,主电机不转。冯工拿试电笔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很老练地说:“问题很大,可能是主电机烧了。今天我没时间,等有空再来帮你仔细检查。”朱清民可等不得,等冯工离开之后,马上借来万用表,分别测量主电机三相线电压。刚才冯工用试电笔测过,三根线全都有火,所以,他说可能是主电机烧毁。现在用万用表测,有两相电压正常,另有一相电压为零。应该不是电机问题,朱清民又惊又喜;喜的是电机是好的。惊的是grinding机钉箱前试车,他一直在场;情况正常。怎么会差一相火呢?联想到1993年OPEN机出口到马来西亚,本厂电工干的恶作剧,难道又是本厂电工缺德?经过逐步检测,朱清民发现主电机交流接触器有一个接点输入、输出都有电压,但通过导线连到电机后电压没有了。他松开接触器螺钉,拔出导线检查,结果,这根导线的铜芯还被胶皮紧紧套着,螺钉紧固在电线的胶皮上。由于电压高试电笔仍然可以点亮,但电压却没有。果然又是人为的恶作剧!值得庆幸的是,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罗师傅也很高兴,突然问朱清民:“你懂电,刚才为什么说不懂?”朱清民:“我没有电工操作证书,连接电源涉及到厂内的电网。我自己连接电源,叫擅自连线。万一冯工反咬我一口,那才吃不完兜着走。”罗师傅鄙夷地说:“什么冯工?跟我一样,在上海都是普通工人!”朱清民对此不宜发表评论,JS市不是一样吗?1988年之前,评一个中级职称难上加难。90年代之后,就因为许多领导干部没有职称,连小学毕业生也送一个工程师、政工师或管理师的头衔。
8月13日晴 35℃
clean机的配电柜被水浸泡过,朱清民不敢声张,先把它搬到太阳下晒。然后,用万用表对照电路图逐个检查触点和回路的闭合情况,有三个时间继电器无法工作。经过四处打听,其它厂家所带的备用电气元件没有相同的型号,华源仓库的田师傅那里也没有。朱亲民想:只能等到周末,把三个时间继电器拆下来,带回寝室修理,能否修好就看运气……后来,朱亲民把它修好了。
中午下班,朱清民和天津纺机的电器工程师老孙一起,站在ENITEX大门口等汽车。一个黑人小女孩,头上顶个搪瓷碗,无需用手扶,走起路来稳稳当当。她每天按时给父亲送饭到厂里来,朱清民每天在这里等车都能看到她。今天,朱亲民一招手,那小女孩竟然走过来,他好奇地问她:“你头上顶的什么,它不会掉下来吗?”小女孩睜大眼睛看着他,不明白他说什么。小女孩五官端正,面部轮廓分明。朱清民第一次感到,黑人并不比黄种人丑,只是皮肤黑一些。小女孩不知他想知道什么,她揣摸着从头顶把饭碗拿下来,递到朱清民面前。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仔细看,碗里盛有半碗米饭,上面还盖了薄薄的一层番茄酱之类的食物。他又看了看小女孩的头,头上什么也没有。对非洲女人的头上功夫他很好奇,大到陶罐小到饭碗什么都能用头顶。……“给爸爸送饭吗?”朱清民问,小女孩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将碗放回头上,离他而去。一阵心寒,若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女孩应该在读小学。她肯定很聪明,但她没有机会读书,这个国家的黑人绝大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小女孩给父亲送来的带有霉味的米饭,对她们家人而言可能属于开小灶。因为爸爸是挣钱的人,需要重点保护,家庭的其他成员,就只有木薯或野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