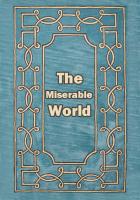整个山寨的布局有些松散,七歪八扭的到处都建有屋舍,有些屋舍还能看出用途,但大多都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众人猜测应该大多都是山匪用来睡觉的通铺,其中也有一些可能是仓库、粮仓之内的存在。
所有屋舍中最宽大的一间,是一栋二层木制阁楼,这座楼阁最是靠后,也离悬崖最近,应该是山匪头领们住宿的地方,亦或是聚众饮宴的大厅。
这座山似乎只有通往山前的一条小路,在山门前小路被截断,进出都必须依靠吊桥,新兵们将整个山顶都小心的窥视了一遍,并没有再发现其它任何可以下山的道路。
此时午夜已过,整个山寨一片寂静,只有几个放哨的在轻声低语着,杂乱的屋舍之中也无一丝灯火,除了不时响起的呼噜声外再无任何动静。
举着火把巡逻的守卫此时也懒散的扛着刀枪,打着哈欠的垂头耷脑的勉强排成两列梯队,穿插着在整个大营里游来荡去。
山寨大门的吊桥早已收起,上面的几个守卫也放心的依靠在,被夜风吹的扑啦啦响的山寨旗杆旁酣睡起来。
…………
火光冲天,山门处兵器交击声、嘶喊声、哀嚎声响成一片,突然而起的喧闹将整个宁静的山顶一瞬间卷进了血与火的漩涡里,所有人都在这惨烈的漩涡里沉沦着狂乱着,生命脆弱的如同路边的野草,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脆不可堪。
所有人都瞪着血红的眼睛如同噬血的野兽,嚎叫着撕咬着翻滚着,一根根兵器断裂一颗颗头颅抛飞。
手中紧紧握着斩马刀,身前一个刚刚一刀斩断身体的山匪,如今尚未死去,身体的上半截拖拉着一地的肚肠,被斩断的左臂骨碴外露,断裂的血管朝外喷洒着艳红的鲜血,满身血污的翻滚着哀嚎着,仅有的一只手用力扣挖着地面,半截身体在地面拖出长长的血痕,一寸一寸的挪动着身体寻求着最后的生机。
从未想过一个人的身体里竟会有如此多的血液,仿佛永不枯竭般的喷洒的到处都是,也从未想过一个干瘦的身体内竟堆挤着如此之多的器官,身体被切开来后满满的堆积了一地。
鲜红的心房还在跳动,一股一股的朝外喷着红红的血液,蠕动的胃块还在消化里面残留不多的食材,肺叶和一堆血管纠缠在一起一鼓一合的做着最后的挽救。
手里的刀变得很是沉重,双腿有些颤抖,浑身血液仿佛蒸发般的消失的一干二尽,灿生很想呕吐,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胃翻腾不已,却只能蹲在地上干呕,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呼吸堵住了食道,隐约中灿生感受到堵住自己的是自己那原本就已经不多的纯良,和对生命的最后一点敬畏。
勉强爬出一米远的半截躯体此时也耗尽了最后的生机,一只手仍然死死的抓进地面,几根用力过猛的指骨大部分都已经断裂开来,碎骨白惨惨的刺破皮肤暴露在外,另一根被截断的手臂无力的朝前伸的笔直,永不闭合的双眼里满是不干和不舍,有那么一闪念间灿生甚至从那双眼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绝望和无比的怨恨。
他应该也有家庭吧?应该也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彩故事,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许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死,而是在渴望那再也见不到的“眷恋”吧?
突如其来的感慨从灿生的心底涌出,无法抑制的冲进大脑之中,自己生活中见过的每一个人都闪电般的从眼前划过,就那么止不住的全身战栗起来,仿佛被一块万年的寒冰封冻全身,这一刻竟如此的压抑和冰寒。
“小心身后!”一声大喝声突然冲进脑海,灿生本能的往前跨出一步,紧接着手中的长刀就在身前一撩,身体顺着刀式的带动朝地面翻身歪倒,右腿一弯,脚尖蹬地支柱上半身的倾倒,左手就势在身后地面一拍,右手中的长刀划过一道弧线将身后偷袭而来的山匪一穿而过,鲜血顺着刀尖滴滴答答的砸落地面。
被一刀穿身的山匪一口一口的吐着鲜血,眼中无比怨毒的死瞪着灿生,原本高举在半空正要砍落得袹刀,此时也被其双手握的死紧朝着灿生的脑袋狠狠劈去。
有那么一瞬间灿生突然不想再躲闪,一命还一命的念头从心底一闪而过。
“噗”的一声,一把斩马刀从山匪的双臂和脑袋上一斩而过,鲜血和脑浆撒了灿生一头一脸。
铁柱的脸色也很是苍白,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但却依然掩饰不住肌肉间无意的颤动。
不是每一个人都生来杀伐果断铁血无情,初历厮杀的新兵们大多都被鲜血和残肢断臂,狠狠的震慑住了内心之中的天真。
感激的看了一眼铁柱,灿生一紧手中的战刀,一把将衣角撕下一长条,一圈一圈的将右手和握柄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被鲜血浸泡过的握把有些滑腻,而战场上失去武器的士兵只有死路一条。
一遍一遍默念着“我是战士~我是战士~~我是战士…………”灿生的双眼逐渐坚定起来,看着眼前血与火的世界一缕缕血丝充斥眼中,暮然间眼中血红一片,大喊一声“杀!~”双手竖握战刀,大步冲入人群见人就斩。
…………
断裂的斩马刀只剩下原本的三分之二,此时被拄在地上支撑着身体,被割出一道深可见骨伤口的左腿跪到在地,鲜血顺着头顶糊满了半个身体,凝固成黑红血块垂挂在发间,凌乱的发际如今凝成一缕缕,披散开来,隐约间露出发丝后一双死死盯着前方冰冷而坚定的眼神。
一路斩杀,不知砍飞了多少颗脑袋斩断过多少根胳膊,灿生就这么红着眼不停挥舞着长刀,将每一个从眼前晃过的影子切割开来,任何接近过来的山匪都在一道血光划过之后爆裂而开。
灿生脑中空白无比,没有去想自己此时在做什么,也没有去想自己的长刀砍翻的是什么,只是一遍遍的低语着“我是战士~我是战士…………”然后将《血战七杀刀》围绕自己的身体一次次的施展出来,如同一阵刀刃旋风在人群里肆虐冲杀。
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冲进了这座木制阁楼,只是这么一路见到人影就冲杀而过,一路砍杀着直到被眼前独眼汉子一把开山刀架住长刀,然后一脚踹飞撞在廊柱上才清醒过来。
大厅里座椅翻到,一具具或男或女或老或幼的残缺尸体分布在四周,灿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自己杀的,不过也没有什么区别,死在自己手中的人还少吗?
独眼汉子胸口纹着一只恶狼,袒露在衣袍外的手臂上也纹刺着火焰云雾,仅剩的一只眼中充满仇恨和愤怒,和灿生一样血红的相互对视者。
战场之上没有正义,更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生死,不是你生就是我死,亦或是我生你死!~
所以相视中的二人谁也没说什么,一挺手中兵器凶狠的厮杀在一起。
独眼汉子手中的开山刀风雨不透,每一次劈砍都带起狂风呼啸的“呜~呜~”声,灿生也是以硬碰硬一把斩马刀舞的灿然生花,血红刀光在开山刀的劈砸下撩、劈、挡、刺,与开山刀激撞的火星飞溅。
二人在大厅里反转腾跃你来我往,将大厅里散乱的座椅和地上的碎尸激荡的四处纷飞。
“铛啷”一声,窄长的斩马刀终究抵挡不住开山刀的厚重,在彼此硬碰无数次后终于断裂开来。
一见兵器受损,任灿生不及细想,手中断刀往后一收,格挡在头前,身体半侧,右脚弯曲足尖点地,左腿一甩就要将身体转到独眼汉子身后,却不想开山刀来势迅疾,“锵”的一声从断刀刀身斜滑而过,被断刀垫偏的开山刀却依然从灿生躲闪不开的脑袋上切割而过。
二人一粘即分相互交换了位置,但灿生的头上却被割出一条巴掌大的创口,翻卷的皮肉里清晰可见出现裂痕的头骨,片刻后鲜血飙涌而出。
一阵剧痛伴随昏厥席卷而来,身体晃动了一下,险些晕倒在地。
断刀一撑地面站稳身形,独眼汉子一摆手中开山刀再次拦腰横砍而来,手中断刀迎着开山刀斜挑而上,“铛~”的一声撞击在一起,灿生当即被震的倒退五六步。
独眼汉子跨前一步正要接着一刀劈斩而下,突然一阵劲风由身后急刺而来,汉子身形一扭,手中开山刀贴着地面旋转着卷向咫尺之外的灿生。
见汉子将刀甩斩而出,身形扭动避过短刺的突袭,灿生一手将断刀卷搅向旋转而来的重刀,一手甩抖丝线带动短刺再次朝身形不稳的汉子钻刺而去。
那汉子见短刺再次刺来,不及细想,一手猛撑地面身体倒立而起,一手却抓向短刺旋转锋刃,却不想灿生再次一抖手腕,短刺方向一变,突然由下而上“噗嗤~”一声穿透汉子手臂。
而此时断刀也和开山刀再次搅在一起,开山刀被挑飞开来,灿生本以为就此无事,却不想汉子撑在地面的手指蓦然一挑一压,被挑飞的开山刀竟也一个变向朝着灿生的左腿削砍而来,却是汉子的开山刀竟也连着丝线。
事发仓促任灿生只能用断刀硬接一刀,再次将开山刀挑飞,却终是被刀刃狠狠的在左腿砍出一条露骨的伤口。
忍着左腿的剧痛,一勾手指穿透汉子手臂的短刺立刻一搅然后钩挂这汉子手臂上的筋健和肌肉倒射而回。
汉子的左臂当即鲜血淋漓的垂挂在身侧,再也动弹不得。
汉子也是一狠人,看了一眼鲜血不止被废掉的左臂,眉头都没皱一下,右手一抖丝线,开山刀飙射而回。
单臂拖着开山刀,汉子身体一弓朝着对面暴冲而去,半跪在地上阴冷盯着对方的灿生也在同时将短刺朝身后一甩,双手倒握断刀朝着汉子迎面而上。
二人即将撞在一起时,汉子身后的开山刀斜撩而上,要将灿生一刀两半,而灿生却腰身一扭手中断刀,在开山刀上一点,整个人一个空翻从汉子的头顶翻了过去,人未落地手中断刀在空中一个横削,朝着汉子的脖颈削砍而去。
汉子见对方翻过头顶暗叫一声不好,匆忙中急忙身体前冲,上半身急忙朝地面滚去,手中重刀却是去势不但不改,反而更是用力挥动,原本横斩的刀刃,在巨力下竟沿着斩东的轨迹演变成朝身后飙刺,奔着灿生尚未落地的身躯而去。
一时间兔起鹘落二人生死变换不定。
身在半空的灿生一见汉子朝前翻滚,嘴角阴冷一撇,手指勾动,甩落的短刺突然从地上弹射而起,将近在咫尺的汉子从背后穿喉而过斩杀当场。
到此时被汉子抛出的开山刀也已经飙射到身前,灿生手中断刀再次在刀身一点,半空中的身体一个侧翻再次翻回原本的站立之处,而开山刀在承接了断刀的点压后,方向一改狠插在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