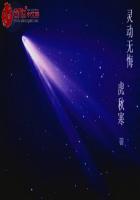燕赤霞听到萧若兰惊叫之声,连忙飞身赶了过去,就在他踏进死门的刹那间,也跟着惊呼一声,便愣在了那里,好久也没作声。
就见死门之内,烛光摇曳,灯火明亮,但令人心惊胆裂的却是偌大的石室,坐满了累累白骨,燕赤霞粗略地点算了一番,竟有几百具骸骨席地而坐,更让人称奇的是那门后还端坐着一位耄耋高僧,面朝门口,容貌恬静,袈裟鲜亮,双掌合十,举在胸前,像是圆寂不久。
燕赤霞稳住心神,前去俯身查看,端详了许久,才怔怔地念道:“怪不得久未听闻白云大师在江湖中走动,竟是在此处坐化往生,实令老夫唏嘘不已啊。”
燕赤霞说着,便朝着白云大师的遗体跪拜了几回,又抬头瞻仰起白云大师的遗容,哪成想,那白云大师突然睁开双眼,开口言道:“早不来,晚不来,早晚要来;早不死,晚不死,早晚会死。”
此番情景,即便是燕赤霞修道日久,也免不了心惊肉跳,魂飞魄散,萧若兰更是惊恐万分,稍作发愣,还没等石门关严,便转身逃了出去,嘴里高声叫唤着:“我的妈呀,闹鬼了,诈尸了...”
石门闭合,燕赤霞已无退路,便仗着胆子,双眼直视着白云大师,开口问道:“不知大师是人是鬼,是死是活,给老夫个痛快话吧?”
白云大师微微笑着回道:“阿弥陀佛,燕使者道法高深,还须老衲徒费唇舌吗?”
“这,这也太诡异了吧,我等前往白云寺,没寻到大师的佛影,却不料在此相遇,怎能不让老夫心生疑问,惴惴不安呐?”燕赤霞听着白云大师的回话,却觉着语气温和,倍感亲切,确不似亡灵作祟。
白云大师微闭双眸,缓缓地又道:“老衲的先祖,乃是沈万三的管家,距今也有二百多载了吧。当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因和一个女子偷情,牵扯到蓝玉案中,致使沈家几乎满门抄斩,只有沈万三的次子沈茂,受到了沐春将军的庇护,才得以逃脱,繁衍后代,并把被杀族人的骨殖收殓在此,由老衲的高祖奉命在此守护陵寝,却不料被燕使者的弟子们误闯其内,老衲正发愁如何处置,你便到了。”
“弟子们不知轻重,搅扰了大师的清幽,还望大师原宥我等的莽撞。不知大师独居洞内,以何为食呀?”燕赤霞心中暗道,莫管你是遁世仙圣,还是得道僧侣,都得吃饭喝水吧,便不解地问道。
“沧浪之水,可解渇意,山中野果,添腹充饥,单凭活命,足矣了。”白云大师目光清澈,淡然回道。
“大师所言极是,弟子受教了。”燕赤霞赶忙稽首应道,又想起张昊天,便再次发问,“不知白云寺山门间的四句偈语,可是大师所留?”
提到此事,白云大师却长叹一声:“唉,说起这话,也有五十年的光景了。想当年,老衲刚刚继承护陵使命,便登上了白云山,筹建白云寺,而那道山门,其实乃是老衲的进出通道,方便登山和入洞所用。谁知老衲刚把院墙和山门砌好,却迎来了首位香客,自称是天机老人,并给老衲留下了四句谶语,说是日后若有香客跪爬几千几百九十九层石阶,前来拜山求医,但凡问及张昊天如何救治,便可复述一番。就在前些时候,老衲自觉来日无多,又怕有违他人所托,便将那字句镌刻在石门之上,却不想被燕使者瞧见了啊。”
燕赤霞拱手笑道:“我等此番前来,就是为救张昊天的性命,如今听闻大师所言,心里便有底了,不日便赶往孤悬海外的逍遥观,寻得十世镜,以解张昊天的身世,让他神清目明,魂魄归位,重返人世。”
“善哉,善哉,如此甚好,老衲也就心安了。”白云大师如释重负,面现笑容,语气轻松地说道。
燕赤霞从白云大师的口中,探得了偈语的由来,不禁眉开眼笑,但扭头去望那些森森白骨,又使他的心绪发堵,便拿眼细看,却发现有的骨骸头颈开裂,有的腰椎折断,如今保持着坐姿,全是被人涂以胶漆续接而成,而且泛白的茬口清晰可见。
“莫要惊疑,沈家几百口子的尸骸,全都在此。据说当年主人家是被分了几批而处死的,有的被砍头,有的被腰斩,还有的是被绞死的,其状之惨,足以惊天动地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白云大师敛住笑容,面目慈悲,哀切地言道。
燕赤霞听罢,不由得为沈万三鸣屈叫冤:“想当年,那沈万三帮着太祖皇帝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却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令人费解啊?”
白云大师微微地摇着头,低声回道:“你可知朱元璋如何说辞?”
燕赤霞脸色茫然,却不知晓,就听白云大师又说:“当时那朱元璋发着怒说,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
“唉,说来说去,还不是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嘛,沈万三家财万贯,功高震主,那太祖爷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若是沈万三舍得散尽家财,或可留得一命啊。”燕赤霞轻叹一声,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沈万三的死因。
白云大师接口念道:“舍得,舍得,舍了便得,不舍不得,老衲如今却舍不得这条老命啊。”
“出家之人,看破红尘,万事皆空,难道还惧怕生死之事吗?”燕赤霞看那白云大师心智澄明,功德圆满,早该坦然面对生死,从容走上往生之道,为何却贪恋尘世,不敢正视六道轮回,便不解的问道。
白云大师苦笑几声,瞅着几百具骸骨言道:“非老衲贪生怕死,而是因老衲年幼出家,后继无人,身负的重任无人接手,这般脱身而去,却对不住先人所托呀。”
燕赤霞听罢,心头却在暗自念叨着,如今沈万三的后人就在隔壁,不知该是以实相告,还是隐瞒下来,省得沈傲霜面对先祖的骨骸,触景生情,伤感万分呐?
杨梦言在外听完萧若兰的转述,说是门内堆满死人的骨头,不免毛骨悚然,惊骇不已,又将耳朵贴在石板之上,静心听了稍许,却没有传来动静,更是胆颤心惊,生怕燕赤霞有何不测,便冲着汲水而回的洛昊空和卓断水吼道:“你们俩快进死门瞧瞧,燕使者在里面流连了好半天,也没个声息,不知是死是活,真是急死人了。”
卓断水将水囊递给杨梦言,又让洛昊空将石门重新开启,不等门缝大开,便侧身挤了进去,却见燕赤霞与一位身披袈裟的老者,迎面而坐,谈兴正浓。
卓断水也瞧见满屋子的白骨,竟心不惊,肉不跳,更不敢打断他们的谈话,便立在门边,握紧逆天刀,一眼不眨地盯着燕赤霞,以防出现变故。
燕赤霞不曾知晓,白云大师双眼注视着自己,却一心二用,两耳细听着身后之人发出的气息,便轻声笑道:“此人天赋异禀,骨骼清奇,处事不惊,眼见着白骨森然,却是气定神闲,心净如初,不为外物所累,堪称武学奇才呀,若是假以时日,燕使者再好生调教一番,这普天之下,实难遭遇敌手啊。”
“水儿,还不快来见过白云大师?”卓断水乃是燕赤霞悉心调教的爱徒,只等着接他衣钵,听闻白云大师赞不绝口,焉能不喜,便把他唤到白云大师的身前。
卓断水行过礼后,再不多言,默然立在燕赤霞身后,面色苍冷,不苟言笑,白云大师凝眉而视,许久才开口:“阿弥陀佛,看这水儿雄姿勃发,丰神骁勇,为何眉头却紧锁着迷惘之色,莫非是为情所困?”
卓断水废话甚少,听闻白云大师如此来问,却不敢隐瞒:“大师所言不虚,弟子确是陷入儿女私情,不能自拔。”
白云大师笑着指向门口,轻声言道:“可是门外的那位姑娘?”
卓断水并未做声,而是点头示意。谁知白云大师沉吟片刻,轻摇着头,随口叹道:“阿弥陀佛,门外女子,戾气甚重,红颜薄命,寿短如花啊。”
此话听得燕赤霞心惊胆颤,急忙疑惑地问道:“大师此言,老夫却不敢苟同,那杨梦言心性纯真,乖巧可人,哪来的戾气藏身,又何谈阳寿将尽啊?”
卓断水也急切说道:“梦言师妹,有口无心,尽管平日里惯于嬉笑怒骂,却无伤大雅,从未做过恶事呀。”
“呵呵,二位莫要惊心,杨梦言皆因累世所劫,却与今生无关,从她的名姓,便可预判,梦言,梦魇也,试想能存几时?”白云大师尽管慈眉善目,语气祥和,却让燕赤霞和卓断水悲恸欲绝。
燕赤霞双眸含泪,战战兢兢地拱手又问:“大师,梦言年逢及笄,含羞待放,正当好时候,老夫怎能忍心让她这般年纪,便撒手人寰,弃世而去,还求大师不吝赐教,如何才能保住她的性命啊,哪怕让黑白无常牵走老夫,换取梦言存活于世,也在所不惜呀。”
“切不可取走燕使者的性命,还是拿水儿之身来换,恭请白云大师成全。”卓断水连忙跪倒在白云大师身前,话语恳切,双目浸血,令人动容。
白云大师摆手笑道:“老衲亦非天王老子,哪有偷天换日之功,还是奉劝两位,倍加小心,多结善缘,或可逆天而行,救她延寿于世吧,阿弥陀佛。”
听闻白云大师所言,燕赤霞和卓断水心思沉重,皆都无话可说,神情凄然,而白云大师却目光如水,安之若泰,也不再多讲。
“燕使者,你们在里面将息,可否无虞?”就听洛昊空在门外问了一句。
燕赤霞扭头对卓断水嘱咐道:“水儿去吧,白云大师所讲的梦言之事,万不可让她知晓,你可记清楚了?”
卓断水点点头,起身离去。白云大师转身望门,喃喃自语着:“阿弥陀佛,世间之事,千奇百怪,男欢女爱,天道使然,不知何故又生出龙阳之好,断袖之癖哪?”
燕赤霞心中自然晓得白云大师所提何事,也没吭声,心里却如针扎般难捱,又念及他料事如神,无所不知,却不敢再替沈傲霜掩饰身份,便垂首拜道:“老夫尚有一事,未曾向大师言明,还请大师勿怪。”
“阿弥陀佛,燕使者舐犊之情,老衲焉能不知?”白云大师面色平和,眼盯着燕赤霞,继而又道,“生门之内,有位昆仑弟子,唤作沈傲霜,乃是沈万三的后人,不知老衲猜得可准?”
若是白云大师感应到隔壁有位昆仑弟子,出自沈家,也就罢了,而他竟能唤出她的名姓,却让燕赤霞舌桥不下,惊诧万分,以往的自负一扫无余,连声赞道:“大师真乃神人也,竟可极往知来,慧心通天啊,老夫虽也会些扶乩卜卦的毛皮,但在大师面前,却是小巫见大巫,鲁班门前摆弄着斧头,不值一提,老夫已然心悦诚服,自愧不如啊。”
“阿弥陀佛,燕赤霞何须如此谬赞,见识多了,自然就会通晓世事,见时知几,还不快把沈傲霜给老衲唤来,让老衲将身后之事交付与她。”溢美之辞听多了,白云大师不以为然,只是轻轻笑着,心头却急着要托付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