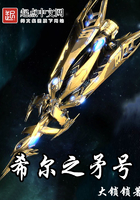王伦租了艘小船从建德向南驶向婺州金华。
千山景色此间有,万古书台别地无。
走遍涪江两岸,无敌金华山。
揽尽世间风光,独数此美景。
曹宅镇。
“胡伯,备马。”
“员外,今日不读书了?”
“爹身体有些不适,我代走一遭。”
“好,好,我这就去备马。”
“胡伯,你不用去了。”
“啊?官人,恁上次去大黄村差不离有半年了罢?路径记不清了罢?”
“哈哈,记得清,有两个小厮陪我去就行了,胡伯你年纪大了,庄里庄外事这般多,就不要到处跑了。”
“好,我听官人的。”胡伯谢了转身去备马,被称呼官人的中年男子检视了一番账册户薄确保无缺,片刻后胡伯取来了马,三人登鞍上马,直往大黄村奔去。
大黄村口好不热闹,十几辆大车路边靠着,几十口百姓聚集在一挂大秤前,一个小厮举着账本划账,两个小厮看秤。
“看郑大官人来了!”一个眼尖的汉子道。
“可不是莫!上次来不得有三五个月了?”
“嗯,嗯,有的,有的。”
这边小厮看少东家来了,匀出一个人上前接引,“官人,怎的劳恁亲自过来了,这些许小事,我们这些下人包管给恁办妥。”
“无碍,读书乏了,过来看看。”郑官人下马靠近人群,百姓们见了上前作辑问好。
“乡亲们今年收成如何?”
“好的很,好的很,又得了几日的好日头。”村正开口道,众人也是附和。
“那坦溪水渠如何了?”
“就是得了官人指点,才叫家家户户得了这水利,得了个大收成。”
“马老汉与他邻家王老汉争地之事后可再有争执?”
两个老汉出了人群,朝郑官人作辑:“老汉得了官人调停心服口服,再不曾争执。”
“好,好,乡里乡亲,为那些鸡毛蒜皮小事争执岂不伤了情分,和气生财嘛!”
众人点头称是,郑官人又询问一些村子的近况,哪家有争执,哪家有困惑哪家染了小病,都一一解答,待众人没了话头,郑官人笑笑:“乡亲们无事了罢?今年收成既然好些,往日的欠账是否还些?”
“是理,是理,当还。”
待小厮们把今这一季的租子收完了,郑官人打开账本,开始对欠账。
“李二,你家去年欠了三石米,这次还多少?”
“今个都能还。”
“孙老伯,年前你家借了二石米,这次还多少?”
“郑大官人,小老儿婆娘害病,一直吃药,能不能宽限些?”
“好,就宽限些。”
“多谢大官人”
“张小六儿,你呢,这二石米可都欠了三季了!”
“郑大官人!小人,小人作买卖折了本钱。”
“怎的?得了好收成又想拿去赌?”
“小人不敢,真的是做买卖折了本钱。”
“那好,既然是做买卖,请何人作的保,又是作的什么买卖?”
“啊,做的,做的那贩药材的买卖,请的,请的那~~作的保。”最后声音小的都听不到了。
“够了!不学好的懒柴!这欠账,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安安心心种地养家!少跑去胡混!有些钱去读点书,不愿种地去做个家仆也有个头面!”
张小六儿懦懦应了。
郑大官人打一早出门,半下午才回来,着两个小厮带着村壮推着大车把粮入了仓,点了账这才完事,推车的村壮一人赏了二十个大钱打发散了,带着两个小厮慢慢回庄。
“大官人,恁就是心善,跟这般农夫讲什么仁慈,这一天跑来,欠账没收多少,空耽误了一日时光,小的下去,包准儿能收回来!”
“百姓自有难处,不可过分。”
“大官人,我看还是利钱太低,使得这些人放肆,外面那些个员外,这借账,哪个不得八十分利?员外这四十分利,太过心善了!”
郑大官人摇头叹息,不复再言。到了庄前,灯火通明,早有苍头出来接了马匹。
“何人来此,听的府中这般热闹?”
“官人好耳力,晌午头来了个员外,带着十来个威风的护卫,说是慕名而来,老爷请了吃酒,官人再不回来,就要派人去请呐。”
“哦?”郑官人也顾不得多想,直入后院,梳洗净了,换了身干净衣裳,这才出来见客,只见老爹堂上正坐,堂下只坐了两席位,再往后三桌二十个大汉围着吃的正欢。
郑官人向老爹请了安,拱手过来,“在下,郑刚中字亨仲,今番迟来,客人莫要怪罪。”
“哈哈,郑亨仲,百闻不如一见,在下姓王,王德胜,初次见面有礼了。”不是王伦,还能是谁?
两人叙礼已毕,郑老员外唤过儿子吩咐几句便请辞去了,王伦看此人有疾
却亲自作陪心中很是赞叹。
两厢落座,郑刚中这才上下打量王伦
,猜测着对方的身份,且吃了片刻郑刚中这才道:“不知员外来访有何指教?”
王伦这算是头一次招揽有家室日子过得不错的土财主,这种人最是难招揽,不过对王伦来讲,除了犯了大案,或是走投无路的都难招揽,也没什么区别,既然来了见一见,说不定以后有机会。
“听闻郑员外精通农桑之治,特来求教,不知可否指点一二?”
郑刚中上下打量了一番王伦道:“员外,我这农桑之治,你即便听的,却学不来的。”
“哦?何出此言?”
“不知员外庄下多少农户,多少牛驴,多少田地?”
“农户三百,牛二百,田地三千亩。”王伦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数。
“哦?敢问牛租几何?地租几何?”
“牛租没有,地租老农一成,新农四成。”这老农说的是济州岛的移民,因为是开的荒地,租赋只有一成,再加上济州岛的地理位置,所以养人为主,收税不是重点,新农说的是高丽南部移民,对于当时税收的起征点,王伦与闻焕章,萧嘉穗,仇悆等人激烈的商讨过,因为南部的耕地肥沃,一亩地平均产量两石以上,又是开好的地,故而众人人强调税赋不可太低,梁山有几十万人马吃饭,王伦却一心要降低,最后定了个四成,一年两熟来算,一户一年收四百石粮食,上缴一百六十石,自留二百四十石,丰衣足食的量了。
“哦?王员外,你这员外做的亏喽。起码少收一倍的租税。交了朝廷的租赋,你还能留多少?”土财主是要给朝廷交税的,按王伦这样收,还要倒贴,不过,皇亲国戚,望族贵胄权臣的封地是不需要交税的。
王伦一笑:“所以前来求教,不欲加赋于百姓。”
郑刚中也笑了:“原来员外是同道中人(考取功名,造福百姓),不过朝廷的赋税可少不得,也罢,按你所言,即便可以自定赋税,也不可如此。百姓务农应专精,如今的赋税不重,二道,三道税确是有些过重,朝廷本意变法轻赋,传到地方却难免偏激。”
“亨仲兄所陈不假,不妨设一乐土,君有何高见?”
郑刚中想想道:“王兄既作此题,我便大胆直言。百千年来,税种多,税额重,无非就是一个钱字,王兄可知我大宋税收大头是什么吗?”
“怕是盐税了罢?”
“不错,这盐税讲起来,称为人头税更为贴切,人不可以不吃,却以为吃的不多,也没多少钱,没想到这钱却是根本。”
王伦点点头,没错,即便到了后世,这盐务税收还是有意无意的专管,这商税收起来难度大,那这看起来很公平的人头税就好操作多了,贫民吃低价盐,富人吃高价盐,有高低之分,有选择的余地。
“再讲这粮税,却是少收不得,百姓勤勉有余粮,懒作就要叫他饿肚子!”
“这……亨仲兄,这样把百姓当畜生,钉死在土地上,与那刮骨熬油之徒有何分别?”
“嗯,确是无情,却也有理,苛税重,土财富而百姓苦,为何江南富而京西荆湖苦?土肥不同湿热不同劳作之人不同,必要其尽力耕作才可。”
王伦汗颜,让百姓死命耕作然后收税就是生财之道?
“王兄觉得我所言太过凌厉?哈哈!”郑刚中大笑几声。
“亨仲兄泰然自若,必有后言。”
“不错,收上来的钱粮除却军饷,吏饷,度支,储备,修葺,还有兴建,兴学,开荒,治河诸般事宜,况几户小农可兴乎?”
“此般大事,用度颇多,但盘剥百姓实过。”
“此乃取之于百姓,用之于百姓,是,多收了粮税,但这钱修整了村道,加固了河渠,清理了河道,还盖起了学堂,请来了先生,若少收些税,百姓真的能过好么?”
“亨仲兄所言乃集中力量办大事,叫赋税不妥。”
“不须花哨编些个名目,叫不识几个大字百姓挠头,每年情况各有不同,多寡官吏商决,起个什么名目百姓能说什么?”
“王某愧然。”是啊,各项支出还不是官府说了算,比如修一条路,难道真的修完了就可以少缴税吗?别做梦了!搞那么多名头作甚!
郑刚中笑笑,唤来下人交待几句,继续道:“我家几代传承,在此生息,知百姓不易,却也知百姓质朴却执拗,也爱攀比,也有嫉妒偷懒做白日梦,需要有识之人引导,软的见效慢,就是村学,硬的见效快就是强制,税收虽重,却能让他们见识到好处,村里通了宽敞的路也值得吹一番。”
“亨仲兄所言字字金玉。”
“哈哈,不才,田垄之事多讲了几句,王兄,专门做的汤,尝尝。”
王伦尝了几口汤,稍稍便见底,郑刚中见众人吃喝已尽,站起身来:“王兄,时候不早了,且请休息罢。”
王伦陪说几句,便跟着郑刚中去准备好的客房,王伦四下一看很是满意,郑刚**手拜别,王伦却道:“听亨仲兄一席话,感触良多,冒昧一问,能否再讨教一二?”13
郑刚中笑笑道:“远来是客,不妨事,待我安了爹娘,梳洗换一身衣裳再来与王兄小饮。且等半个时辰。”
“多谢亨仲兄。”
郑刚中转身离开回到大堂,几个丫鬟仆人在收拾碗筷。
“官人,这员外真是个妙人。”
“怎讲?”
“他带来的二十个壮汉护卫个个雄壮,却是极守规矩,吃饭也不作言语,每次上菜都陪着小心,这杯盘碗盏舔个光溜。”
“何止他那护卫,那员外,那跟班也吃的干净,却是从没见过这样的员外家丁。”
郑刚中听了一阵,打发下人都散了,自去拜了爹娘,梳洗一番,换了身衣裳提了一壶好茶去寻王伦。
王伦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想法需要郑刚中来佐证,梳洗好了静等。郑刚中见了门口站的笔直的护卫,笑了笑,叩门,王伦亲出迎进,俩人打开话匣直又聊了两个时辰这才散去。
第二天,王伦与郑刚中达成了采买稻种,菜种的买卖,汉城府现在种植的作物,大多是当地已有的,为了不影响收成,王伦没敢在第一年大换,以后就要逐步引种高产量高抗病的稻种了,现在江南的稻种有几十种,郑刚中推荐了五六种,由郑家供货,皆大欢喜。
王伦很是想把郑刚中拉上自己的小船,可留在当地的事务也不小,叹了口气,别离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