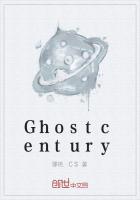苍茫浩瀚的星空里:星系多如牛毛,日月繁似尘埃。一日月成一世界,一世界内一乾坤。
九州星!
中州大陆;盘古国;燕山郡;陈家村。
三间茅草房,一圈篱笆墙。
小菜园旁,几只母鸡正在土里刨食;旧木门边,一条小黄狗趴在门前懒洋洋的晒着太阳;茅草檐下,泥巢中的小雏燕正在喳喳的抢着亲燕喂过来的蜻蜓;泥烟囱上,一缕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
纸糊轩窗,吊挂在泥棚顶的木钩上。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口,把窗前的旧书桌照的一片雪亮。
木桌上,放着一只带着裂纹的榆木笔筒;笔筒里插着一新一旧两支毛笔;笔筒旁摞着几卷破旧的竹简、一方砚台和一块黑黝黝的铁牌子。
书桌旁的木椅上,端坐着一位年近三十的青年人。他身材高大魁梧、遍体瘦骨嶙峋、一双眼窝深陷、满脸肌肤蜡黄。小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宽下巴,颌下一部短髭须,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一副憨厚木讷的样子。
青年身上的麻布长衫已经洗的有些发白,肩膀上还打着一块灰色的补丁。他手里握着一卷竹简,正在那里专心致志的读书。
咯吱~!
推开房门,从屋里走出来一个小老太太,老人家微微驼背,苍头白发,满面愁苦,看上去没有六十岁也差不太多。
她穿着一件灰白衣衫,衣服倒是洗的一尘不染,只是上面补丁摞着补丁,黑的、红的、绿的、土黄色的……什么颜色的都有。
老太太脚下趿拉着一双千层底儿的布鞋,前边露脚尖,后边露脚跟,鞋帮也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整个鞋帮也就是勉强还能挂住鞋底儿,走起路来,踢里踏拉直响,就算石头不硌脚,鞋底儿也觉得硌脚。
老太太从泥墙的木橛子上摘下一个新编的柳条篮子,篮子做工很精致,看得出来,这户人家应当有双巧手。
趴在门旁的小黄狗撩起眼皮看了她一眼,见她不是给自己送吃食儿的,就继续懒洋洋的趴在那里晒太阳了。
老太太踢里踏拉的带着鞋,推开小菜园的篱笆门,旁边刨食的母鸡呼啦啦跑了过来,想趁机会溜进去扦点菜吃。
老太太一晃空篮子,小鸡子扑啦啦飞出一丈多远。
母鸡们见老太太已经随手挂上了园子门儿,根本无机可乘,一只只都悻悻然的溜达回去继续刨食儿去了。
隔壁老陈家是个富户,家大业大院子大,房多地多驴马多。
陈家婆娘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高挽发髻,头插银簪,上身穿着一件花布衫,腰系丝绦,腿上穿着一条天青色长裤,脚上蹬着一双新做的绣鞋。
她的身材丰盈,面泛红晕,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显然是个不愁温饱的。
见老太太刚好进园子,隔壁陈家婆娘隔着篱笆招呼道:“岳老嫂子!摘菜呀!今天做点啥呀?”
岳老太太笑道:“林姐啊!还能做啥呀?糠窝窝能吃上遛不挨饿那就不错不错的了!你这小菜园伺候的不错呀,你看那萝卜苗长的,多水灵啊!”
陈婆娘:“哈哈~!好啥呀!老嫂子,你家乐意吃萝卜英子不?乐意吃的话,我给你们摘点儿。”
岳老太太:“不啦!不啦!林姐,我家的菜也都下来了,再不赶紧吃就老苗子了。”
陈婆娘:“老嫂子!正好在这碰到你了,我问你点事儿,你家牤子是不是快有三十了?”
岳老太太:“是呀!林姐!牤子过年就二十九了,什么功名也没考上,还把身子给耽误了,现在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你说这可咋办呢?都快愁死我了!”
陈婆娘:“老嫂子!您可别怪我多嘴啊,牤子念了这么多年书,也没念出个啥名堂,这眼看着就快过了半辈子了,你家老岳大哥也不说给张罗成个家,真想让孩子打一辈子光棍啊?”
岳老太太老脸一红,长叹一声道:“哎~!房子漏雨,缸里没米。把箱子底儿掏出来,家里连扯二尺布的钱都没有,我和你岳大哥就是两个老汤药包子,除了种地啥手艺也不会,挣钱的本事不大,糟蹋钱的本事倒是不小,这些年没攒下什么家底儿不说,反倒是攒下了几十两银子的饥荒。牤子还是一个书呆子,哪个好人家的姑娘愿意往咱们这个大火坑里跳啊!”
屋内的穷书生虎躯一震,握在手中的竹简也随之微微发起抖来。
陈婆娘见岳老太太满面羞惭,一跺脚气道:“诶呀!你看我这张嘴呀。老嫂子!我可不是来笑话你的。我呀是想跟你说个事儿。老嫂子!你听说过幻界宗吗?”
岳老太太心中纳闷儿:“幻界宗?听说过呀!那不是传说中神仙待的地方吗?”
陈婆娘看了看四下无人,把嘴凑到岳老太太的耳边道:“老嫂子!前几天,我家三儿去镇里看二驴子,听到一个信儿,听说六月初八,幻界宗又要招人啦!这回就在唐皇庄那边儿开道场。
老嫂子!你跟岳大哥商量商量,要不让你家牤子也去试试吧,万一被仙家看中了,说不定将来也能做个活神仙呐,又会呼风唤雨,有会点石成金的,多好!咱们牤子要是成了活神仙,还怕没人愿意给咱们当儿媳妇儿么?到时候,你们俩不也能跟着享享仙福呀!”
岳老太太惊喜的道:“真的吗?林姐?”
陈婆娘:“小点声!老嫂子!可别吵的让全屯子都知道了。”
岳老太太满脸的感激,隔着篱笆拉住陈婆娘的手道:“林姐!你让老嫂子说什么好呢,我和你大哥绝对不会忘了你的好。”
陈婆娘抓住岳老太太的手笑道:“哈哈~!老嫂子,看你说的,唐皇庄离咱们这有好几百里,一路上净是些荒山野岭的,三儿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
你和我老岳大哥都是厚道人,你们家牤子也实诚,识文断字又有见识,不像咱们都是睁眼瞎的,让三儿跟你们家牤子一块儿走,我心里头就是踏实。
那么地!我给牤子出路费,让他骑我家毛驴走,一会儿你跟老岳大哥商量商量,再看看孩子是啥意思。
铲地的也快回来了,我得赶紧把菜洗了去。老嫂子,订好了给我个信儿啊!”
岳老太太提着篮子,一路踢里踏拉的跑进屋,口中连连低呼:“牤儿!牤儿!”
岳尊见老娘满面红光,老眼含泪,赶紧上前搀扶:“娘!怎么了娘?”
岳老太太目光烁烁,她压低声音颤声道:“祖宗显灵啦,祖宗显灵了呀!”
岳尊:“……娘!您别着急,坐下慢慢说。”
岳老太太抓着岳尊的胳膊,语无伦次的道:“坐不住!坐不住!牤儿,仙家招人啦!仙家这回又要招人啦!六月初八!对对对!就是六月初八!还剩下不到十天了,听说这回就在唐皇庄那边设道场。
牤儿!这回老陈家愿意给咱们出路费,还能借咱一头小毛驴,让咱跟着三驴子一块儿去。牤儿!这回咱们要是能让仙家挑中,咱们老岳家也能出个活神仙,到时候我和你爸也能沾到你的光了!”
岳尊一听心中阴霾尽去,也跟着高兴起来:“太好了!娘!”
提起幻界宗,岳尊就想起了一个传说。
故老相传,燕山深处有一个神仙门派,名叫幻界宗!幻界宗里面的神仙,人人都能腾云驾雾,个个都会呼风唤雨。民间也有很多关于幻界宗的传说:不论是降妖伏魔的、还是惩恶扬善的、又或者是治病救人的都有。
虽然人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幻界宗的传说,但是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够说的清楚幻界宗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人说它隐藏在燕山深处的群山之中,也有人说幻界宗其实是建立在云端之上。不管怎么说,凡夫俗子肯定是找不到幻界宗的。
凡人唯一能够见到幻界宗的机会,就是幻界宗每隔十数年,都会在燕山郡挑选一处城镇设立道场,随缘招收一些弟子或杂役。
听说,西边百十里地之外,有个叫佟家围子的地方,以前叫周家烧锅。六十多年前,就有一个姓佟的穷小子幸运的被仙家选中,成了一名仙家杂役。
相传,当初这个老佟家,曾经一度穷到连裤子都穿不上,一家子六口人,穷到只有一条棉裤穿,谁出门谁就穿着这条裤子出去,不出门的就光着屁股在家,围在被窝里遮羞。
自从佟小子被仙家选中当上杂役以后,每隔三五年,他就能往家里寄上几十两银子,没过几年,他家就盖上了大瓦房,还买了几十亩地,院里也停上了三驾大马车。几个弟弟还娶上了大户人家的姑娘,生了一大堆有出息的孩子。
三十多年前,这个周家烧锅就改名叫佟家围子了。
陈婶说,最近幻界宗又放出风来,据说下个月要在唐皇庄一带设立道场,听到信儿的人各个摩拳擦掌,打算去唐皇庄碰碰运气,万一被哪个仙家看中,从此也算是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了。
今天陈婶子提起幻界宗,岳尊突然想起桌上这块奇怪的铁牌子来。
岳尊平息了一下烦乱的心绪,他拿起书案上那块黑黢黢的铁牌子,心潮翻涌,想起了小时候偷偷跑到前山雷公坳里去玩的情景。
小岳尊天生愚笨,两岁才能翻身,三岁才勉强学会走路,五岁才磕磕巴巴的讲出人生的第一句话。村里的小孩们经常围着小岳尊跳起脚来唱一首自编的儿歌:
傻牤子,嘿儿嘿儿笑;哞儿哞儿哭,像牛叫。
傻牤子,啃手指;别人吃饭,他吃屎。
小岳尊当然还没蠢到吃屎的地步,不过也差不太多了。孩子们除了嘲笑他,就是欺辱他,没人愿意跟他一起玩耍。
大人们忙于生计,小孩子们又不愿意跟小岳尊一起玩,岳尊就只好自己一个人玩儿。
陈家村南不远,有一片常年雾气蒙蒙的山坳,这个山坳里草木葱茏,毒虫众多,还经常闹雷灾,今天劈倒一棵树,明天劈碎一块石头,村里人说这个山坳里有妖精,雷公这是在劈妖精呢!
因此,雷公坳就成了陈家村的禁地,大人孩子都不敢进去。
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大莫过二百五。
别人不敢进雷公坳,小岳尊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既然村里的孩子都不愿意跟自己玩,小岳尊就一个人偷偷的跑进雷公坳去玩,掏鸟窝,捞鱼,捉虫子……可以说雷公坳里记录了小岳尊许多美好的童年时光。
说起来,岳尊书桌上这块黑黢黢铁牌子就是在雷公坳里的小溪边发现的。
当时,它就镶嵌在一块裂开的大青石里,岳尊是用鹅卵石砸了好几天,才把它从那块大青石里抠出来的。
自从得到这块黑黢黢的牌子以后,小岳尊的心思也逐渐变得活泛起来。
也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小岳尊发现自己开始能够理解小朋友们的语言,甚至偶尔还能揣测出一些小朋友的心理活动了。
傻牤子不傻了,小孩子们纷纷对他刮目相看,岳尊的小伙伴也渐渐多了起来。
小时候,老岳家的家境也还算殷实,小岳尊很快被送进村东头的私塾里读书。也许是注定命里多舛,二十年来,岳尊屡次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
这些年来,由于常年累月在昏暗的小油灯下苦读,岳尊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就算下田锄草,都分不清哪里是草,哪里是苗。
好在岳尊生了一双灵巧的手,他早就已经暗暗的下定了决心,如果今年秋试不中,那就天天织席编篓,好歹靠着这门手艺也能养家糊口。自己要是勤奋些,再帮人代写信件,抄本书什么的,过个三年五载的,差不多也能把家里的债给还清了。
提起幻界宗招人这一茬,岳尊又想起这块从大青石里抠出来的铁牌子,拿起它来细细观察,牌子上面似乎带着些许淡淡的荧光,很奇异的感觉。凝神细看牌子正面的那些花纹,依稀可见几个浑然天成的古文——真仙令。
咦?真仙令?
岳尊的心猛然一阵狂跳,心中暗道:这块牌子果然是跟神仙有关的。从小到大,岳尊天天摆弄这块牌子。岳尊心里纳闷儿,以前怎么就从来没有发现这三个字呢?难道说,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仙缘来了?
既然发现了它是仙家宝贝,岳尊可就再也舍不得拿它来镇纸了。虽然炙热的阳光把木桌晒的很烫,真仙令入手却是一片温凉,这更让岳尊确信,真仙令一定是个仙家宝贝!小心翼翼的把它揣进怀里,岳尊暗暗下定决心,为了尽快还清债务,为了治好父母双亲的病患,这次一定要竭力寻找仙缘,争取能被仙家选中。
过一会儿,岳老爹扛着锄头回来了。
岳老爹把锄头挂在屋檐下的墙上,见岳老太太笑的满面春风,连眉宇之间多年以来一直郁结着的愁苦之色也一扫而空。岳老爹忙问:“他娘!这是咋地啦?莫不是咱家园子里刨出金元宝了?”
岳老太太把糠窝窝放到饭桌上,她一边连连摇头,一边合不拢嘴的笑道:“不对!”
岳老爹心中大奇:“难道是有人来给咱家傻牤子保媒啦?”
岳老太太继续含笑摇头:“也不对!”
岳老爹一拍脑门儿,恍然道:“看你笑的这么开心,一定是你身上的病全好了,对不对?”
岳老太太仍然摇头:“哈哈~!还是不对!”
岳老爹眨巴眨巴眼睛:“嘿~!还跟我卖关子。牤子!快跟我说,到底是咋回事儿?”
岳尊三言两语,就把仙家要在唐皇庄开设道场的事儿说了一遍。
岳老爹听完叹了一口气:“我还以为是啥天大的喜事儿呢,原来就是个这,看把你俩给笑的,没出息!”
岳老太太给岳老爹夹了一个糠窝窝道:“嗨!你叹个什么气?怎么就没出息了?”
岳老爹道:“这仙家道场好是好,老话说‘一人得道’那是‘鸡犬升天’呐!我太爷爷小时候就去参加过幻界宗道场,呜呜泱泱几十万人,那可真是人山人海呀。别的不说,就连大家撒的尿,都在路边淌成了一条小河。”
岳尊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岳老爹曾经多次讲起过祖上的这一段儿往事。
岳老爹咬了一口糠窝窝继续道:“兵过三千,接地连天。兵过一万,无际无边。好几十万人聚集在那一块儿,黑压压的人脑袋就跟无边无际的小麦地一样。人流拥起来,一浪接着一浪的。”
见岳尊露出恍然之色,岳老爹道:“明白了吧!这老么多人,仙家也就挑几个人带走,能被挑中的,那都得是祖上积了八辈子阴德的人家。
咱们老岳家,祖祖辈辈都是从土里刨食儿的,从我往上数个八代,别说念书当官的了,连个手艺人都没有,咱家哪有那么深的福分呐!”
岳老太太一听,心情也沉重起来,沉吟片刻以后,她不满意的瞪了岳老爹一眼:“哼!你就是这样,没多大出息,还竟说丧气话。
光凭咱家那几亩薄田,能够交税赋就不错了,连饭都吃不饱。拿啥修房子?拿啥给牤子娶媳妇儿?这回他们老陈家愿意出钱,我说什么也得让牤子去试一试。”
岳老爹道:“我也没说不让孩子去,我是让你们别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岳老太太给岳尊夹了一个糠窝窝道:“别听你爹瞎嘚嘚,这次咱们肯定能选上。等咱牤子成了神仙,到时候咱们不用花钱,牤子也能给咱领回来一群跟画上一样好看的大姑娘当儿媳妇儿。”
岳老爹也哈哈笑了起来:“哈哈!净想美事儿,还一群?能领回来一个就不错不错的了。”
岳老太太喝了一口白菜汤道:“他爹!你年轻的时候走的远,这唐皇庄到底在哪边儿?离咱们这有多远?”
岳老爹吞下一口糠窝窝道:“差不多是在东南那一片儿,大约是过了陶家堡往南,奔七家子那边去,徐相屯儿往南还得有四百多里呢,那边太远了,我也没去过。”
岳老太太放下碗:“听说陶家堡东边那个芦苇荡子里,张三儿可多了,牤子你们过那的时候,可千万多撺联点人儿,一定得白天走,可别贪黑儿过,再让狼给叼了去……”
岳尊连连点头:“知道了!娘!我又不是头一次出门儿,去年赶考的时候走过那条路,您放心吧!”
岳老太太道:“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张三儿就吃你这种满不择胡的。过了七家子那边道都生,哪条路上有劫道的,哪片林子里有狼虫虎豹,全得靠嘴勤多问,出门记得嘴甜点儿,别像个死橛子一样不爱吱声……”
岳尊咽下嘴里的糠窝窝应道:“娘!您就放心吧,还有陈三儿呢,那小子比猴还精。”
岳老爹直起腰杆道:“唉~!说起老陈家,咱们得记着人家这个情啊,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有朝一日咱们还得报答人家。
人都是三穷三富过到老,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老陈家也会有个为难招灾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咱们老岳家可千万别忘了伸出手来拉帮拉帮。”
岳老太太也说:“可不是嘛!别的不说,就陈三那么能败霍,多少钱能够他糟践呢?牤子!我跟你说啊,这一道上你可别跟他学坏了,什么牌局呀,青楼的,都得给我离远远的,那都是祸害人的地方,就算陈三花钱请你,你也不许去,听到没?”
岳尊把头点的跟鸡扦米一样:“知道了!娘!”
……
夜半时分,岳尊躺在炕上久久难寐。
书上常常描写,古时高人授艺,总是要预先考验弟子的品行,想来仙家也是如此,这次跟陈三一起去寻找仙缘,一路上一定要随时随地多行善事,说不准哪件事儿就是仙家的考验呢。
他悄悄的从火炕上爬起来,坐到书桌边,从怀里掏出那块黑黝黝的真仙令,翻来覆去的仔细端详。
黑黝黝的真仙令,表面很平整。借着皎洁的月光,把眼睛贴近了令牌仔细的看,依稀还能发现一些很淡很淡的细密纹理,这些纹理优雅的缠绕在一起,线与线之间竟然有一种辽远的感觉,好似隔着深邃的天空一般。
以前我怎么就从来没注意观察过它呢?这真仙令冬暖夏凉,在大青石里也不知道藏了多少年,历经多少风霜雪雨,却从来不曾生锈,显然应该是一件宝物才对。真仙令啊真仙令,你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宝物呢?
仿佛能够感应到岳尊的想法,岳尊掌中的界魂令突然泛起一层荧光,然后一股氤氲的白色雾气从令牌中渐渐缭绕了出来。
很快的,一缕又一缕半透明的雾气争相涌了出来,这些雾气有的是瑰丽的红色、有的是妖异的蓝色、有的是纯净的白色,还有的是神秘的黑色,它们互相撕扯着,咆哮着,争先恐后的想要从这块令牌的牢笼中挣脱出来。
岳尊发出一声短促而又低沉的惊呼:“啊!”
手一抖就把真仙令扔到了桌子上:“当啷啷~!”
令牌在桌子上当啷啷颠了几下,最后静静的躺在那里不动了!月光下,黑黝黝的真仙令还是往日那种老样子,并没有任何特别,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幻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