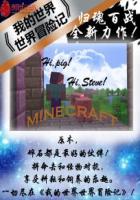既然他们赶尽杀绝的话,就别怪她心狠手辣了,城门处肯定会有马厩,到时候可以抢夺一匹骏马然后直接从城门处冲出,当下只得唯一这么一个办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留在城内死路一条。
说不定一手造成这样局面的老者就躲在暗处看着狼狈不堪的白苏逃亡,说不定她这些亡命逃杀只是上位者的一场赌局,比方说老者和城主的赌局,白苏成功逃亡哪一方就要付出代价,而另一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将白苏留在这里的这么一个游戏。
她不禁有这个想法,比一刀杀了她更惨,给她希望,却是绝望,得到功法也没用,要送出去才有用,但是城内又没有信得过的人,如果这本功法真的能够治愈瘴气病,那她死也值得了,但是一旦不值得的话,白涟也会死。
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而造成的思绪混乱还是想想其他能够转移注意力,不让伤口那么疼痛,逐渐间,伤口那种火辣疼痛感逐渐渐弱,这可不是好消息,第一是体温开始下降,第二是失血过多伤口氧气不足开始冰凉,无论是哪一个都于她不利。
快速奔跑间,一名身穿蓑衣头戴斗笠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冲出,他似乎注意到白苏的异状,那一霎那他就惊呼出声立马拔出武器迎面而来,尽管她不想再浪费体力,但是这场战斗是无法避免,不知道是距离过近还是其他原因,对方并没有拔出长剑。
而是取出一把带锯齿的匕首,哪怕倾盆大雨中,上面的锯齿也清楚可见,似乎让白苏能够看清楚一般,他的动作算不得上快,电光火石之间,他的匕首剑锋朝着白苏面门从上往下劈砍而来,似乎要将她好看的面蛋撕裂上一道伤疤一般,而这次她没有闪身后退。
没有受伤的左手取代了灵巧的右手,此时的右手根本没有力气去提起刀,更别说砍人了,她左手正持刀,右脚右挪,整个人平移而去,左手刀锋朝着对方的手腕关节用力劈去,这只是一般的切果刀,可不像可以刺可以插的匕首一般,这把刀只能用劈和砍之类的大开大合招式。
但这并不影响她那高超的技巧,在劈到对手手腕之时用刀锋朝着对方手臂从左往右一拉,锋利的刀锋插入对方的手腕再从手腕一路顺着筋骨往上拉,如同顺着纹路切牛肉一般,鲜血两溅开来,从她拉刀起,他的右手已经没有办法收回。
已经顾不上右手,如若再被白苏拉刀下去,说不定整条手臂都要被废掉,他左手握拳朝胸,利用左手手肘击打在距离极近的白苏前胸,这一下重击甚至发出闷响,打的她胸膛一闷,踉跄后退,划过去的刀锋也收了回去。
尽管一下击退白苏,但他的右手也废了,白苏可不会因为对方伤势而手下留情,持刀的左手顺势往右甩,紧接着反手用刀锋朝着对方的喉间而去,将没有反应过来的挡路人喉间破出一条撕裂伤。
在切喉之后,她第一次意识到手中武器并不适合她,当下发泄一般用刀尖朝着面前没倒下的男人腹部捅上一下,但是刀尖并不像匕首一般尖锐,用力的捅了对方腹部两下,他才不情不愿的捂着喉间跌落在地,鲜血打湿脚下的雨水。
给无色的雨水加上鲜红的染料,她扔下不适合的切刀,将对方那把跌落在地的锯齿匕首捡了起来,做完这一切都气呼呼,尽管喘着气,但她还是要尽快赶往马厩,在失血过多之前。
披在右肩上面的外套也是被雨水打湿,伤口一片冰冷,似乎从内部而来,而不是被冰冷的雨水夺走体温,走起路来似乎还带点摇晃,头也有点重,脚下步伐也带点轻。
她用力的甩了甩头好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光返照一般用力的吸了两口气,整个人腰杆也挺直了起来,当下她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奔跑,已经能够看到不远处的马厩,马厩似乎在一个类似于集市的热闹场所当中。
所幸的是集市大部分摊位都是露天的,没有屋檐让人躲雨,在穿过通入集市的圆形石头拱门之后,她都能够看到整个马厩,那是一栋类似于箭塔一般的高型建筑,上边的窗户突出一支旗帜,上面有着这个城市的标志。
建筑旁边有着一个巨大的石蓬,还有着可以朝两边打开的木制推门,想必那个巨大的石蓬就是马匹的圈养处,说不定推开推门就能看到里面一片片绑在木栏杆里面的马匹。
尽管她努力的让自己隐藏,但是两名身穿轻皮甲的城卫军打扮的看守马厩的士兵还是发现了她,当下其中一名手持长枪的卫兵伸出手指住白苏大喝道,白苏并没有退缩,而是朝着二人冲锋而去。
她可不能在二人干扰下抢夺到马匹,在对方招惹多的人之前还是尽早解决好,似乎她这个冲锋激怒了卫兵二人,他们似乎认不出白苏是通缉犯,还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当然白苏更倾向后者,但愿这些人还不知道她被通缉了,好让她通过城门。
当下手持长枪的卫兵双手紧握长枪握柄,锋利且尖锐的枪尖朝着白苏喉间而来,她立马朝着右边闪去,但他的攻势随之一改,直插改为横挥,尖锐的枪尖似乎有灵性一般,剑锋朝着她的喉间划来,当下她只好脚下用力踏下,身影借助这股力朝后跳去。
但他的攻势如同节节暴升一般,一枪接着一枪而来,他改横挥为直刺,做出一个标准的直刺动作,手中长枪先是往身后拉,紧接着爆发力量一般,枪锋朝着白苏脑门而去,如果被刺中的话绝对多出一个透明窟窿。
果然每次后退都不是好结果,不是被追打就是被连式,她暗骂一声,左手的锯齿匕首正持,从下往上,朝着他直刺而来的枪锋而上,一下将击打而来的枪尖打偏,紧接着她脚下步伐连动,整个人贴着长枪枪棍而进,手中匕首更是在对方惊骇的眼神中插入他的眼眶,连惨叫都来不及就去报道了。
另一个手持着长剑从左往右朝着白苏胸膛劈砍而来,尽管这一剑极其迅速,但还是让白苏险险躲过,剑锋几乎是擦着她的衣衫而过,当下她手持匕首,一个闪身,用撕裂性的锯齿匕首插入对方的腰间一带而过。
他整个左腰几乎被斩开,但是要比斩开要残的多,一条巨大的撕裂伤口使他失去了最后的战斗力,持剑的手都软了下来,她过犹不及的将匕首捅入他的下颚,就和之前一样,将他残忍的杀死。
她将匕首收回腰间,拾起对方的长剑,在马背上短短的匕首可不管用,连别人的衣角都砍不到,尽管在马背上肯定是长枪更管用,但是此时的她只能用左手,没办法动用两只手手持长枪的情况底下还是长剑比较好,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看管的原因。
马厩的推门并没有锁,她用发出剧烈疼痛的右肩撞开推门,进了马厩,走到最近的一匹骏马旁边,她身上不知道是不是湿透的缘故,尽管有伤口,但是鲜血没有刺激到眼前的骏马,她几乎用尽全身的体力才踏上马鞍,闻闻的坐在马背上。
她左手手持着长剑,还拉着缰绳,脚下马鞍踢了一下马腹,马儿吃痛开始朝着她控制的地方而去。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分,哪怕是早上,天空也是一成不变的乌云暴雨,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才能结束,她毫无血色的嘴唇抿了抿,现在只是凭借一口气才不倒下,肩膀因为失血而一片冰冷,说不定失血过久才治疗哪怕她的命没事,说不定她右手都因为缺血而坏死。
她得抓紧时间了,马厩距离城墙不远,但是面对白苏这个通缉犯,城卫军明显很为重视,当下为了对付白苏,卫兵们举着戟围成了一条警戒线,让她吃惊的可不是有备的城卫军。
而是那些身穿白袍上面有着银桦叶子不同颜色的弟子们。
银桦宗。
看起来之前那一笔帐是要现在结了,尽管她不认为她是那么多人的对手,但是不战就降可不是她性格,当下她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她直接朝着卫兵组成的警戒线冲了过去,脚下的马鞍用力踢打而去,似乎感觉到主人的心情一般,它嘶吼一声,人力而起,随即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去。
一直警戒着的卫兵又怎么不知晓周边的事,从白苏骑马冲锋而来,他们就分散开来,以不同的站位,身子伏低,手中长戟对准冲锋而来的白苏或马匹。
她在马背上,踩着马鞍的双脚紧夹,手中长剑高举,在冲锋距离足够的时候将长剑用力挥舞而下,靠的最近的一个倒霉鬼头骨直接被剑锋敲烂。
她手中长剑剑势转变,从劈转撩,下一刻将旁边挡路的卫兵长戟直接砍断,还在对方身穿护甲的肩膀上留下一道长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