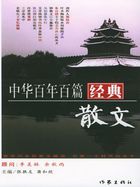夜色如水,两匹青马沿着跃马岭官道缓缓向南而行。
马上两人都是儒生打扮,其中一匹马背上驮着一个包袱,乘客似要远行,正是吴阚平和李念生。
只听李念生说道:“阚平兄,帝都豪门林立,没有靠山难以立足,你可要想好了!”
吴阚平遥看前路,眉峰紧锁道:“两年前是丁家屯的丁成才庄主,去年是细柳营的段东家和龙川福祥商行的钱东家,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被将军府捉去,散尽家财才勉强保住性命。”
“今年轮到了俞家,俞侯爷下狱,偌大的俞氏分崩离析,连小小的沈家酒坊都成了强盗匪窝,就因为越兄弟姓俞!整个苦茶镇几乎被夷为平地,死伤几十人,沈掌柜和俞越小兄弟不知下落。下一个又会是谁?”
吴阚平的目光落在李念生脸上:“或许是你,或许是我。大玄究竟还是不是大玄之天下?不管有多难,我吴阚平都要试上一试,纵死无憾!”
李念生默然不语,良久方道:“惭愧啊惭愧,可恨念生却没有阚平兄有这般志气。”
吴阚平微笑道:“念生这是说的哪里话,若不是你冒险替为兄打通关节,我如何能走的出龙川?这份恩义吴阚平铭记在心!”
李念生道:“此去帝都千里迢迢,阚平兄一路珍重。”
吴阚平抱拳拱手:“念生兄,就此别过,有缘再见。”说罢双腿一夹马腹,那马哒哒哒四蹄翻动,越跑越快,转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
……
……
有了血月神舟,终于不用再受风沙之苦,俞越每日吃饱就睡,没风沙的日子就躺在甲板的椅子上欣赏大漠风光,偶尔跟须延陀喝喝酒,斗几句嘴,倒也逍遥。
自那日以后,须延陀绝口不提破魂枪,似乎忘记了这事。
又走了十几天,巨船逐渐慢了下来,拉船的驼群也少了许多,沙丘之中偶有几株不知名的灌木。再往前走,黄沙之中稀疏的长着许多或高或矮的红色怪树,树干扭曲,树皮沟壑纵横,或许已是深秋,树叶一片金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一片高大的沙山连绵起伏,巨船在山中穿行,驶过一个狭小的山口,眼前豁然开朗,沙山怀抱之中出现一片开阔的沙湾,平滑如镜,犹如同一座波澜不惊的巨大湖泊。
沙湾三面用大石砌筑,防止沙山崩塌,山腰一片石屋高低错落,足有数百间,入口两侧山顶是两座巨大的石头堡垒。
问过侍女,才知道此处名叫沙港,血月神舟的停泊的“港口”。
巨舟缓缓驶入湾内,靠着“码头”上,一群白袍大汉解开驼群身上的绳索,系在石墙上的铁环之上,又取了许多巨大的石块堆在大船头尾之下,抛下巨锚,将船牢牢栓住。
血月神舟已是穷奢极欲,不知耗费多少钱财才造得出,没想到为这巨船专门营造的沙港也如此宏大,又得消耗多少心血、人力和财力?
俞越暗暗称奇,如此巨大的工程绝非一日之功,恐怕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营才行,须延陀果然是个二世祖。
在沙港停留了不到半天,俞越便被人带到一处队伍之中,跨上一峰骆驼,随着驼队,缓缓向北行进。
队伍不徐不的走了两天,地上的草木渐渐多了起来,想必即将走出大漠,这两天俞越再没见过须延陀。
第三日一早,穿过一片乱石丛生的戈壁滩,眼前呈现一幕奇景,只见一片白雾接地连天,犹如一堵看不到边的高墙横亘在天地之间,突兀的将大漠割开,仿佛到了世界的尽头。
也不知那白雾不知从何而来,又如何在烈日暴风下的大漠之中而凝聚不散的。
一阵风吹来,那白雾随风变幻,一缕缕一团团纠缠在一起,被阳光一照,七彩缤纷,令人目眩。
驼队停了下来,有人大声的说了几句什么,驼官取出一条粗大的麻绳套在骆驼脖子上,把绳头递给前面的驼官接上,如此一根接一根,半个时辰后,所有的骆驼都连成一行,这才吆喝一声,向白雾中走去。
俞越心道,想必是白雾中难以识路,唯恐走失了,俗语说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便是一条绳上的骆驼。
白雾轻薄如纱,弥漫在四周,行走在白雾间,颇有几分飘然出尘之感。
往前走雾气越来越浓,阳光几乎全被白雾遮挡,只能隐隐看清驼队的影子,到后来居然伸手不见五指,根本不知脚下的路在哪里,若不是跟着队伍,恐怕早就迷失在这片白雾之中了。驼官们不住的吆喝,此起彼伏,短促而有节奏的前后应和,应当是一种相互提醒的法子。
走了大约三四个时辰,空气变的潮乎乎湿漉漉的,好像来到水边,白雾渐渐稀薄起来,隐约能看清周围状况。
终于,有阳光投射下来,俞越暗暗松了口气,走在白雾之中,目不能视物,跟在无星无月的黑夜中没有区别,甚至更加让人压抑和恐惧。
透过薄纱似的白雾,隐约见前方出现一座大山,山势险峻,峰峦直插云霄,这么一座大山在数百里之外就应看的清楚,不知为何只到近前才发现,如同从天上掉下来一般。
行至山脚,只见树木丛生,一片郁郁苍苍,见惯了沙海单调的苍黄之色,这团浓绿让俞越不由精神一震。
一条狭窄的山道蜿蜒向上,仅容一头骆驼通过,驼官们把绳子解开,鱼贯而行。
驼队越走越高,一侧便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向后望去,见白雾氤氲,已然看不清楚来路。
又在山间走了一天,地势渐缓,山道也变的宽阔起来,走了莫约莫约四五十里地,远远的见前方两座山峰耸立,两峰之见是一道石墙,足有五六里地,全由厚重的麻石砌筑而成,高达十余丈,生满了青苔,显然是年深日久。
大路的尽头是一座巨大的城门,两扇城门都由厚重的木头制成,外包铁皮,缀以铜钉。城楼之上有身披铠甲头戴遮面铁盔的武士来回巡查值守。
驼队停在城门前的空地上,须延陀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头戴金冠,腰束金带,坐在一头雪驼之上,再加上他高大的身躯,显得气度不凡。
须延陀遥指城门对俞越道:“此地便是我须延部王庭所在,大漠第一雄城——永远攻不破的巴托亚吉城!”
俞越点点头,这座大城隐藏在白雾之中,又有高山之天险,易守难攻,加之城墙坚固无比,防守严密,可谓固若金汤。
就在这时,城门洞开,两排精壮的胡人武士分立两侧,个个挺拔如松,背弓跨刀,显得十分威武。
跟着又走出一群白袍人,有老有少,俱穿着华丽,神采飞扬,应是部族里的官员贵族。
当中一位白发老者满脸堆笑,走到近前,手抚左胸对须延陀躬身一礼,叽叽咕咕的说了几句。
须延陀坐在雪驼上微微点了点头,回了几句话,便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之中向城内走去,俞越由几名仆从引领着跟在后面。
穿过长长的城门洞,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此城建在一座巨大的山谷之中,从城门高处望去,近处是一片麦田,足有数千亩,按说这个季节麦子已经收割完毕,这里依然是绿油油的尚未成熟。远处又有一道城墙,隐约可见里面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的房屋高低错落,沿着山势一层层排列过去,一眼望不到边。
城内十分整洁,房屋大都是青石所造,与大玄的房屋样式迥异,别有一番异域情调。街上店铺林立,行人熙熙攘攘,甚是热闹,大多身穿白袍,女子用黑布将头裹住,面罩黑纱。
路上行人见到须延陀一行人,纷纷肃立在街道两侧,向须延陀躬身抚胸行礼。
走不多久,来到一处广场,正中高耸着一栋巨大的宫殿,尖顶圆柱,墙上雕刻着繁复的纹饰和弯弯曲曲的文字,显得庄严肃穆。
大门左右竖着两根石柱,柱顶是两尊高达十余丈的雕像,一尊满脸悲悯,俯视众生;另一尊手举弯刀,横眉立目,威猛之极。
须延陀朝身旁一人耳语了几句,便领着几名身份颇高的贵族走进宫殿大门。
一位年轻贵族毕恭毕敬的将俞越请上一辆马车,送到一处宅院之内,用生硬大玄话告诉俞越,此处是埃米尔专为贵客准备的住处。俞越不知道什么是埃米尔,或许是须延陀的称号,类似族长,国王之类。
没想到这须延陀身份如此尊贵只身深入龙川,杀戮镇西军官,挑衅风从虎,而他的部族竟然也允许他以身犯险,胡人所为果然不能以常理度之。
宅子里有三男一女四个仆人,供俞越驱使。这些仆人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显然是修习过武道。俞越暗忖,这哪里是仆人,分明是来监视的,须延陀还真看得起自己,以现在自己的修为,难道还能从这固若金汤的大城逃出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