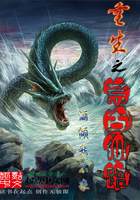亦珺,中秋节那夜回寝室之后,我虽去顶楼阳台跟他说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话,给他讲了许多笑话,但在这之后,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是不是蜷缩一团看风吹起的窗帘,整夜无眠。
高二上学期临近期末的时候,亦珺接连好几天都没来上早自习,来上课的时候眼圈老是红着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起晚了,眼睛是被寒风吹的。
有天,我决定去他家等他一起上学。他家那段路有什么店有多少电线杆我记得一清二楚,以前每次晚自习后,他送我回家,可是走到路口时,我不舍与他那么早分开,便说,我送你回去吧,然后我们绕着步行街转一大圈,我老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他笑着听,偶尔也和我争辩几句,然后就慢慢走到了他家,可结果还是他以女生夜路不安全的借口把我送回来。
我记得那天我特别怕,因为起的太早了,冬天的夜又特别长,昨夜下起了大雪,路上只听得见我咔嚓咔嚓有节奏的脚步声,然后各种拐角处出现一个拿着电锯的人或雪女的故事一一在我脑袋浮现。
我走的飞快,走到他楼下时,顿时舒了口气,他有一种能令我心安的魔力。我发现四楼窗户还亮着灯,便急急忙忙跑了上去,在楼梯口,却看见他被谁给推了出来,重心不稳,一下跌坐在地。
屋子里响起男人暴怒的声音,“你妈呢?”说着就听见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钱藏哪了?你个小畜生。”
亦珺冷冷地回,“小畜生还不是你的种,你这辈子也别想见到我妈。”
昏暗的楼道灯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只看见他穿着薄薄的衬衣,身体止不住的颤抖,我才知道,哪怕头顶同一片太阳,总有人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生长,很快,我听见一声尖叫,它来自我的喉咙。
亦珺震惊地回过头,我看见他颧骨有很深的淤青。我还没醒过神来,他就拉着我飞快地跑了。
后面是那个男人——应该是他爸粗暴地询问,“谁在那?”
他拉着我一直到他家附近的小学操场,白茫茫的世界映的他的身影原来这么单薄,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难过过,眼如灯灭。
我不顾他的反抗急忙把自己的外套、围巾、手套通通给他穿戴上。
然后,他哭了,那种压抑的隐隐的无声流泪,他抱着我,把下巴抵在我的肩膀,平时高大挺拔的他现在柔软脆弱地像一个棉布娃娃,声音因哽咽而沙哑,他说,“若素,只有你才让我感觉温暖。”我能感觉他的泪透过我的毛衣,寒冷侵蚀我的皮肤。
亦珺他告诉我,爸爸是赌鬼,欠下巨额赌债,逼得妈妈两年前不告而别,他一没了钱就来找他,踢他,拿皮带抽他,让他说出妈妈的下落,可是他也不知道,只是自己那张银行卡会不时地收到匿名寄来的钱。
“那是妈妈,我肯定。”他把我放开,我看见他眼里燃起又瞬间黯淡的光,他说,“可是她为什么当初不把我一起带走?”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我要一辈子给他温暖,让阳光照进他的生命里。
那天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有时候捂着肚子,疼的汗大颗大颗的直往下滴,一直那么恶劣生活的他,还每天都拿笑脸对我。他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所以每天早上都会带饭去学校,妈妈看我保温杯里粥一盛就是满满当当的就用无比惊讶的眼神瞅我,我说,你女儿胃口大你又不是不知道,然后去买他喜欢吃的小煎饼,看着他吃的喷香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云端漫步。
我抬头望了一眼紧闭的门,心生内疚,因为不是他们,因为没有体会到那种切肤的痛,所以我们永远不理解他们因伤害而敏感的心。
但是亦珺还有我,端岚一个人外地求学,从没见她有什么很好的朋友,去教室、食堂,甚至回寝室她总是形单影只。
她是不是很孤独?
与此同时,疾步穿过狭长走廊的端岚慢慢在转角口停住了脚步,来来往往不时又互相挽着胳膊牵着手的女生,或两两成双,或三五成群,在走廊反射穿梭的欢快笑声在孤独者的耳里愈发如巨潮般汹涌而至,一声声拍击耳膜,拍打心脏。
她以为她的心脏已经麻木了,可竟有微微的羡慕和疼意传来。
不是不想和她们一样,肆无忌惮的,想笑便笑,想大声说话就放开了嗓门。
不是不想做这般明媚的女子。端岚攥着书包带子的手有些无力地软软垂下。12年来的冷漠、嘲笑、排挤早已将这些明快的色彩吞噬,没于她看不见的巨大的黑洞中,她的情绪甚至整个世界都是暗暗的灰色,像此时的天,乌云层层,看不见光亮。
她站在原地,出了神的眼睛毫无焦距,片刻,她从书包里掏出手机,颤颤巍巍地拨下那个她最不想拨但记得比自己生辰还清楚的号码。
尖锐而沙哑的中年女音从那边传来,“打过来没?要不然不能说我不给他吃的了,实在是太穷了。”
端岚眼前浮现那个瘦小的身躯。她说,用那种许久未开口因而自己都觉得不像自己的声音说,“等会就去。”
说完那边就传来嘟嘟声,端岚无奈地握紧手机,匆匆朝校外ATM机走去。
刚刚那句“如丧考妣”把河东狮弄得现在神色十分尴尬,她张着嘴发愣,半晌才小心翼翼出声,“楚啊,这.......我......”
楚哥说,“得了,姐姐,等她回来你就别再说什么了。”
“对对对,我们会帮你试探,不过我认为她应该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我帮她把脸上的面膜扶好,这时,手机铃声大作。
电话里蓝轩昂大吼大叫,“姐姐,你怎么还不来啊,我想吃桂林米粉,多加点花生。”
看下钟,原来都已经五点四十多了,楚哥笑的贼猥琐,“又是你那老相好啊。”
我长叹一声,“如果是,你觉得我会是这个语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