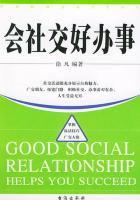翌日清晨,思雨还没有起床。我便独自一人闲逛,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华林园。园中各种名花争奇斗艳,我的心却全然不在这些花上。突然,似乎撞到了什么,然后听见了孩子稚嫩的啼哭声。低头一看,一个孩子摔倒在地上。我连忙去扶,还没等我碰到他。就被一个突然赶来的人推倒在地,嘴里骂道:“大胆贱婢,竟然胆敢冲撞太子,还不快跪下。”我连忙跪了下来,皇后也闻声赶来。见娇儿仍然啼哭不止,连忙抱过来哄着。那个看似是孩子奶妈的女人也连忙跪了下来,慌张的解释道:“奴婢正与太子一起捉蛐蛐玩,不想这个不长眼的奴婢突然跑了过来,撞倒了太子,奴婢未能护太子周全,请娘娘恕罪,请娘娘恕罪!”奶妈磕头道。
皇后一边柔声哄着怀中的孩子,一边将盛满怒火的目光投向我。我正不知所措,司马攸却恰巧经过。
“桃符给皇嫂请安。”他满面含笑的走了过来。
“王爷今日得空来宫中走动?”皇后也敛了怒色。
“皇上说,桃符出去游历这些时日,没人陪他练剑,很是技痒,所以今日特召桃符进宫与他切磋。”
“既然如此王爷快去吧,不要在这儿耽误了!”
“不急,这是桃符送给太子的小礼物。”说着,他将一个精巧的竹笼送到太子的怀中。太子看到这个漂亮的蛐蛐笼子,突然止住了哭声,拿在手中不停的把玩。他看似无意的瞟了我一眼,笑道:“你就是阮步兵家的女儿—阮玥?”
“王爷也认识这位阮姑娘?”皇后惊疑道。
“桃符怎么会认识呢,只是进宫不久就听说宫里多了一位画师,画技十分出色,而且竟是阮步兵的千金!”司马攸笑道。
“还不参见王爷?”皇后怒目喝道。
“小女阮玥参见齐王!”我行礼道,心里却极为难过。没想到正式的像他介绍自己,竟是这样的情景。
“你冲撞了太子可是大罪,你可知罪?“他正色道。
“阮玥知罪”。
“有罪就当罚,该如何罚你呢!”他又摆出一副苦恼的样子。“皇嫂,你说该如何罚她?”
“王爷以为呢?”皇后笑问道。太子止了哭声,皇后的情绪也变得平和了很多。
“皇嫂,若问桃符,那桃符可要讨赏了!”他一脸坏笑的瞥了我一眼。
“王爷请讲,相信皇上也会同意的。”皇后眸光一亮,欣喜道。 “皇嫂说笑了,桃符只是听说,阮步兵家的女儿作画师从卫协,画功了得,所以请皇嫂令他为臣弟画幅画,可使得?”
“如此,也算罚吗?”皇后笑道。
“还请皇后给桃符这个面子!”
“既然如此,若不答应,就是本宫这个皇嫂太过小气了,本宫就把她交给王爷,是罚是作画,听凭王爷。”
皇后离开后,他将我扶起。“那日的事你还怪我吗?”他将玩世不恭敛去,眸光像一汪深不见底的潭水。他只是说了这几个字,我心中便觉酸涩不已。
“没想到你是齐王。”
“这不重要!我只想知道你还怪我吗?”我握住我的双肩,仍旧问道。
“你在乎吗?”我不答反问。
“当然!”他肯定道。
“你在乎那日就不会转身就走!”想起那日的事我又委屈,又气恼。
“那日我只道你误解我,一时气盛,可我很快就后悔了,可我回去时,你已经走了!”他解释道。
“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走就走吧,还回去做什么?”我赌气道。
我心里正难过,谁知他竟一把抱住我。那时与他相逢,虽然心会砰砰跳,后来与司马炎在一起时也有过同样的感受,但那似乎都来自于陌生男子靠近时情不自禁的悸动。可此时,我既委屈又高兴,竟也有抱住他的冲动。也许在我心底的深处,十分想念这个男人。虽然,我很想沉溺于这个怀抱,但我不能,我只能一把推开他。
“皇宫不适合你。”他突然说道。我想他是误会了我推开他的原因。
“我知道,只是人生之事,大多身不由己。”我转过头,不去看他。
“那日在承阳宫外见到你,我还以为你已经是皇兄的嫔妃了。”他用力将我的身子板了过来。
“我虽不是,但皇上也不会允许我出宫,更不会允许我思慕其他男子!”我义正严辞道。
“你是说皇兄不允许?”他惊异道。我以为我已经说服了他,心里虽有些失落,但也觉得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谁知他竟说:“那你是否思慕其他男子呢?”他急切地渴望着答案。
之后,我们陷入了一片沉默,他只是深情的盯着我,我却呆呆地望着他,然后慌乱地躲避他的目光。
“记得,你欠我一幅画!”他忽然留下这句话,便匆匆地离开了。
当日,晚膳过后。皇上忽然驾到。我和思雨都吃了一惊。思雨悄悄的退了出去。只留下我和皇上。他背手而立,很长时间都没有说一句话。
“皇上,我去给您倒杯茶!”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我只好先开口。
“不用了,我只想和你说几句话。”他开口道。 “皇上请说。”我心里不安,总觉得他要说的话与司马攸有关。
“听说齐王让你为他作画?”他转身看着我,深沉的眼眸看不出什么情绪。
“是,皇后说~”我急于搬出皇后,可未等我说完,他便打断了我的话。
“我让他不要打你的注意,”他顿了顿,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因为你是朕的女人。你猜桃符怎么说?”他的语气淡淡的,眼神却深沉地可怕。
“阮玥不知!”我低着头,不去看他。不知道他到底想怎样。
“桃符说窈窕淑女,君子好求,更何况眼下你还不是朕的女人。”我的心好像已经跳到了喉咙,却只能强装镇定。
“你呢,你怎么看?”他突然认真地问我。
“阮玥只是奉皇后之命为齐王作画,并无其他。”无论如何,他是皇上。他的皇权,足以让任何人攀附,也足以另任何人畏惧。太多人想离他近一些,但靠得越近,就会越如履薄冰,步步为营。总有一段距离,任何人都不能跨越,即使是自己挚爱的女人,或是自己至亲的兄弟,司马攸不怕,但我不能不替他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