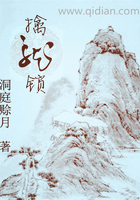云无心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这下好了,剑没拿到,反把小命儿给赔上了,这山下怎么尽是骗子?”
桑柔默默地坐了下来,清点着随身携带的干粮。长鱼酒坐在她身边,在静默中看她慢慢把干粮取出来,又放回去。
“那是否意味着……师姐你,也是骗子。”云樗冷冷道。
他的脸色是出乎意料的阴沉,他说出来的话是出乎意料的惊人。长鱼酒和桑柔都懵了,更别提云无心自己了。
“小樗,你在说什么……”
云樗不耐烦地打断了她,“你三番两次离间我们三人的关系,又总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说丧气话,好让我们知难而退打道回府。你还让我们不要相信端木前辈。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他冷冷地看着云无心,就好像在看着一个陌生人。
“但我知道,你的目的就是阻止我们找到风沉渊,阻止我们揭开关于大宗师的秘密。江湖乱,宗师现,你们唯恐当今世道不乱,于是千方百计阻挠大宗师出世。很好,现在你已经成功了。”
桑柔忙劝道:“小樗,你怎能这么说你的师姐?快道歉!”
云无心显得很伤心,可当她开口时,语气却是从前未曾有过的镇定,镇定得让人心里发慌。
“小樗,你不要胡闹了。知道吗,你在姑射山的罗盘已经非常不稳定了,罗盘上到处燃着星火,随时都有被焚毁殆尽的可能。师傅此番遣我来保护你,正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我比大师兄更加适合这个任务,我也有十足的信心完成师傅的任务,将你平安带回姑射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云樗张了张嘴,似乎仍然想要辩驳些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最后,他生硬地开口道:“我还是不相信你,除非你能证明给我看!我现在困了,想睡觉。”
说罢,他便将头靠在冷硬的石墙上,当真睡了过去。
云樗那孩子气的举动引得长鱼酒哭笑不得,他轻叹一口气,打趣道:“没想到这一次,咱们又给女人骗了。”
云樗没有回答他,竟然是真的睡着了,均匀绵长的呼吸声回荡在牢房狭小的空间中。
“你们两个啊,若是再不长些心眼,以后还得被咱们女人骗。”桑柔强颜欢笑着打趣道。
“如果还要下一次机会的话。”她小声道。
云无心从腰间拔出马头长剑,又从怀中掏出一块干净的丝绢,从头至尾小心翼翼,一遍遍地擦拭着剑身剑锋剑鞘,仿佛在爱抚自己的孩子一般。剑锋被她擦得雪亮雪亮,在黑暗中盛放幽幽的光彩。
桑柔终于将携带的全部干粮清点完毕。
“还够吃一个月。”她轻声叹息道,“我们四个人,只够吃三十天了。”
长鱼酒道:“那些狱卒不是会定时送饭过来么?”
桑柔肯定地说道:“那饭菜肯定有问题,不然那些江湖人也不至变成如今这般癫狂模样,这饭菜肯定是被下了致幻的迷药。”
长鱼酒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有理。”
桑柔叹了口气,将头枕在长鱼酒肩上。
“这两日,大家都少吃些吧,能挨一日是一日。”
长鱼酒伸出一只手,轻轻环在了她的腰际。两人就这么静默地并排坐着,听洞外隐隐绰绰的风雪碎玉声,碎成万千晶莹珠玉,仿佛蜷缩在烧着火盆的温暖屋子里,外面是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而屋内是这世上唯一安全的地方,他们尚可偷得一日安稳清闲。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堂里读书声朗朗,泥土的清新味道从花园另一边飘来。吴起斜倚在窗边,目光不时瞟向窗内读书的学子们。
那些稚嫩青涩的面庞,多么像当初的自己。不过时间是不等人的,他也再回不去当初意气风发的状态了。三个月前,通过岳丈田居的举荐,他在穆公手下混了个芝麻小官,无足轻重。好在聊胜于无,他总算距离自己出将入相的志向又近了一步,哪怕只要小小的一步,却也是可喜的。
他有了妻室,有了牵绊,不再只是自由自在、潇洒无度的一个人了,他注定要负担更多,也注定要承受更多,可他义无反顾。
不知何时,曾参已经来到他身后,用温和的目光静静注视着他。
寂静的学堂里,莘莘学子们还在认真研习着《论语》,曾参的声音压得很低,尽量不打扰到他们。
吴起的眼神有一瞬间的空白。
“六年了……”他叹了口气,轻声道。
时间过得真快,距离那个鲜血淋漓的绝望雨夜,已经过去整整六个年头了。
曾参又问:“想家么?”
“想。”
微风轻轻拂过,唤起吴起心头最温暖的记忆,那是独属于家的温暖记忆,最真实,最不可忘记。
“年关将至,大伙儿都忙着收拾包袱回家过年,你也回去看看吧。我听说,你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你打小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现在你又走了,家里便只剩她一人了,怪冷清的。今儿个你若是回去,她定会很高兴的。”
出乎意料,吴起摇了摇头,决绝道:“我不回家。”
曾参皱紧了花白的眉头,显然对吴起的回答颇为不满,“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离家六年,却一次也不曾回去探望过你母亲,是为大不孝。说说看吧,你为何不想回家?”
“不想回就是不想回,哪来那么多缘由呢?”
吴起叹了口气,又道:“六年前,在我离家远走的那个雨夜,我曾亲口向母亲发下誓言,若不为大国上卿,不出将入相掌天下大权,我吴起誓不回家。可如今我依旧没能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在齐鲁一带混了那么久,却依旧是个不入流的芝麻小官,即便我回家了,依旧还是会想家,拼命地想,想得要命。不如不回。”
曾参的脸上有了怒意,他没法理解,也不愿理解。他冷哼一声,道:“宁愿天天在外流浪想家,却不愿回家,真是莫名其妙!”
吴起摇了摇头,轻声道:“我并非不愿回家,夫子,难道我现在不正试图回家吗?我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在领我回家,每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难道不是这样吗?已经快了,快了,我马上就要到家了。”
他凝望着碧蓝如洗的青空,似是一个人自言自语,透出一种独酌无相亲的寂寞。
“我不管你在说些什么,在你拿出实际行动以前,任何言语的辩驳都是苍白无力的。”曾参脸上怒意依旧,并未因着吴起的一席话有分毫转变,“你太自私了,一味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你又何曾为你母亲着想过?她何罪之有,竟要受如此冷遇?”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你母亲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曾参说完冷冷一拂袖,转身离去了,只留下吴起一人倚在窗边,心神不宁。
一年后。
吴起心神不宁地坐在墙角下,也不管那墙是不是危墙,会不会忽然倒下来压着他,这一切他统统都不想管了。
在鲁国摸爬滚打了七个年头,他终于混到了官位,离大权在握仅有一步之遥。只要再进一步,他就能达成期盼已久的愿望,兑现他当初对母亲发下的誓言了。
然而现如今,这个誓言已经失去了意义。
因为他再也不会回卫城了。今晨他刚刚接到乡里的信函,得知母亲不久前已过世了。他对着那封皱巴巴的信看了许久,直到悲伤彻底麻木他的心,直到他已经痛到习以为常,痛到漫不经心。
母亲走得很不放心。
信里说,母亲亲临走前一直都很想见他最后一面,却终究没能达成心愿,最后还是带着无尽遗憾离开了人世。
要是这世上没有遗憾,那该有多好。大家心里都好受。
消息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他还来不及更加悲伤,便拖着沉重的脚步出了门。他本是要去官府的,那里还有一大堆官文繁务等着他去处理。
可是双脚却不听使唤地带他到了学堂。
唯有在这个地方,他才敢放肆地嚎啕大哭,把心底郁积已久的痛苦全都发泄出来。
他在繁花盛放的墙角下孤独徘徊,听远处学子们郎朗的读书声,细细回味过往的点点滴滴。
这一切,唯有他一个人独自品尝,又独自咽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来与他分享,那是独酌无相亲的寂寞。
原来六年前那个雨夜,是他跟母亲的最后一面,一转身就是永别。那时候他还咬下自己的皮肉,蘸着鲜血信誓旦旦向母亲许下青云誓言,然后一转身,就把她丢弃在了大雨中。
这记忆最真实,最无法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