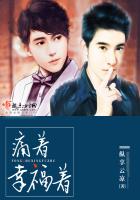看向安宝,发觉她还睡着,伸出手将她的额上汗湿的发理开,手指忽然一顿,即然游移到她咬破的嘴唇上。
双眉一凝,手心似乎有些湿热,抬起手,竟是血红一片,急忙拉起她的手腕,只见,手腕上的白带早己经脱落,昨日的伤**露在宽气中,血痕遍步,鲜血淋漓。
心脏一紧,像被人死死捏住,双用力绞动,疼的不可抑制。
早己猜到昨夜她是如何自己挺过这难熬的一夜,疼惜和无力似泉水一般涌上心际,涌至喉间,吞咽不下,又上涌至尖,涌出几缕酸气,直至眼眶,微微发热。
轻轻的执起她的手腕,送到嘴边,落下极轻的一吻,纵是这般轻柔,却仍让她皱起了眉头。
容逑征了一下,忽然起身出去了。
很快,他便回来。
手里拿着药箱。
仔细的清洗,认真的涂药,耐心的挑出她伤口里的每一分碎屑,其间,还要不停的观察她的反应。
待一切结束,天色己经大亮了。
安宝被皱着眉头,被屋内的光线刺的睁不开眼睛。
“再睡会。”正要起身,被容逑又按了下来,破天荒的,没有催促她练剑,而是让她休息。
“不用了,赖床会成习惯的,我没关系。”
“不听我的话了?”
安宝眨眨眼,扬起一个俏皮的笑容来:“就是不听了,你又能柰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