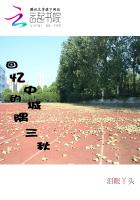不论是和家人还是和同僚,在回忆起诛杀吴曦那件震惊朝野,轰动西北的大事件时,安丙并不喜欢一上来便展开宏大的叙事,反而总喜欢从开禧元年岁末那个黄昏说起。那是一个积雪堆垒,阻塞了家家户户出行的道路,街道因而显得安静得过分的黄昏。那个黄昏,他结束了那一年的全部工作,因此心情舒畅,突然来了兴致,决心且不回后宅歇息,却叫了在军中给自己当护卫的弟弟安焕,换了便装,一同来到街上,要去城里新开张的那家金牛酒家小酌两杯。金牛酒家的十年存酿醇厚甘洌,回味悠长,不输于安丙老家甘溪场的落鸿渡酒。三杯冷酒入愁肠,可着离人思故乡。早已五十开外,在外为官多年的安丙,在那个岁末的黄昏,有些思念那远在华蓥山下,渠江岸边的故乡了。
安丙自淳熙年间考中进士,除了先后两次丁父母之忧,其余时间一直在外为官,历任大足县主簿、利西安抚司干办公事、曲水县丞、新繁县知县、小溪县知县、隆庆府通判、大安军知军。在外久了,每到年节,满腹都是思乡之情和归家之念。
一向繁华热闹的大安军治所所在地三泉县城,在那个黄昏显得空空荡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冷清得店铺都懒得开门,偶尔一只身披积雪的野狗从某个破洞里钻出来,在墙角雪地里嗞嗞地撒一泡冒着热气的狗尿,然后使劲晃动身体,将积雪抖落地上。
地上,积雪虽厚,却掩藏不住街道本应该有的丰富信息:散落的柴草,杂乱的足迹,清晰的车辙,黑乎乎的骡马粪便,胡乱扔在街边的畚箕、箩筐,懒得收回家去的各种摊点……安丙饶有兴致地将这一切都搜罗进眼底,衙门前往金牛酒家的这段距离,足够将他对大安军精心治理所呈现的兴旺繁荣一一地展现在他眼前。
他记得,从衙门出来,一直到金牛酒家门口,他的兴致都很高。因为金牛酒家没有像其他店铺那样早早打烊,关门避寒,而是高挂了灯笼,大开店门,笑脸迎接寒风中可能上门的生意。这种做生意的态度,他非常喜欢。
然而,当安丙在店家热情的迎请中一脚刚踏进酒家,另一只脚还没来得及离开雪地时,他那塞满胸怀渴望借酒抒发的乡愁,却陡然凝固,并定格为一个僵硬的进店动作。他瞬间定在店门外的僵硬动作很快便传导给了贴身护卫安焕。安焕敏捷转身,按剑回望,凛然有大侠的风范。
扫了安丙兴致的,是四个正在他治下的大安军街道上撒野的人。
空荡荡的大街上,突然间就冒出了这么四个特别不应景的人,安丙气得快笑了。谁这么不要小命了,竟敢在大军屯驻的大安军大街上胡作非为?
安丙停下脚步回望的时候,金牛酒家掌柜的和肩头搭了根抹布的店小二,以及七八个吃酒的客人,早堵到了门口,一齐探头朝外望。好奇心驱使他们比安丙都更迫切地想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激越的刀兵碰击声又像一道无形的高墙,挡住了他们的脚步。他们就那样滑稽地堵在门口,不让他们的父母官进店。
进入安丙和一众堵在门口的家伙眼里的,是三个黑衣蒙面,一副夜行打扮的人。他们手持单刀,凶狠地朝另一个身穿羊皮袄子的青年招呼。青年右手持剑,左手捂着胸口,脚步踉跄,且战且逃,从街头直望酒家这边过来。他踢碎了几坨积雪,踩扁了一堆马粪,吓得正在粪堆上找食的几只母鸡惊叫着飞跑了。
众人看得明白,青年脸上被划了至少两道口子,伤口肌肉外翻,血肉模糊,面相显得格外狰狞。而他捂住的胸口,雪白的羊毛袄子被染红了一大片,指缝间犹自有鲜血汩汩涌流。一个胆小的家伙喊一声“杀人了”,扭头跑进大堂,登登登上了楼,却又忍不住好奇,转而伏在窗前俯看。是掌柜的。掌柜带头,其他几人当然效仿,也登登登登转瞬上了楼。
安丙朝安焕递了个眼色,安焕会意,二人一同来到大街上,拦住了四人的去路。安焕按剑而立,安丙则将双手笼在翻毛羊皮袖子里。安丙脸色看起来十分平静,心底里却万分恼怒。突然出现在大街上的凶杀斗殴,破坏的不仅仅是他浓烈的思乡之情,还有他善于治理辖区的名声。那三个黑衣蒙面的家伙简直太不长眼,追着一个瘦弱的年轻人砍杀,都杀得人家快倒下了还不肯收手,实在太不给他安某人面子了,他以为。
羊皮袄子青年被三个蒙面人追杀得急了,回身挥剑格开砍向自己后背的两把单刀,却吃不住两把单刀的大力砍杀,一个踉跄,他朝前猛蹿了好几步,堪堪蹿到安丙面前,脚下一软,就要倒下。他赶紧将剑插进雪地,想将身体支撑住,却挡不住脚下无力,一条腿早跪了下去,像似要给安丙行半跪大礼。
就在青年跪下的一瞬,另一把单刀早抵近他的后腰。一个蒙面人右手单刀前探,左手捏个刀诀,一脸要将青年送上黄泉路的狰狞。这个动作引来了楼上的一阵惊呼。可惜单刀未能扎进青年的后腰,却被突然飞来的一脚踢飞向酒家楼上聚满人头的窗口。刀尖插进木头窗框,颤悠悠地晃了半天,惹得窗里一阵见鬼似的惊叫。
单刀被踢飞的蒙面人显然半天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呆在原地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好。他这一刀明明有十足的把握戳进羊皮袄子青年的后背,直达心脏要害的,怎么会眼前一花,手腕一麻,刀就无缘无故地飞了呢?他没看懂,但他身后的另两个蒙面人却似乎看得很明白,因此齐发一声喊,一左一右,挥刀不取羊皮袄子青年,却朝安丙包抄了过来。很显然,那迅若闪电的一脚,来自神情悠闲若无其事的安丙。
落日的余晖被挡在街道西边的房屋背后,街上光线已然略显昏暗,然而刀光闪烁,依然直逼人眼。楼上的惊呼声再次响了起来,带着惊悚恐怖的颤音!
两柄单刀还没沾上安丙毛绒绒像只狗熊的皮外套,一柄长剑早划破大街的冷寂,当当两声脆响,生生格开了两把单刀。作为贴身护卫,保护的又是自己的亲哥,安焕显然是非常称职的。
安丙见弟弟安焕替自己解了围,而且只三招两式便将两个蒙面人逼退了好几步,便不再将注意力放在蒙面人身上,却蹲下身去。他知道,那个半跪在他面前,嘴里不断涌出鲜血来的青年,支持不了多久了。
安丙仔细瞅了瞅青年垂下的头,又看了看被不断滴下的鲜血浸染的雪地,皱紧了眉头。但他只看,不问。他知道,青年如果有什么需要交代,问与不问,他都会有所交代;如果没有什么需要交代,就算问破喉咙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