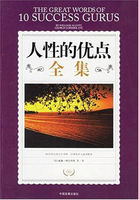有一天,街上忽然传着:胡聋子死了!
消息是从几个买菜的家庭妇女口里传出的。
“那么好的老人啊!一辈子医了几多人!”“胡聋子啊,可惜了!”她们摇着脑袋,从小梅院门口走过。
小梅的心猛地沉下去!胡聋子,多好的老人啊!从母亲那一代,就得到他的治疗,一直到今天,得宝和兵兵还在接受他的治疗。老人行医一辈子,是这条街,不,是这一带方圆多少条街穷人的守护神。是穷人的救星啊!
小梅赶到胡家去。一路上,脑子里就回放着老人给人看病开药时的情景。上次给得宝看病,写方子的时候,老人的手握着毛笔,已经微微颤抖!哦,好人不能久长啊!
那门口果然挂着白幡!大门两边,贴着新写的对联。“世有魍魉桑梓病,天降菩萨活苍生”,字迹苍劲,一看是隔壁老塾师的作品。老塾师姓董,和过去在这里搞工运学运的董先生是未除服的远亲。日本人来了,他失去职业,提着篮子走街串巷卖百货。
今天他没去卖货,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不住的给送花圈的人写字。
小梅走进屋。胡聋子安卧在棺材里。银白的胡须,长长的,分开在脸颊两边,嘴抿着,眼睛闭得很紧,脸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表情固定着,似乎轻蔑,似乎哀伤。
小梅烧了三柱香,又在遗像前烧了几张纸。她没有钱财,只能买了些纸钱香蜡,交给胡家人,权表心意而已。
街坊渐渐来了。这方圆一带,哪家没得过胡老先生的治疗?人们敬了香,都在门口站着,蹲着,讲述着老一辈人的故事。胡聋子的故事,早在人们口里传说,现在是集中了。
老塾师写完字,也搬把椅子,坐在门口场地。
忽然人群一阵嘈杂。只听见“嗵嗵”的皮靴声,很快,一群人来到门口。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中间一个军曹,沉着脸,按着军刀。庞哈子带着几个鸡杂鸭杂,也跟在一边。
人们霎时鸦雀无声。这些凶神,来这里做什么呀?
老塾师从椅子上起来,对那军曹鞠了一躬:“请问贵军来寒舍,有何贵干哪?”
那军曹哼了一声,回身“哇啦哇啦”几句,几个日本兵不由分说,直接就进了屋子。胡家人见状,不知究竟,对庞哈子说:“我们家丧事呀,你们惊了亡人可不好!”
庞哈子阴沉着脸,同样不出声。
一会,进去的日本兵出来,对军曹说了几句,军曹的脸上稍微开了些。他对庞哈子说:“庞的,你的说说!”庞哈子便清清嗓子说:“有人报告,你们这里在聚众,发泄对皇军的不满!”
众人愕然。不知道从何说起。
庞哈子指着门上的对联说:“这对联就有问题!什么桑梓病?什么菩萨救苍生?莫以为皇军不懂!这里地方病了么?皇道乐土不好么?要哪个菩萨来呀,莫不是要重庆的菩萨来!”说着,他愤愤地走上前去,扯起那对联,“撕拉”一下,撕成碎片。没有一个人敢拦他。老塾师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气愤。
日本人看看众人,都沉默无语,便大声说了一阵,庞哈子翻译,大意是说日本军队来这里,是帮助你们的,你们切不要被重庆的宣传迷惑。大日本皇军总是要踏平那里的!说完,“哇啦”一声,带着兵就走。留下这里几十人,战战兢兢,不知道如何是好。
老塾师叹口气说:“都散了吧!不要给他们口实。唉,这年头,老人走了,连来看看也看出毛病来了!”
有人说,一定是鸡杂鸭杂搞的鬼。这些年,街坊有红白事情,都是要先跟他们打招呼,塞钱塞烟。胡家没有打招呼,他们就搬来日本人,闹一场,叫你不顺畅。
老塾师说:“就是不跟他们打招呼!王八蛋!他的祖宗是谁呀?还记得吗?”说着又叫众人散去,只留下胡家亲戚。
按照礼数,人去世要在第三天出殡。那天早晨,小梅天不亮就叫醒了得宝和兵兵。
“快穿衣服,我们要去给聋子爷爷送葬!”兵兵懂事的赶快穿衣服,得宝动作稍慢,也很快就穿好了。
小梅给两个孩子胸前别上一朵白花。自己在胳膊上戴上一个黑袖标。三个人牵着手,来到胡家门前巷子里。
街坊邻居全都起来了。黑压压一片,扶老携幼,站在两边,看着胡家那里。
咦,日本人竟也起得这样早!还是昨天那军曹,带着十几个宪兵,十几个鸡杂鸭杂,挎着枪,亮着刺刀,扶着军刀,阴沉着脸,不怀好意地扫视着周围的中国人。人们都不敢和日本兵对视,也没有一个人因此退走,都在静静等待着那个时刻。
唢呐声凄厉地响起来。“呵!”一声长啸,八个壮汉,抬起棺材,从胡家出来,缓缓转到巷子里,走过人们面前。
忽然,有人喊道:“胡爹爹行善一辈子,老少爷们,跪下啊!”顷刻之间,“呼啦啦”,所有人都跪下了!无论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童稚孩子,都那样虔诚地跪下了。仰着脸的,脸上挂的是泪痕,低着头的,多是孩子,他们不住地磕头,似乎这样可以把老爷爷磕回来!
黑压压的一片,无尽头的下跪的人丛,在这清晨的巷子里,观之叫人惊心动魄!
呜咽声升起来了,先是妇女,跟着是男人,呜咽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那声音不高,其间却有着无限的压抑,似安魂曲,似命运敲门,说不出的悲,说不出的哀!孩子们看大人哭,也都跟着哭,一时嚎啕成一片。
日本人被这场景搞得不知所措,想制止,又没有理由,所有人都跪下了,只剩下他们十几个拿枪的士兵,再就是被中国人叫做“汉奸”的便衣。在这样多的人中间,他们显得那样零落,那样孤单,那样不合时宜。
棺材终于过去了,走出巷子,向远方的墓地走去。跪着的人们纷纷站起,无声地流散在大大小小的门里面。日本人大叫一声“开路!”汉奸们跟在后面,也撤离去。
小梅牵着得宝和兵兵的手,心里,只觉得有说不出的悲愤。
红玉隐居在江南山野小镇,一晃,几年了。
小镇远离前线,这里群山环抱,傍晚时分,夕阳从远处山峰间的缝隙里散出光芒来,灿灿的,将山坡上那些桃林染成一片静静的通红。
夜晚,银光铺地,月儿有时像一只盘,有时像一个弯钩,无声无息地滑过这片山间谷地。月光下,各式各样的禽鸟小兽在灌木中栖息,偶尔发出悠长的叹息。
小小药店,生意总是那样,节俭一些,可以有些小的积蓄。陈子敬对这一切很满意,就是红玉,也找不到不满意的理由。福生之后,又添了个女儿叫枣花,孩子很听话,他们喜欢偎依在娘的怀抱里,缠着娘讲白蛇娘娘的故事。
但是远方,抗战的春雷一直在地平线上隆隆响着,路过小镇的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曾经热血青年的红玉,不可能无动于衷。
小镇邮局的墙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天天贴着一张本省的日报,红玉有时候去那里看看。上面有战争的消息。最叫她不能平静的,是从报纸上,她知道就在不远处,在江南的江河山谷之间,活跃着一支新的军队,当年包克带着她们,就是要去投奔那支军队。那次行动失败了,伙伴们付出了惨重代价,燕玲牺牲,包克牺牲!千辛万苦,只因为包克说了,那支军队是未来国家的希望。如今他们到江南来了!就在不远处,在几百里距离的敌后,他们建立了根据地,打击着日寇,时时有胜利的消息传来。
要是当年他们在这里多好!自己一定跟着包克,去那军队里做了一个战士吧?这想法叫红玉激动,也叫她感叹不已。一切都晚了!包克不在了。自己走投无路,被丈夫收留,做了一个家庭妇女。永别了,曾经的梦想,才华横溢的包克,下辈子再聚吧!可是有下辈子吗?
红玉有时和丈夫谈谈报纸,丈夫对那些没有丝毫兴趣。对于红玉的过去,陈子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妻子,是两个孩子的妈,这就够了。陈子敬曾经有很大的决心,将生意做大,然后到上海去,当一个大药店的老板,可是市场残酷,自己的实力太小,几次努力都失败,他也就放弃了。这小镇很好,生活便宜,人们都尊敬他,走到哪里,都有熟悉的面孔,陈子敬渐渐离不开这个小镇了。
他知道妻子有些文化,从来没有去细想它。一个女人而已。女人的天职,就是伺候丈夫,为丈夫生一个比一个结实的孩子。除此之外,女人还能要什么呢?他夜里睡得很安心,完全不知道妻子心里的波澜。
天亮了。陈子敬伸伸懒腰,睁开眼,红红的晨光从窗子里照进来,把屋里映得亮堂堂。砖铺的地上,散乱地堆着枣花的裤子和褂子,这孩子睡觉一向不老实,常常把被子上搭着的衣服蹬一地。
另一个小床上,福生的被子平平展展,显示着和妹妹的不同。
陈子敬去推妻子:“福生娘,福生娘!”
红玉睁开眼,看了看窗子说:“还早哩,叫什么呀?”陈子敬换了个称呼,还是去推她:“枣花妈,起来呀,该做早饭了!”以往都是红玉做早饭,可是今天她忽然生气地说:“你就不能做吗?规定是我做早饭!”陈子敬吃了一惊,看着红玉,像是不认识的。这是怎么啦?今天陈子敬要去远处进货,以往这个时候,妻子早早就起来了,做好早饭,给他准备好衣服、袋子等等,晚上他回来,老远就看到自己店里的灯光。
为节约,家里总点一盏昏黄的小油灯,对于远方归家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灯光更叫人舒心的呢?
陈子敬没有和妻子较劲,自己爬起来,去灶边,抱来柴禾,点燃火,将水米下锅。陈子敬做饭是把好手,很快,饭就香了。
红玉睡在床上,听见丈夫走来走去的忙活,心里也有点愧疚。这几年,她已经习惯了做饭洗衣服,今天突然对丈夫发态度,他一定不知所措的。
她很快穿起衣服,走到儿子床边,叫着:“福生,福生!”儿子哼了一声,再叫,儿子睁开眼,憨憨地叫了声“娘!”福生这孩子,天生厚朴,小小年纪,天天跟在娘前后。娘做事,他就在一边帮忙。娘拣菜,他也用小手去将菜根上的泥土摔掉,娘去河边洗衣服,他为娘拿着棒槌。福生走路脚很重,红玉走在前面,听见后面福生咚咚的脚步声,心里总要泛起疼爱的波浪。这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啊!
看儿子娇憨的样子,红玉止不住去儿子脸上,亲了一口。
那边的枣花已经醒了。“娘,也来亲亲我!”枣花小哥哥两岁,平时都跟着哥哥玩,哥说东,她不往西,有时在晚上,兄妹俩在油灯照不到的地方躲猫,枣花一下子看不见哥,就哭起来。就是在娘面前,枣花不让着哥哥。娘要是抱了哥哥,她看见,非要娘抱她不可。现在看见娘亲了哥哥,枣花又吃醋了。
红玉笑起来,走到女儿床前说:“你莫学哥,他是懒虫!”
枣花说:“懒虫你还亲他呀!”红玉说:“没有呀,哪个亲了他的啊?”福生也说:“就是没有,娘只给我盖了盖被子啊!”
枣花说不过哥,看看又要哭了!
红玉哈哈大笑,一把将女儿连被子抱在怀里:“好了好了,我的乖女儿,娘现在就亲你!”说着在女儿脸上啜了一口,枣花破涕为笑。那边,陈子敬大声说道:“饭熟了啊!哪个不起来,当心吃不上饭啊!”
两个孩子立刻争先恐后穿衣服,小枣花一慌,将袖子穿错,急得叫娘:“娘,娘,快帮我!”福生看了,赶紧跑过来,帮妹妹把袖子脱掉,重新穿好。
红玉看得心里一动。儿子,真的是厚道啊!
四个人吃饭。饭是包谷米,就着腌菜,两个孩子吃得很香。红玉不声不响地吃着,陈子敬看老婆不高兴,有意找话跟她说,红玉只是躲不过去了才答一声。吃过饭,陈子敬用一根棍子挑起一卷麻袋,对儿子说了个:“我走了,在家听你娘的话啊!”福生说:“爹,早点回来啊!”给爹把门打开,看着爹走出去,他又到路上,朝着爹走的方向看了一阵。
枣花吃了饭就去地上玩耍,福生从外面回来,把板凳放顺,又拿来一块抹布,将每一条凳子抹干净,顾客来了,是要坐的。
红玉收拾着碗筷,看着儿子做事,心里既感动,又难过。儿子这样小,就知道替大人分担了。这个家庭是温馨的。一对好儿女,丈夫脾气温和,开着药铺,吃饭不愁,全镇子的人,都说这家人家使人羡慕。的确,如果仅仅过生活,镇子上这样的人家不多。
红玉的内心,没有人能知道。曾经投身过那样波澜壮阔的战争,曾经和那么多勇敢的战友并肩战斗,曾经和包克这样优秀的人共生死,这样一个人内心的渴望,不是小镇人能够理解的。
组织又在大地上传出了声音,那声音像春雷,在红玉心里引起轰鸣。好多个不眠的夜里,红玉感到自己的热血沸腾,一种沉睡多年的向往又在心里复活。
这是近来缠绕在红玉脑海里的思绪,陈子敬当然不知道。陈子敬照例天黑才回,照例在街的那一头就看到了家里的灯光。他兴冲冲地走进门,儿子看到爹,高兴地叫了一声,跑拢去,爹把他抱起来。远处的枣花看见了,连忙过来,爹却腾不出手来,枣花有些沮丧地跟在爹身后,直到爹放下哥哥,又放下背篓,才得空拉住爹的手。红玉到厨房去,端出饭菜来。一碗黄瓜,一碗青菜,一碟豆腐,一碟咸菜,陈子敬大口吃着,两个孩子围在一边,不时向爹讨一片黄瓜吃。
红玉看着,眼里泛起笑意来。天真的孩子啊,孩子永远是叫人心疼的!
夜很快就深了,一家人照常睡觉,俩孩子玩累了,很快就睡去。红玉吹灭灯,过来躺在陈子敬身边,陈子敬伸手给她掖了掖被子。
沉默了一会,陈子敬问:“你这几天怎么啦,好像有心事?”
红玉说:“你难道不知,日本鬼子打来了啊!”
陈子敬笑出声来:“原来是这个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这里离前线不知道多远呢!不是那些报纸,谁知道什么日本人!”
红玉说:“可是日本人是真的进来了,我们这里也会被他们占领的。”
陈子敬说:“不管哪个进来,都是要吃饭穿衣的。得了病,都是要吃药的。”
红玉说:“不能那样说啊,他们是要我们做奴隶的。”
陈子敬不以为然地说:“就是报纸上说的什么亡国奴吗?其实老百姓,哪里管那么多,不管哪个在台上,总是要做事吃饭!”
红玉听着,有些生气了,把身子转过去,不再理他。陈子敬也不在意,打了个呵欠,不一会就睡着了。
传来消息,日本人离这里已经不远,很多县城都被他们占领了。但是更加广阔的乡村,他们还无力染指。另一方面,由于日军的入侵,造成很多的空白地带,不少实力人物拉起了队伍,各式各样的旗帜到处飘扬。其中最大的一面旗帜,是新四军。
邮局的墙上,多了些小报,几乎天天有新鲜消息。看多了,红玉渐渐知道,新四军到江南已经几年了!开始他们人数不多,可是都经过严峻考验,富有游击经验,和群众有天然联系。他们武器十分简陋,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们迅速进抵日军已经占领的地方,在敌人军力暂时达不到的地区建立政权。如今他们已经是绝对的一支实力军队!
有一天,红玉在报上忽然发现一个极其熟悉的人名,开始她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新四军挺进支队队长某某,参谋长某某,政治部主任……”
红玉在这个名字面前楞住了。说惊雷在平地炸起,也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感觉。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么?他怎么会活在人间?是不是梦幻啊?红玉又将那篇报道仔细看了一遍,确确实实写着:政治部主任包克。而且,他所在的根据地离自己只有几百里。
绝对不可能是同名同姓,包克的名字很难模仿,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一定是他,那个带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兄长,那个和自己生死与共的亲人,那个忠诚无比、在最后一刻还记得掩护自己的大丈夫。好多年了,为了包克的牺牲,红玉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没想到今天他又出现在视线里。
红玉忽然感到一阵惶惑,包克还活着!而自己呢,已经和别人成了家,养了孩子。要是见了面,和他说什么呀?他会责怪自己吗?一时心里乱纷纷的,脑子也觉得一阵晕眩。转念一想,不管怎么说,包克还活着,就是好消息。曾经有多少个夜晚,想到他,心里刀扎一般,恨不得和他共赴九泉!如今他竟然奇迹般的活在人间,该高兴才对呀!红玉的心,时而高兴,时而内疚,两种情绪交织,使她呆了一样,有人来买药,她也不知道如何打理。顾客奇怪地看着她。亏她还记得歉疚的一笑。内心翻起了巨潮,体内无数血管在膨胀,心跳个不停。红玉想放开步子,跑到什么地方去大喊一阵,跑到筋疲力尽,将最后一丝气力也耗尽。包克活着!真好啊,老天,你是有眼睛的!那样好的人,怎能无声无息地逝去?他活过来了,熬过了九死一生,如今他重归队伍,指挥着精锐的战士,在抗日救国第一线向着敌人冲锋。国之栋梁,我之亲人!
红玉的心狂了,整个沉浸在对包克的思念之中。
福生牵着枣花,从外面回来了。俩孩子围在红玉身边,叫着肚子饿了。红玉看着孩子,心里泛起无限柔情。刚才的思绪还未散去,两种情思交汇在一起,叫她感到纷纷扰扰,无从调理。
陈子敬一如既往,每天盘算着生意,完全看不见妻子惶惑的眼睛。
红玉的判断没有错。那个政治部主任真的是包克。
那年,包克帮助红玉藏好,自己一路狂奔,引开特务,在林子尽头,特务们向他开枪,他几处负伤,被送到医院急救,伤好后被关进远离社会的山里,在一个集中营里坐牢。
不久,为释放政治犯,国共两党谈判,有地下情报人员,将这个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名单提交给了共方代表,代表依据这名单,向国府要人。几经交涉,包克竟然奇迹般的从那个森严的集中营里活着出来了!
没等身体完全复原,他就按捺不住,向组织上请求工作。
“我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不能再耽误了!”他的理由。
组织安慰他,劝告他休息,他又休息了一个月,再次坚决要求工作,这次组织答应了他。
要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新四军,充实军队。那时候军队正在扩建,急需干部,包克是资深的地下党,有文化,又经过严峻斗争考验,军队求之不得。很快他就到了部队,从基层领导做起,直到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在战斗空隙里,他偶然会回忆过去,尤其怀念和红玉一起的日子。红玉活着吗?她在哪里啊?他想尽一切办法找红玉,却一直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
小镇上,一切依旧。战争似乎离这里很远,人们照常干着营生,地里的庄稼照常生长,小小药店,顾客还是那样来来往往买药。事实上,日军并不远,只是这里实在偏僻,日军暂时没有到这里来。
陈子敬又去进货,红玉在店里,守着两个孩子,没有顾客的时候,她常常冥思苦想。
形势这样紧张,陈子敬却没有一点打算。日军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老百姓都在谈论这事。在这偏远的小镇,日军可能不大会像在南京一样大开杀戒,但做顺民是前提。自从看到包克的消息,红玉已经下定了去找部队的决心,唯一放不下的,是两个孩子。假如自己走了,陈子敬一个人带着孩子,是很吃力的。如果药店照开,吃饭可能问题不大,但没有母亲的日子孩子怎么过?这些都叫人揪心。
那么为了孩子留下来?红玉实在不甘心。这样一个大时代,有血性的人们,都在为拯救祖国而战斗,自己怎么能置身事外。那样做,自己的一生就是可鄙的。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想想包克,怎么能在家里呆得下去啊?更何况,这里马上将被敌人占领,做顺民,做亡国奴,红玉是断断不愿意的。
一旦想到离开家,红玉又犹豫起来。
这个简陋的屋子,处处有她和陈子敬共同劳作的迹印。这里有温暖的气息,可以避开外面的风雨,尤其重要的,这里有孩子的亲昵。孩子啊,我心里的珍宝!假如有一天,你们醒来没有了妈妈,你们是怎样的伤心呢?红玉不敢想下去。
福生带着妹妹,在外面枣林里玩耍,枣花尖叫着,哥哥也嘿嘿笑着,在林子里绕圈子跑。一会,他们跑进来,“娘!娘!”两个人都叫着,喘着气,枣花抱住红玉的腿,把脸埋在上面。红玉心疼地抚摸着枣花的头发,这孩子,快要打辫子了。福生呆呆地看着娘和妹妹亲昵,红玉说:“儿子,过来!”福生规规矩矩过来,红玉把儿子一把抱住,在他的赃脸上亲了亲。
夜里,她一晚上起来几道,看孩子的被子是否蹬脱。有一次陈子敬醒了,不以为然地说:“你干嘛那样惯他们?没有哪家像你这么把孩子含在嘴里的!”红玉没有理他,他翻个身又睡着了。
想了许多日子,红玉偷空,给陈子敬写了一封信。
“陈兄,”红玉考虑很久,给了这样一个称呼。非常时期,一旦离开,谁也不知道结果怎样,这一别,说不定就是阴阳两界!陈子敬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了她,对她好,给了她遮风避雨的港湾,这是她不能忘记的。这个温厚的男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勤勤恳恳经营着这个小家庭。陈子敬的爱,和他的性格一样,温和朴实,在这样的男人身边,尽有安宁伴随。
当战争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中的时候,陈子敬的单薄就显现出来了。过于缺乏大丈夫气概,对国家民族几乎是冷漠看待,这一切和红玉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看到包克的消息后,红玉真切地感到,陈子敬不是自己的爱侣,思想距离太大,他是一个勤勉的家庭男主人,绝对不是战友,更不是心心相印的知音。人世间,这样的同路,回想起来,不能说没有幸福,更多的是酸楚吧?是命运叫他们结合,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现在要分开,也是命运吗?
考虑很久,写下这样的文字: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你身边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孩子交给你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知道,孩子是我的心头肉,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会丢下他们的。拜托你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孩子长大也会感激你!不要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也不要问我去做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的命运。愿你保重身体!如果可能,为孩子找个妈,我在远方也会为你们祈福!”写好这封信,就像母亲生下一个难产儿,有一种解脱感。她把这封信藏在柜子的夹层里,准备在离家的时候放在枕头下边。
那天,借着说福生生日,给福生和枣花都照了相,红玉将照片贴身藏了。
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只等着上路。去那里要走许多天。带一点钱,带几件换洗衣服,其余的都不需要了。
这些天,红玉总把两个孩子揽在面前,亲不够,抚摸不够,福生似乎觉察到什么,问:“娘,你怎么眼睛是红的啊?”红玉说:“风大呀,风把娘的眼睛吹红了。”福生便笨笨地跑去关门。红玉看着儿子幼稚的身影,眼泪真的流下来了。
预定的日子到了。陈子敬不在,红玉把两个孩子领到隔壁汪婆家,对汪婆说:“那边村子里有个客户的款子要收,我去一下,孩子麻烦您管管。”汪婆高兴的答应了。
红玉对福生说:“带着妹妹好好玩啊!凡事让着妹妹,她小不懂事,你是好孩子!”福生懂事的嗯了一声,对她说:“娘,你要早回啊!”就像是知道什么似的,眼睛一直看着娘,也不说话。
红玉心如刀割,赶紧转身走了。到转弯处回头,儿子还牵着妹妹在呆呆地望着娘哩!看娘回身,福生又叫了声:“娘,早些回啊!”
可怜的孩子,娘是一去不回了啊!红玉吞下眼泪,狠着心往前走,走到镇外,四下无人,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红玉沿着一条大路走着。
记不得走了多少天。乡村里,几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到哪里都靠步行。红玉独自一人走在路上,倒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太阳升起来了,大地一片金灿灿,田里,庄稼都伸着腰,随风点头。如果是和平时期,该是一片风和日丽,升平景象。现在寇兵的威胁无处不在,就是菜花再香,也抵不住空气里有一种肃杀。
走完平地,又进了山。
中国大地上,山真多啊!江南的山,那样绵延不绝。红玉走到一个山脚下,仰看那山,遍布灌木茅草,小路曲曲弯弯,几步就看不见前面,路边也长满一人深的茅草。红玉弓腰在山路上走着,渐渐上了山腰。小路很狭窄,风从山的那一面吹过来,将身上的汗吹干。红玉觉得很爽,放下小包袱,依着一棵树站着,向前方望去,山峦如海,成百上千的山峰,此起彼伏,波涛一样一直绵延到天边。
黄昏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较大的庄子,红玉下意识地感到不能进庄,应该找个偏僻的人家歇息。她绕了一圈,走过那庄子,到一家孤单单的人家投宿。那家人有老人,有孩子,看到红玉一个单身女人,倒很热情。红玉和他们说好吃饭出钱,老人很高兴。几个孩子也围着红玉,看她白净的脸。正吃饭,那家儿子回了。一个壮实的庄稼人,背着一个大箩筐,箩筐里是一筐青草,割来喂猪的。看见红玉,那汉子楞了一下,跟着客气地问:“来客了啊?”老汉说:“是路过的,到这里找丈夫。”汉子哦了一声,再没说什么。
吃罢饭,红玉到老汉给她腾出的农具房休息。坐下没多久,听见外面有嘈杂的脚步声,红玉立刻警觉起来,站起身,想从门缝里看外面。还没到门口,听见老汉在外面大声叫着:“大姐,大姐!”
红玉抽开门栓,看见两个男人站在门外,其中一个挎着手枪,另一个背着土枪。
“我们是李司令的部下,来看看你!”挎手枪的直截了当地说:“你从外面来,又没有人认识你,我们奉命对你进行审查!”
红玉说:“我来找丈夫,有什么审查啊?”
那人严肃地说:“谁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叫红玉把包袱打开。
红玉无奈,打开包袱给他们看。他们翻得很仔细,看到没有什么违禁品,就将包袱还给红玉。“你得跟我们走一趟!”那人说。红玉说:“为什么呀?我走路犯了什么吗?”
那人回答:“犯没犯什么我不知道,到了司令部就什么都知道了!”看他们不容分说的样子,红玉只好跟他们一起走。走了一会,到了那个大庄子。庄子里已经家家户户点灯了,红玉他们从人家门前过,没有引起一点动静。
所谓司令部设在庄子中央,一家富裕人家家里。门口站着一个穿灰军装的兵,刺刀在暮色里闪亮,走进去,又是两个士兵荷枪站岗,院子里人来人往,房间都亮着灯。送她去的两个男子带她进了一间屋子,屋里有三个人,都穿灰军装,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看见红玉,一起转过脸来。
一个人给红玉搬来一条凳子。红玉坐在凳子上,看着他们。其中一个问道:“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做什么?”
红玉说:“我是于吉镇的人,丈夫到这里来收购药材,一直没有回去,我来找丈夫的。”
那几个人对看了看,露出不相信的神色来。那人又问:“你一个单身女人,兵荒马乱的,找丈夫,哪个信呢?说吧,谁派你来的,只要说实话,什么都不要紧。看你一个女人,家里还有孩子吧?我们可以放你走。”
一边有人马上补上:“要是不说实话那可对你不妙!”
另一个人加了一句:“今年以来,晓得杀了几多汉奸!都是派进来的,又不说实话,把我们惹烦了!”
红玉说:“我是真来找丈夫的。”
这样问了半个多小时,三个人不耐烦了,高个子说:“你今晚再好好想想,明天上午再问你,要是再不说实话,那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叫把红玉带下去。
红玉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外面有哨兵站岗。那房子的门上有缝,月亮从缝里照进来。红玉躺在一堆稻草上,看着月亮,心事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