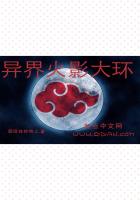女儿才十一岁,怎么可能怀孕。他们明知不可能担心出事还是草草地放下工作搭车赶来,回到家看见女儿除了情绪有点低落,身体长高了些,没什么怀孕迹象。像审问犯人一样问东问西,问来问去,最后只有对她的指责和谩骂。
人家为什么欺负你啊,你好好在学校待着人家会欺负你啊。欺负你你不会打回去啊,看你长这么高怎么这么怂,一点都不像是我的女儿。你知道我们在外面赚钱多辛苦吗,来回跑一趟得花多少路费吗,一点都不给我们省心。哭哭哭,就知道哭,哭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不是奶奶过来插一句骂孩子能解决问题吗,他们会从白天骂到黑夜从黑夜骂到天亮,在他们看来无论发生什么一切全是女儿的错。日思夜想的父母真正地来到身边的时候,竟然是这样的陌生和疏离。
胡菲菲忍着泪水抱着猫到自己的小房间,她只能跟猫说心事,只能对着猫流泪。她坐在小床上,抱着猫,听着隔壁房间父母的谈话。他们说他们已经攒了足够的钱准备再生一个孩子。
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几点,胡菲菲被一阵刺耳的猫叫惊醒,摸着黑爬起来,穿过父母的房间,发现他们不在家,只有奶奶躺在椅子上轻摇蒲扇似睡非睡。
门前有一棵葡萄树,哗啦啦往下掉叶子,猫就悬空挂在葡萄架上,脖圈勒得它不停动弹就要叫不出声。菲菲赶忙找了剪刀和凳子,一刀剪短绳子,猫啪的一声坠地,惊恐地逃到房间角落里。
又是那只黑色公野猫,菲菲多次见它在院墙上徘徊,绿色的眼睛在黑夜里像两盏耀眼的灯盯着咪咪。她想咪咪刚才一定和那只黑猫经历了生死搏斗,这样的想象让她再次回忆起郝帅、老鼠、胖子、竹竿和鼻涕虫。她要像刚才追打黑猫那样去回击他们,即使他们像黑猫那样顺利逃脱,那是他们的事,回击则是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