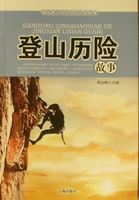“后面的事你们就都知道了,文玑在子书晋被囚禁的时候对焕娘滥用私刑,后来子书晋逃了出来,搜了大半个侯府才找到地牢。”师父耸了耸肩,从包袱里取出水袋,喝了两口。
焕娘叹了口气道:“可惜当时的我执着于他的背叛,根本没想过他为何会这样做。”
“这么说来,幕后黑手,是少主子书秦咯?”我摸了摸下巴,自信地说道。
焕娘看了我一眼,继续说:“后来,是子书秦来救了我,我曾一度认为,或许,我应该相信我这个未婚夫。
“回到子书城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想,他应该是在躲着我吧。杀手幻境,就此瓦解。
“我们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后来,十七岁那年夏日,子书秦要在我们十二个杀手中挑一个做贴身护卫……”
◆◇◆◇◆◇◆
天刚亮了没多久,外面便传来一阵惹人烦的骚动。阿焕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末了,她捂着眼睛,大喊:“晋!你去看看……”
话未说完,便失了声。她就这样躺了许久,才移开了手,翻身下床。
晋已经离开了。她又……喊什么呢。
她忿忿地冲出了幻碧阁,想去看看到底是谁一大清早就打搅她的好梦!
然,门外一个人也没有。
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荆芜花香。
她愣了一瞬,急忙环顾四周,却在无意中瞧见幻碧阁的墙头上,探出了一枝荆芜。
一枝荆芜蜿蜒曲折,从高墙上探出,有那么几朵含苞待放的,似有暗香来。
风似乎强了一些,吹散了花香。她从心底泛起阵阵凉意,不由得抖了两下。
“初秋了,荆芜花就要开了。”身后,一个冰凉的男声由远及进,话音刚落,一件尚残留有余热的外袍披到了她的肩上。
她没有回头,淡淡道:“多谢少主。”
“他们可扰着你了?着实放肆了些。”
“少主想要做什么?”她终于回身,正眼瞧了他一眼。
“准备你们十二个人的最后一轮比武啊。”他粲然一笑,“阿焕,我希望你能赢。”
“输赢本就不是什么定数,少主又何出此言?”阿焕边说着,边转过身,朝幻碧阁走去。
“你一定会赢。”他低声说道。
子书秦所说的比武是在两日后举行的,那日一大早,他便将那十二个人聚集到了比武场。
鼓声四起,他们分散在比武场的四面八方,拿着各自称心的兵器,伺机而动。
不知是谁大喝了一声,十二个人同时向场中间涌去,一时间,打的难舍难分。
似乎是出于习惯,晋和阿焕并没有打算同他们争,而是一开始就不动声色地退到比武场的对角处,全然做起了看客。
他们看着那十个人为了活命而争得头破血流,不念旧情,全然变成了磨牙吮血的怪物。
场上,刀剑相撞而发出的锵锵声不断,到处是绝望的嘶吼、痛苦的哀嚎,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好一处人间炼狱!
他们原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姐妹,关系扉浅;他们的实力不相上下,又深知对方的弱点。这分明就是在考验他们的心啊。
心软的不忍心伤了自己的搭档,因为他们之间情谊是万物都不可比拟的。
而对于心硬的来说,剩下的十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死一个便多了一分活命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如此斗了将近半个时辰,这场混战才总算停了下来。
彼时,场上只剩下了陌、音、安、若和幻境六个人。
远处,响起了几声清晰的掌声,“很好,现在中场休息。”说罢,子书秦便转身离开了。
待他走远,子书安便瘫软在地,连剑都丢在了一边。她颤抖着身子,慢慢爬到了子书易的身旁。
她犹豫了片刻,伸出手来覆上了他的眼。
忽然,一支弩箭朝她射过来,她来不及躲闪就被贯穿了胸膛!
她难以置信地抬头,对上了不远处子书陌的一双深邃的眸。
“为……”
“你不是一个称职的杀手。”在她身后,子书若敲着手里的短刀,悠悠开口。
阿焕嗤笑了一声,寻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
子书音和子书若交换了一下眼神,悄悄往阿焕那边靠近。
然她们刚走了两步,就有两把剑飞过来,生生插进了她们脚前的地面。
那两把剑她们再熟悉不过,是子书繁和子书和的。
她们扭头看了看左边尚未收回手的晋,又看了看右边侧身看来的阿焕,默默地退了回去。
难怪幻境能稳居杀手榜榜首,他们的默契竟已到了如此地步!
晋不自觉地轻勾嘴角,抬脚朝阿焕走了过去。
约莫还有三步远的时候,阿焕喝住了他:“怎么?你也想杀了我吗?”
“当然不是。”晋皱了皱眉,“我来是想同你商量一件事。”
说着,他走到她的身旁坐下,“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不应该是除掉他们三个吗?等比试结束了,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阿焕没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他看,看得他连心跳都漏了半拍。
良久,她忽然起身,甩了甩剑道:“休息够了吗?”
晋满意地笑了,执剑起身,与阿焕并肩而立。
闻言,他们三个对视了一眼,将晋阿焕围在中间。
但他们还是太高估自己了,如此缠斗了几回合,三个人便一死两伤。
阿焕捡了子书陌的弓弩,一步一步缓缓踱到子书音和子书若的身边。
随着几声箭刺进血肉的声音,她们瞪着一双眼睛,倒了下去。
“嘁,有什么不能瞑目的?”她轻声发笑,蹲下身子用若的短刀扎进她们的双眼,来回搅动,“弱者,不就应该去死吗?”
她看向了晋,笑靥如花,“晋,你说是也不是?”
“阿焕,你怎么……”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是吗?”她站起身来,越过一具又一具尸体,走向了他,走向了她此生最信任的人,走向了那个她以为可以相伴一生的少年。
“你可还记得,我的剑术师承于谁?”她从袖子里取出手帕,轻轻擦拭着剑上沾染的血。
“……我。”晋闭了闭眼,沙哑的声音里透着太多的思绪。
“那你说到最后活着的,是深谙剑术的你,还是你亲手教导的我呢?”她丢了手帕,渐而笑开。
晋亦笑:“既然是最后的结局,当然只有最后才清楚。”说着,他比好了姿势,随时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