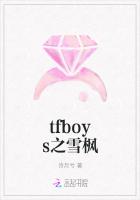“不要怪宁师叔,他同你先前提到的人有深仇大恨。”陆天罡说罢,端起一碗店主自酿的梅花酒一饮而尽。
显然,在此之前两人已经说了许多话了。这已经是翌日的下午时分,陆天罡昨夜安顿好了苏执白后,并没回到四圣宫,而是在住在了苏执白相邻的房间。在这件事上,尽管他本人一再辨白说“只是懒得走路,并不是在这里看护你”,可心里头却未尝不觉的,这个身子骨瘦弱却坚硬的向块昆吾石的家伙有些对自己胃口。
他对面作着的苏执白不置可否的笑了笑,尽管此时他的脸色还是那般惨白,但隐隐却觉得,往日那种因罕疾而引起无力感稍稍退却了一些。
陆天罡又自顾自的斟了一碗酒继续说道:“畸余原来是个很好的大夫......他的针刑虽然使人痛楚无比,但所刺之处却不是什么要紧的穴位。而且为了防止囚犯死的太快,那些针都被极其名贵的药材泡过。”
苏执白没有奇怪对方是怎么看出自己心里的疑惑,所以只当他是自言自语,于是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我本以为你是个粗豪之人,没想到你却只喝梅花酒,我虽然不会喝酒,但却听懂酒的人说过,这种酒原本是度数极高的高粱白,但几经蒸煮后,原本的浓香烈辣却没了,在加入冰糖同梅花炖煮后就寡淡无味的很......”本来他还想继续置评一番,但看到那碗梅花酒的颜色后就失去了兴致。
此时碗中的梅花酒在夕阳下呈现出淡淡的脂红,像是冲淡了的血水,散发出一抹怪异的腥香。
陆天罡看着苏执白脸上的茫然若失。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种很复杂的神色,随手捻碎了一粒花生米的红衣,熟练的将后者扔进嘴里后才说道:“你先前所说的那个让你送信的人,其实是我的小师叔。后来,发生那件事后,西极仙山便把他逐了出去。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而宁师叔从那之后性情就变得乖戾暴虐,莫说是像你一样普通人,就是他自己门下的弟子都被他打死了好些。”
陆天罡既然没说当年发生了什么事,苏执白自然也不会傻乎乎的凑过去问。其实他并不关心当年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在乎陆天罡嘴里隐隐透出来的意思。
不通修行的普通人难道......便不是人了吗?
在那个名叫清溪的、小到在九州图志上都没有标注的小镇上,都是些普通人。他们一样有哭有笑是活生生的人。亲人死了,他们会痛苦难过,逢着好事,也会乐不可支。
苏执白不想再去想这些事情,但随即他又想到了那个自己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门房。这晃晃天下之人几十亿数,而能够洗经伐髓过了修行门槛的有多少?十分之一?病大叔说过,如果自己的气海不碎,到也算得上是一株苗子。而像自己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苗子”的人,却连十万分之一都没有。那这天下能开启修行一途之人怕是不到万余。
因为多,所以轻贱罢了。
陆天罡没想到自己一句信口之言,会让对面那个家伙想到这么多。在他看来,所谓修者,在神守清灵意贯太虚凝汇出平生第一缕内息之时,便已经和前一刻的自己成了云泥之别。这种想法没错。
也许是察觉到酒桌上的气氛开始像某种决然的态度转变,一时间两人默然无语。
直到两盏茶的时间过去,陆天罡才醺醺然的说道“以后有什么打算?”。
“哪里能修补气海?”苏执白反问。
“啥?”
“哪里能修补气海。”
此时日已向晚。禁城之中的暮鼓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声响。
陆天罡碗中的酒水似乎也受到波及,起了一圈圈细小的涟漪。他想了一会,开口说道:“九州之中能人异士不少。但说起来,当今世上,也许只有一人才有可能做到。”
苏执白深吸了一口气道:“谁?”
......
太玄剑霄的名头就好像是初春第一抹草色,纵然是顶着四圣第一的名号,在与之毗邻的京畿之地却反而显得稀松平常。
这种稀松平常就好像是距离太近导致的一种“它就在我隔壁,翻个墙就能进去”的错觉。
所以西京人谈起太玄剑霄总会露出一抹平淡神色,远不如谈起其他三圣时的那种仰之弥高的敬畏感。
苏执白当然知道太玄剑霄的大名,却并不曾听人说起过这所用三尺青锋的寒芒铸就的宗门,竟然就在西京城东三十里的太玄峰上。
这会儿他已经和衣而卧,望着窗纱外朦胧的月影,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感情。
愤怒?被一个朝夕相处许多年、病恹恹的老混蛋差点害死自然是要愤怒的。但不单单是愤怒那么简单。怨恨?那七十三刺确实是仅次于历次血潮狂涌的痛楚,但畸余是个可怜人,何况陆天罡的话里,畸余应该有一段可悲的故事。
苏执白想了想,月光下,他的眸子一亮,心中想起陆天罡的那一抹隐隐的骄傲,宁沧海那种看待牛羊的眼神。
“咳、咳”。他抑制住自己渐渐生发出来的情绪。生平第一次想说出一声“不。”
这是以往十年不曾有过的,因为他有病,所以一样有病的老混蛋禁止他多思多想多感,更因为......清溪镇真的是个很简单的地方。可现在他破戒了,他想了思考了知道那些事情是错的,所以他想说“不”。他想说“不”了,就要为了说出这个字付出代价。
就好像老混蛋为了喝一口酒,便要连咳三大碗红痰一样。所以他一定要修补好这个内里残损不堪的身体,想活着,要活着。活的久一些,说“不”的机会就多一些。
于是这个乾元八年的秋夜里,苏执白订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去叩开一扇十五年才开一次的门。
正在他打定主意的当口,窗户无风自开。一个娇小的人影披着月光跳或者说是摔了进来。
苏执白并没有一双猫眼,可他还是看出来这是个比他年纪还小的小姑娘。借着月光打量一眼后,他从床榻上下来,向着小姑娘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轻轻合拢了窗子。又在小姑娘抗拒的目光中将对方拖进了床底,并且细心的用布帛擦干了两处血迹,才重新躺回床上。
半柱香之后,一个黑影投射在了窗纱上。苏执白知道,那是循着血迹到来的人。此时这个黑影应该站在窗外的房檐上。就在心跳如擂鼓的当口,黑影却猛地腾空而起,消失了。
床上的苏执白并不知道,他其实应该感谢一个散着青色光芒的罗盘。这个被黑影拿在手里的罗盘并没有将指针比向该指的方向,而是划了一个漂亮的弧线,指向东南。
等过了好一会,苏执白终于确定那人不会回来后,才小心的将小姑娘从床下拖了出来。由于不敢点灯,所以只能借着月光查看对方身上的伤口。
借着皎洁的月光,苏执白正要解开小姑娘套在外头的短襦,却冷不防被一口糯米般细牙叼住了虎口。
他看着姑娘一双寒冷的眸子,才想起来再小的姑娘,也是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