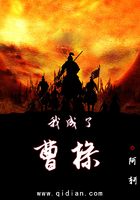两季分化1
我们在夏的光影里,遮盖罅隙,遮挡属于青春的温暖,逐渐冰冷。
写秋推开门,包厢内的暖气混杂着吵吵闹闹的声音扑面而来。偌大的房间塞下了不下二十多个成年人。
在写秋站在门口有些发愣的时候,一个打扮得干净而又落落大方的、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女人走过来,亲切地挽住了她的手:“陈大作家,还记得我不?”
写秋先是一愣,仔细地打量了了一下她。“......班长?”
“哎呀,居然没忘记我。”班长一笑,脸上像开了朵花似的,“不愧是十一班的大才女。我看了你写的书,居然把班里所有人的底都抖出来啦!”
“那都是高中时候的好玩事儿,我觉得挺有趣的,写的时候顺便感怀下青春吧!都老了。”写秋开玩笑般感慨着,挽着班长往饭桌那边走。
这是写秋的一次高中同城同学聚会。过了这么多年,可能性格不改,但容貌都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老了。写秋暗暗感叹。
寒暄了一会儿’渐渐安静。班长开始清点没来的人。“闻夏呢,闻夏怎么没来?”班长顿了顿,看向写秋,“写秋,你和闻夏关系那么好,你知道她为什么没来吗?”
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写秋,写秋却垂下了眼帘。
闻夏,闻夏。这个曾经这么熟悉的名字。闻夏,闻夏。
“闻夏,我以后干脆嫁给你好不好?你比那些男生还贴心!”
“闻夏,放学等我哦。”
“闻夏,以后我写的小说第一个给你看好不好?”
“闻夏......”
写秋轻轻地的说:“我不知道。很久没跟她联系了。”
班长失望地“哦”了一声,并没有在意,继续清点起另外没来的人:“童彤......”
写秋却依旧垂着眼帘出神。闻夏,那个曾经代表着永远的朋友、自己所有秘密的名字,又是什么时候生疏了的?
......
闻夏和写秋住在同一栋四合院里,那种四合院在这个北方的小城市里已经不多见了。房子不高,分为两层,写秋一家住一楼,闻夏一家住二楼。
很神奇又很正常的是,写秋的妈妈和闻夏的妈妈是从小到大的闺蜜,所以闻夏和写秋也是一对好闺蜜。当初怀着宝宝们的时候,两个妈妈就商定好,夏天出生的叫闻夏,秋天出生的叫写秋。闻夏写秋,怎么听都应该是一对好朋友的名字。
晚秋的风吹过小弄堂的道路,斑驳的石阶上悄悄爬过一只觅食的蚂蚁,深红色的枫树叶静悄悄地布满石板,安安静静的午阳镀在屋檐上。似乎在等待什么人的到来。
随着回荡在空气中的笑语声,路的尽头出现了两个女生。两人都蜷缩在莫名肥大的校服里面,一个女生扎着高高的马尾辫,辫子随着说话的频率有节奏地轻微摆动着,很漂亮,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精致感——这是普通甚至有一点点丑陋的校服所不能掩盖的。她的声音很清脆,听她说话就像在听百灵鸟歌唱一样。旁边那个女生则比她略矮一些,脸有些消瘦,但整体看来还是有那么一丝清秀在里面。她没有把头发扎起来,齐肩的短发老实地搭在校服上,长长的刘海还差一点点就要逼近眼睛了。她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于是这样一来,她那那种瘦弱里就又添上了一股书卷气。这就是写秋和闻夏。
一般来说,放学的时候,都是擅谈的写秋在兴奋地说一天的趣事,而闻夏永远是那个最好的倾听者。她永远都是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头稍稍往写秋那边偏一点。每当写秋需要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的时候,她总是非常中肯地发表一两句自己的想法,转而又恢复成淡然的样子。
“今天早上那个谁谁又迟到了,哎他怎么老那样啊,老师不是说他住得很近么......”写秋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像是迟到的人是她一样,比人家还懊恼。
“写秋,今天我在老师办公室里看到一个女生,应该是转校生,没见过。”闻夏罕有地打断了写秋没有意义的话题。
“哦?新生哦。不过谁没事会在初三转学啊。”写秋又摇了摇脑袋,马尾辫晃动。
“不知道。”闻夏见写秋似乎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就没再提起。
“我到家了。”写秋从包里掏出一连串钥匙,铜串在恰好的阳光下碰撞出清脆的声音,“今天作业好多啊,我有不会的会问你噢闻夏。”她招招左手,右手拿钥匙插进门锁中。
“嗯。”
“哦对了......闻夏!”
“什么事?”
写秋扬起左手,三指弯曲,比成一个电话的样子,冲房子旁边那棵高大的梧桐树摇了摇,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看闻夏。
闻夏先是愣了愣,随即会意,点点头:“知道了。”
这棵高大的梧桐树有着她们共同的秘密。如果不仔细看,没有人会发现梧桐树的枝丫间缠绕着一根长长的铁丝,这根铁丝从二楼东边的闻夏的窗户外,吊到一楼东边写秋的窗户外。铁丝的尽头吊着一个小篮子,只要写秋有什么东西要给闻夏,只用将东西放进篮子里,然后摇动铁丝,正在窗边写作业或者看书的写秋,就会听到系在铁丝上的铃铛的声音,再将东西拉上来,就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了。通常是写秋写些少女情怀的东西,然后传上来给闻夏看,又不会让家长发现。
闻夏笑着摇摇头,在心里隐隐觉得有些幼稚,但没说什么,回身继续往楼梯上走。每走一步,她的笑容就会隐去一点。直到最后到达老旧的家门门口时,她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疲惫,冷漠的秀丽面孔。
她不知道为什么,叹息一口气,手上拿着钥匙开门。
“我回来了。”
一句充满期待的话语,随即飘散在空荡的房间里。
没回来。
闻夏又叹一口气,站在门口开始例行公事的换上鞋底有些脱落的拖鞋。放下沉重的书包,她草草的往隔壁房里瞄了一眼。
还是没人。
她走到自己房里那张靠窗户的木头长书桌前,随意抓过一张写满潦草算式的纸,匆匆写下五个字,扔进垃圾桶。正准备开始写作业,却被突然响起的清脆铃声吓得手中一颤,一个字没写的练习册上出现了一道伤疤一样长长的黑色水性笔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