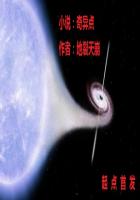我们顺着山路往前走,不多时,一个隐藏在山林中的竹子楼在我的眼里若隐若现。那楼古色古香,精致淡雅,更近一点时,我们看见了竹子楼的全貌。
竹子楼还有一处亭台,连接亭台的长廊横亘在我们眼前。亭台中,我们看到了一把琴弦。琴弦之前,有一张圆石桌子,围绕着圆石桌子的是三四张石凳子。
独门梨邀请我们坐在石凳上,她去给我们沏茶。
趁沏茶的功夫,大头环顾四周,对我说:大人,你猜马容,他会在哪?
我轻声地说:看现在的情况,他应该不在家。
我忽然想起一事,问大头:大头,我的剑呢?
大头想到剑,站起来,从自己身上开始翻找。
当我看见他从容地从裤裆中拽出我那把剑时,不禁瞪大了眼珠子。
那剑被大头用布缠绕包裹了起来。我接过剑,剑全身被大头的裤裆暖得暖和,但我闻起来,总有一股骚气。
独门梨端茶过来,看见我对那剑闻个不停,问我:你闻什么呢?
我感觉尴尬,收起剑,说:没,闻闻我的剑,香不香。
独门梨一听到剑香不香,下意识觉得这把剑是把好剑,她不禁也凑过来闻了闻。
一股骚气灌入她的鼻孔,她皱了皱眉,脸色一红,把茶放在石桌上,就离开了亭台。
其实这把剑的确是好剑,但谁说好剑就一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即使是散发着浓郁香气的好剑,在裤裆里捂久了,味道不还是会变。
世间万物都是互相转化的。
我又将剑递给了大头,并叮嘱他以后只要跟在我的身边,我的剑都由他保管。原因是我这个人是比较懒的,手中不喜欢拿东西,身上不喜欢带东西,一身轻松,逍遥自在,多好。
大头不得已接过剑,表示同意我的说法。
我又补充强调一点,不准再将剑放裤裆。
我怕的是这把好剑在大头的裤裆里放久了,就浑身上下散发出浓郁的骚气。以后如若我再跟高手过招或比武,剑刚拔出来,还没有出剑,对方就被这剑的骚气熏倒在地,那岂不是胜之不武,有辱我的名声,也不像我的风格。
大头将剑背在了他的身后。
他的流星锤中间的链子挂在他的颈椎上,两边的流星锤正好平衡,以和谐的姿态压迫着他的颈椎。
长此以往,他以后要是不得颈椎病,那才奇怪。
我盯着大头,大头不知道我为何盯他,浑身不自在。
大头不自在到摸了摸自己的糙脸,问我:大人,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我依旧盯着他,说:没有。
大头又摸了摸他的大头,问我:大人,我头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我还是盯着他,说:没有。
大头更加不解,问我:那大人这样看着我,是想跟我说什么吗?
我体贴地问大头:大头,你累吗?
大头随口说:累。
说完实话,大头忽然觉得在上司面前说累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他连忙改了口,说:不累。
改口的同时,大头还对我强颜欢笑。
我看着简单的大头活得都累。
我跟大头说:大头,你要是觉得累,你就不会先把你的大锤和我的剑放下?
大头忽然意识到这一点,忙听从了我的建议,卸下了他的武器。
大头刚将武器放下,一阵风吹过来。这风好像只穿梭在长廊中,以一个迅猛的姿态单方向冲击着我和大头。我们被风吹得瑟瑟发抖。天地间那样诡异。
大头和我都察觉到了这份诡异,大头旋转着他的大头,连续不间断地注视着四周。
我也同样如此。
我们同时转到背朝着琴弦的同时,忽然听见琴弦的响声。
第一声,三两句的调琴。
随着这琴声的响出,我跟大头同时眉头一皱,菊花一紧。那一瞬间,我们两个害怕到不敢转头的地步。
大头的眼睛乜斜向我,看见我同样乜斜着他。
我乜斜着朝他示了意,意思是让他转过头看看后面是谁在拨动着琴弦。
大头万分恐惧,颤抖着,牙齿响动着转了头。
与此同时,我也转了头。
只见马容一身从容地拨动着琴弦。
我起身刚要说什么,马容抬起手制止了我,轻声说:二位且坐,听马某给二位抚琴一曲。
我们两个坐定,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马容开始弹琴。
琴声刚开始缓慢悦耳,我不禁闭上眼睛,深深享受和陶醉其中。琴声连绵不断,声声入我耳朵,引发我情感深处的共鸣,那一瞬间,我看到万物宁静久远,山河大地,万古星辰,都在慢悠悠地运转。陡然间,琴声急促起来,像倾泻而下飞流三千尺的瀑布,像滔滔不绝的江水,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点燃人的情感,使人感到震撼,像巨大的锤子敲打在人柔软的心灵上,使其宣泄,使其爆炸。正当那琴声达到高潮之时,戛然而止。马容潇洒地一摆袖,姿态迷倒众生。琴声的感染力太大,以至于在其戛然而止之后,依旧在我的脑海中久久回荡,不能忘怀。
我睁开眼,看见马容也在看着我,那一瞬间,我们像是完成了心灵的交融,让我不禁暗自佩服马容技艺的高超传神。
大头脸上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
忘了,他欣赏不动琴。
琴罢,我鼓掌赞叹道:妙。马兄的琴弹得妙。
马容听我赞扬,不禁感觉渐入佳境,手托着下巴,一副享受的姿态。
马容问我:你是怎么找到这来的?
我说: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只有大头和我知道,我们是误打乱撞来的。
大头听我这慌撒得滴水不漏,一脸鄙视地看着我。
但我的目光很快又捕捉到了他的目光。当他发现我的目光捕捉到他的目光时,他匆匆地收了他的目光,转而露出讪笑。
马容又说:来找我何事?
我说:张大人的意思,还想请你回去跟他干。
马容不屑道:前提是我跟独门梨分开?
我点了点头。
马容更加不屑道:哼!他张千岭算是哪路货色啊,我马某人虽然不比他的名声,但好歹也是江湖中排的上号的人。当初他的人追杀我的时候忘了。
我继续说:张大人说。
马容猛然打断我后面的话,说道:别什么大人不大人的,那是你的大人,不是我的大人。他算什么大人啊,竟干些小人干的事。
马容的话音刚落,大头冷不防地就冲了过去,使劲出了一拳。
马容也完全没有意料到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匆忙仓促之中,他举起了他的琴他的琴挡了这一拳。
结果,琴弦全部崩断。
拳头砸的地方,也陷进去了一个拳坑。
时间好像定格在那里,马容眼睛大睁,嘴微启,出神地望着他那被毁的琴。
同样的眼神又看了看大头。
大头一脸恼怒地对看着他。
马容怒吼一声,出脚用力而迅猛,将大头踢到了我的身前。
为了防止大头后退到我身上,我下意识地出了掌推了大头一下。不料这一掌太过生猛,大头一下又被我推到马容身边。
大头惊诧地扭过头看着我。
我立马装作失手的样子,为了化解尴尬,我转移了注意力,对着我的手掌吹了口气,并使我的手掌抖动起来,装作不受控制的样子。
大头看见我这样子,又幽怨地转过头去。马容趁大头转头之后头还未稳的空隙,就一拳上去,打在大头的鼻子上。
大头结结实实受这一拳,头部向后呈现近乎平行地面的弯曲,步子又后退几步。
一声巨响,大头的大头砸在了桌子上。
他的眼睛还看着我,嘴里有气无力地说:大人,帮我啊。
我贴近他的脸,语气温柔地问他:你痛苦吗?
大头此刻自然还在头脑眩晕的状态当中,点点头。
我说:好,我会帮你的,帮你减少痛苦。
说完,我一下子拍在了大头的肚子上。
大头的肚子受到一击,痛处立马转移,整个人还没有从眩晕中缓过劲来,就不得已又站了起来。
他捂着他的肚子,脸色被憋得发青,青筋暴起,龇着牙说:大人,你,这是帮我?
我一脸认真,认真地朝他点了点头,说:嗯啊。为了减少你头部的痛苦,就只好先委屈你的肚子了。
大头哭笑不得,说:不是,大人,我是说让你帮我,打他。
我这才装作幡然醒悟的样子,指着马容说:打他啊?
大头使劲点了点头。
我点头,说:那好。
就这样,我跟马容开始了巅峰对决。
几片叶子随风卷起。
这个季节冬天刚过,春天刚来,好像并没有叶子。
空气翻卷而过。
高手在过招之前,都是先要用眼神过招的。
我注视着马容,马容也注视着我。
我用眼神对他说:一会儿我装作很挫的样子冲向你,你把我往他身上打。
马容心领神会,用眼神告诉我:好。
我吆喝了一声,奋不顾身、气势汹汹地冲向了马容。
到了马容身边,我握紧了拳头,抬起了胳膊,却被他一拳打飞,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大头的身上,将他砸翻在地。
视线中是长廊的天花板,我躺在地上,四肢大张,背下,我感到无比的柔软。
大头在下边近乎哭着说:大人,你压死我了,你赶紧起开啊。
大头的这一声哭嚎将我从柔软的幻想中强拉硬拽至醒。
我站起了身,大头也站起了身。
我真诚地看着大头,对他说:大头,这样不行,我们会吃亏的,这样,你听我的,我们两个一起上。
大头也真诚地看着我,说:好,大人,我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