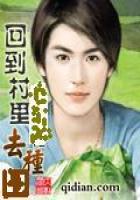绿皮车厢的新漆有些发亮,却藏不住那股幽深的铁锈的味道,车窗外的一切萧瑟无味完全算不上是风景,真是不懂刘妈老师挂在嘴边说这绿皮火车真是个好东西,我抬眼看看周围的人群,没有什么特别,跟葛家村里的村民一样一脸的老实忠厚,但是感觉每个人都在盯着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我动了动那双穿着当时唯一带在身边的黑色亮皮浅口高跟鞋的双脚,踢了踢座位下的皮箱,还在,看没人注意轻轻地将肉色西洋长丝袜的脚后跟从有些磨脚的鞋里解放了出来,稍稍卸下了心里的戒备,紧抓的黄色牛皮手包都被我捂得有些发热了,估计早上摸得雪花膏肯定糊了上去,心里边不觉有些想发笑。
走的时候太紧急了就拿了这个手包,身上的湖蓝色短袄和粉白色百褶裙都还是莺儿给我拿的,这么糙的料子搁以前我哪里肯穿,短袄的旗袍领微微有些扎脖子,所以我总是调整领子,期间的时间真的太漫长了,窗外的黑烟囱让我想起了葛家村,在这儿生活了三个月,这终于回去了还真有点想刘妈、刘大哥他们了,心里感觉空空的,眼泪不知怎么的止不住的掉下来。
打开皮包,包里还是那些东西,一盒夏士莲的粉底,一支小号的蜜丝佛陀口红,一支明星香水厂的新品紫罗兰香水,我拿起淡紫色的香水,手指间的摩挲感让我兴奋,可能是太长时间都没碰过这些东西了。
黄色牛皮内衬同样纹理高级质感柔软,我忍不住重温那熟悉的触感,这时火车进站,汽笛声和火车车轮的摩擦声更加刺耳,我一个不稳稍稍倾斜,原本扁平的手包一边一个小白条晃入了我的视线。
我急忙翻开包掏出纸条,铺开,是丹琪的花蕊系列的一支唇膏的发票签单,八月八号,时间就是三个月前我离开SH的那一天,还真是久我都快忘了。
车上的人群稀稀拉拉地走了很多,往窗外一瞄,果然,已经到了浦口站,月台满满得都是人,下车上车熙熙攘攘的旅客,吆喝不断的小吃贩子,一堆穿着单衣的挑夫袖子卷地老高跃跃欲试冲着火车门,眼神挑剔地只拉扯那些穿着整齐的旅客特别是那些穿着老式旗袍臀部扭地厉害的“太太们”。
窗外的热闹看着很是烦躁,笼屉内松针铺底的汤包冒着热气,骨头汤打底的百叶上小贩随意撒上一撮葱花滋滋的香味仿佛带着小贩的叫卖声穿透进车厢,里面的旅客早就坐不住了,咕咕两声我尴尬地摸摸扁平的小腹,不敢贸然出去,只好艰难地蹲下身子拉出皮箱,出门前刘妈特意嘱咐给我带了煮鸡蛋路上垫垫肚子。
我慢慢剥好鸡蛋准备放入口中,旁边一个小男孩的注视让我不得不注意,他乱糟糟的头发,稀溜溜的两条鼻涕挂在干燥的嘴唇上,我吞了吞口水把鸡蛋递给了他,还好只有一站了。
下车前我打开手包准备补个口红,诶,发票不见了,奇了怪了,我看看周围,旁边一个戴着黑礼帽睡觉的大叔就没醒过来过,对面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甜蜜地分享着一个香气袭人的烤红薯,刚刚他们分明下车了呀,我再一次看了看旁边的大叔,一动不动,不对,开始他是有些轻微的呼噜声的怎么没有了呢,他是不是在装睡?
我灵机一动,故意装作没坐稳倒在他身上,嘭的一声他直接重重地摔倒脑袋砸向右边的座椅,我吓得猛一起身,周围的旅客都躁动起来,砸过去的是位长相宽厚的中年人,他没说话只是扶起他归座,却不成想礼帽掉了一脸沉睡的大叔还是没醒,中年人走过来轻轻对着他耳朵喊了两声没有动静,众人的神经绷紧了起来,车厢难得的寂静。
中年人大着胆子拍了拍他的脸又使劲晃动他还是没动静,食指凑近他安静的鼻头下,手指微微颤抖,瞪大了眼睛,反应过来,下意识往后退了两小步,“他没气了!”
我迅速反应马上摸上他的脉搏,脉搏搏动停止,身体已经变凉,肌肉僵硬,瞳孔扩张,应该死了有几个小时了。做出了初步判断后,不禁有些后怕,心中一阵不安惶恐,麦子啊麦子你胆子还真是变大了呢!
终于到了SH站,刚下车一个清脆的声音就不停地喊着“小姐,小姐”,看着莺儿一脸的灿烂,我心中的乌云算是消散了大半。心里默默安慰自己,算了,别想那么多了。之后就回了家。
麦落
1926.11.12
”麦小姐,就这些吗?“
面前的警官脸放大在我眼前,我机械地点点头。
”丁警官,那天我知道地一字不落地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