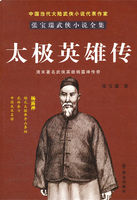独山洼浅山坡头上的洋芋像一个营养充足的尕媳妇使劲儿大着肚子一样,一天变一个样,四月头上就出齐了苗,五月中洋芋秧儿便盖住了地面。台地展开了明媚的面庞,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熬受了寒冬如同熬受了爱情折磨的女人们,终于渡过了荒年,后腰里别着铲子成群结队涌向洋芋地的场面酷似正月里涌向旱场往人堆里挤着看社火,除草松土的铲子泛着银银的亮光把女人们的脸照得通红,精心侍弄的每一个洋芋秧秧都是儿女们调皮的鬼脸,红头巾绿头巾把独山洼三百余亩浅山坡地打扮得比往年更动人。她们开始有了逞能的力气和嗓子,以一只手压住一只耳朵的百年如一的传统姿势,漫起了少年。而此刻的男人们也变得多情起来,他们放着大路不走,偏偏顺着田间小道挨着女人蹲下,厚着脸皮喊起了少年:
咂了个舌头亲了个嘴,
浑身上麻给了九天。
回忆到这里的时候,马长存像刚刚得体而圆满地做完一件事儿,脸上表现出了几分得意和满足。
湟水平静得如同睡熟了的婴儿,偶尔听见那一声两声流水的汩汩声,就像婴儿幸福而甜蜜的鼾声,间或,又像婴儿吃胀了母亲的奶水,打着长长的饱嗝儿,轻微而有节奏。马长存站起身来动了一会儿隐隐发麻的双腿朝前走了几步,他想抽一支烟,但摸了好几回都是空着手从衣服口袋里出来的,其实想抽烟只是一种意识,伸进衣服口袋里的手好几次都摸到了烟盒,但都忘记了把烟拿出来。马长存开始抱怨自己的忘性太大了,也许是老了的征兆吧,说话做事没有从前那么果断了。
马长存借着麻擦擦的月亮高一脚低一脚慢慢腾腾地走下去。他已经走过了那片白杨树林,此时,天空中浓一块淡一块的云彩开始慢悠悠地散开来。远处,苍茫的天宇似雨水洗过一样,西天又露出了半片片韭镰月牙,显得异常生动可爱。这时候,湟水离他只有一百步之远了,他借着突然间又亮起来的月亮的银光和自己的感觉,兴步而行。湟水拍打着黄土岸,发出啪啪的声音来,像是女人们从盆里捞出衣裳使劲儿在空中抖落着水,间或还能听见松软处黄土落在水中的扑扑声。他的目光透过树林的缝隙往河道里望了一会儿,河面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由于不是满月,所以水面上看不清月亮和星星的影子。
不远处,那棵百年老柳孤单地守候在村子的西头,树影投下来,正好掩盖了村西头的几个庄廓,黑沉沉的。朦胧的月辉中,老柳树壮实而精气十足的树冠混沌不清,分不清树干和树枝,只有那一片巨伞一样的树冠像一朵青云一样,任晚风尽情地吹拂,它那苍老的枝条左一下右一下慢慢地摇来晃去,迟缓得像一个长着罗圈腿的八旬老头。偶尔有一枝枯萎的枝条落下来,发出凄凉而绝望的声音来。
马长存心中油然涌起一种孤独和失落感来,明明知道自己老了却又无法挽回,权力逐步失去却又无能为力,使他的内心深处像刀子一下一下在刺。此时此刻,他又很自然地回想起土地承包后近十年来的一些事情来了。
那次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的砍伐树木的事件,虽然被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抓了一个典型,来了个杀鸡给猴看,刹住了那股风,但他马长存并不笨,尤其对周围的环境他是十分敏感的,他非常清楚而又冷静地感觉到社员们对他的尊敬不如从前了,尤其是土地和农具全都分给各家各户之后,那些年轻娃娃的面部表情就更明显了。有几个有些能力的虽然当面不敢说啥,但背后嚷着要当村长当书记的他也并不是没有听见。他之所以装着听不见,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形象,不跟年轻人一般见识。领袖早就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看来,鸡叫狗咬是有个时候,着急是不行的。
马长存虽然这么平心静气地想问题,但真正着急的还是他自己。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主动权和自主权,这块地里种啥那块地里种啥再不会来请示他了,他也不会有站在旱场上指手画脚今儿干啥明儿干啥的那种得意劲儿了。过去敲钟出工或全大队人围着旱场分粮的时候,社员们离不开他,是因为跑水、跑化肥、跑农机、打庄廓、招工、当民办老师都需要他跑路子找门道。现在,他那种特殊的地位和身份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发生了改变,他在他们眼里虽然还是书记,但含金量远远地不如从前了。
当应该让马长存知道或者让马长存点了头才能操作的一些事儿,却没人告诉他就在村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之后(比如盖新房、立大门之类),马长存的自信心便大大地打了折扣,他开始怀疑自己在村里的权威了,孤独和愤怒越来越影响着他的情绪,无名之火烧得他心口窝发烫,却无处发泄。如果说村里岁数和他差不多的人有点对抗心理的话,还能说得过去,可团支部书记刘海林这年轻娃娃给他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想建一个大理石加工厂,这就让他想不通了。驴日的贼尕娃们,人心没有鸡蛋大,骑了骡子想骒马,想吃个天爷的熬饭,还要个金碗银筷子哩!五八年大跃进不是也办了工厂吗,咋样?还不是胡日弄了一阵子。土地天生就是种五谷杂粮的。
马长存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刘海林想搞大理石加工厂的念头犹如怀在女人肚子里的娃娃一样一天天疯长着。那些日子,刘海林像热锅上的蚂蚁见天价跑东宁、西宁,跟几个建筑公司拉关系跑销路,要把石头变成一沓沓的票子。而对于马长存来说,要把油花花的十亩水地跟石头疙瘩和现代化的高楼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让他产生不了一点兴奋,相反地,好比用五寸尕藏刀在他的骨头上刮肉。为了台地大队,为了一分一亩的土地,他曾伤过多少脑筋,他苦苦经营了三十年,三十年啊。为了吃饱肚子,人干的事情他干,人没干的事情他也干了。凡事不能光往钱眼里钻,钱是个啥东西,是人身上的垢痂洗了一层又一层。钱是一泡臭狗屎,越挨得近越臭,能把人心染黑。刘海林把台地变成小城市,算他娃娃的本事大,可要占石得海大地的十亩水地是绝对不行的。而对于刘海林来说,开矿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事情。上面的政策不就是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吗?光守着二亩土地,就是把金子种上也发展不起来,可马书记咋就听不进去呢?那些天,刘海林一有空儿,就双手托着下巴望着台地村对面的石山出神,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优质大理石。他仿佛看见大理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厂房烟囱拔地而起,台地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身为村支书的马长存虽然表情很沉着,但心里一点也不踏实。他每天远远地绕着石得海大地走过,冷冷地看着刘海林那自得的样子,心里暗暗自语:娃娃,只要不破坏山头上的植被,加工大理石我并不反对,可你要占村里的水地,就是我马长存点头了,社员们也不会答应的。不信就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刘海林万事俱备之后,就来求马长存组织村里的头头脑脑开个会。白天答应好了晚上要开会,可吃过晚饭马长存有意串了远门,过了午夜才慢腾腾地摸回了家,让刘海林空等了一晚夕。马长存心里明得像镜子,自己在村里的威信虽然不如从前了,但还没有到无足轻重的份儿上,只要他不参加,就是刘海林有天大的本领也弄不起来。前几日,儿子甜言蜜语地劝他,儿媳妇也娇滴滴地左一声大右一声大,又是敬纸烟又是倒茶,充当刘海林的公关小姐。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清楚得很,这都是刘海林的外围战。你刘海林真能行,比乡长的章法还大,自己不来,却打发我儿子和儿子媳妇打前站,我就是不买这个账。
第二天晚上,刚吃过晚饭马长存就假装感冒头痛早早地躺下了,刚把被子捂在头上刘海林就来了。马长存知道,刘海林迟早会来找他的,只要刘海林求上门来,他就要好好教训教训。
刘海林进了屋,先问声好,然后站在了炕沿跟前。马长存装了一会儿装不住了,便从被窝里懒懒地爬起来,披了衣服盘腿坐在炕上,半睁半闭着眼睛,不说坐,也不说不坐。
“马书记,我……”
“我弃权啦!”还没等刘海林把话说出口,马长存便堵了回去。
“老支书,你看,你老先不要生气,办好办坏是大家的事情,我们年轻人嘴上没毛说话不牢,还指望你给大家做个工作。你老八百多口人的父母官撒手不管,咋能成哩!”
刘海林专挑好听的让马长存听。马长存听了这些顺耳话,果真起了变化,失去平的心像熨斗熨了一样。他就喜欢听这样的话,土地承包到各家后,尤其是把村里的集体财产呼啦啦分干了之后,社员们的腰仿佛一夜间粗壮了起来,就从未对他这么尊敬过,虽然当面还不敢顶嘴,说话的时候也似乎洗耳恭听,可下去后就是不按照他说的话去做。他对这些情况清清楚楚,可各扫门前雪了,当面又无法找到整治的办法。现在,马长存半闭着眼睛泥神爷一样听着刘海林蜂蜜一样的奉承话,舒畅得像趴在长条椅上有人给他搔背。瞬间的满足之后,他突然睁开了眼,肩膀耸了一下,指着刘海林的额头愤愤地训道:
“海娃,看你还懂一些人情事理,我就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都是农民,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庄稼人就得本分,老老实实种庄稼才是庄稼人的根本。水有源木有本,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去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记住这些,即使错也不会有大错儿。甭日弄那些个没边没结果的事,钱这东西到头来都是空的。”
“可大多数人都赞成这么搞,人家河南、山东的农村都在轰轰烈烈地搞,电视、报纸上天天宣传,我们再不办起来,就落后了。再说乡政府也是很支持的。”
“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窍。人家河南、山东搞是人家的实际,基础好,我们村还不成熟,还需要等待和过渡。需要过渡,懂吗?这是吃饭,不是耍瓦砣儿。”
“书记,你这是言过其实,没那么严重吧,不就是十亩地吗?石得海大地不行,往其他地方考虑也行嘛。你算算看,就是每亩打一千斤粮食,十亩地能打多少?再扣去籽种、化肥、各种收费,还剩多少?再说县上乡里都是批了条子的,就等你的话哩!”
“这个口子我不能开。”马长存异常坚决地说。
“你老人家就高抬贵手,放个话吧。反正上面有条子,就是一时半会儿错了,有上面的条子挡着,也怪不了你。”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噢,土地是随便批的吗?想批给谁就批给谁,这又不是我马长存的私人财产,想咋样就咋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你老召开个会,做一做社员的工作。”
“工作我可以做,但占水地不行。”
“不行?”
“就是不行,除非我马长存不当这芝麻官。”
这一老一少的对话持续了三天,第三天,马长存没有想到,刘海林把王乡长给请来了。
乡长一进门就握住马长存的手,马长存也不示弱,抢先开了口:“乡长大驾光临也不早打个招呼,来来来,到里屋坐。”
“好书记哩,我想坐,可坐不住哩。海林的大理石加工厂办不起来,我这个乡长给党委没法交差,还请老书记多多包涵。”
王乡长看上去很年轻,比刘海林大不了几岁。马长存死缠硬拉把王乡长拉进里屋倒了一杯茶。王乡长就势接住茶杯说:“老书记,你看这事咋办?”
马长存没有说话。其实他马长存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包涵,让我包涵啥?想占地占多少还不是你们说了算。看来,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就跟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自己的力量再大,也是无法阻挡的。一九八零年,土地刚刚承包的时候,自己也是极不情愿的,可最终还是轰轰烈烈地分了。想到这里,马长存含含糊糊地说:“这个么,这个我考虑。”
其实,马长存的考虑是多余的,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执行而不是考虑。乡党委已经决定的事情,他不同意也得同意,乡长亲自大驾光临,完全是出于要给他这个老书记给一个面子。
刘海林的大理石加工厂是怀胎十月的媳妇,想生也得生,不想生也得生,台地村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大理石加工厂建成那天,听见石得海大地那边第一声鞭炮响,马长存的心里便咯噔一下,接着隐隐作痛。马长存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如果说那次砍伐树木是对他权威和地位的试探性进攻的话,那么,这次不管他反对就占地建厂,就是对他权力的公开挑衅。虽然心里的那一下“咯噔”刚刚过去不足一分钟时间,刘海林就来请他,并把他让在主席台上就座,但他的感受就像被人强奸了又当着他的面说他如何如何纯洁高尚一样。
也就从那件事情开始,马长存灿烂辉煌的历史,如同深冬默默无闻的湟水东流而去,远远地消失了,他从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变成了一个阴郁、沉闷的孤独者。他的威信虽然还没有完全失去,但他分明感觉到自己再也无力维持过去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了。
马长存每天走过村口时,不免要仰起头来看一看那棵老柳树。老柳树实在太老了。而那口用钢板焊接成的柱状的大钟,由于雨水的浸蚀,生出了一层厚厚的铁锈,完全失去了铁的光泽,高高悬吊在柳树苍老的枝杈上,苍茫成一疙瘩黑云。而那块能够敲出使他愉快和自信的节奏的钢轨接头的夹板儿,也不知让谁家的娃娃当废铁卖给了收购站了。这帮败家子,有一天说不定连自己的婆娘都卖掉哩!可怜的马长存仿佛一个耍猴子的下路人丢了鞭杆和锣似的,一时没有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