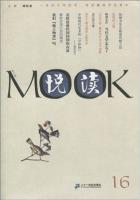半年后,江农生从省委党校回到酒泉258队机关。
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吴书记的办公室,室内一个简易书柜,一张办公桌,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放下东西后,直接到吴书记办公室,两人谈了一会儿工作的事情,临出门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对吴书记说:“吴书记,咱们四分队的炊事员崔永杰都快六十岁咧,身体也不太好,你看能不能把他给调回大队来,重新安排一个工作?”
“那个老怪物啊,哼,他哪里肯听劝,有些情况你不了解,你以为我不想调他回来呀?”
“那为什么一直没有调回来嘛?”
“他和我是老战友,当年我们俩是一个团的,我是团政委,他是一营营长,当年他可是响当当的人物,由于作战勇猛,多次立功,还上过报纸呢!”
江农生吃惊地问道:“那他怎么在我们队当了炊事员咧嘛?”
吴崇光喝了一口水,慢条斯理地说:“你听我慢慢说,转业到咱们队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行政科长,干了一个月不到,说啥都不干了,他说自己没文化,当科长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劝说都不行,没有办法,我们就征求他的意见,看他自己想干啥,他说自己参军前在小饭铺里干过大师傅,觉得做饭自己没问题,我们就安排他到大队食堂做饭。”
“那他咋跑到野外去咧嘛?”
“这老伙计坚持要到野外分队去做饭,理由是野外分队的生活还有点部队生活的影子,没办法我们就想啊,让他先去过过瘾,几年后再调回来。这些年,每年我都要跟他私下谈几回,就是谈不拢,他还呆上瘾了,最后,我们就直接下调令,给他当时所在的二分队又安排了一个炊事员,让他失业,逼他回大队来,谁知他背了一口行军锅直接奔玉树沟了,噢,对,就是你当时负责的项目组去了,把我搞得哭笑不得,只好由他去了。”
江农生联想到平时崔永杰的表现,顿时心中肃然起敬。
“要说他这个人啊,思想境界在咱们全队是最高的了!别的不说,就他的劳保现在积存了都有十几年的了。”
“他为什么不领嘛?”
“他呀,所有的工作服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地穿,就是经济员追着屁股给他发他都推三阻四的,要么让发给衣服不够穿的同志,要么说自己有穿的,不需要,反正是发不到他的手里。”
“崔师傅确实是一个政治觉悟高、思想过硬的好同志啊!”
“要不这样吧,你明天和组织部长李爱民去一趟四分队,宣布一下对陈少华和邵建勋的任命,顺便再和老崔谈一谈这个事儿,这老伙计该退休了。”
“好吧,明天我就去。”
到达四分队转运站时,已经下午四点了。
刘玉荣和王海英正在柴火堆旁整理柴禾,三个孩子在房子前面打闹嬉戏。
一见江农生他们下车,大家都围了过来,江农生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分给孩子们,抱起最小的尚小阳使劲儿亲了几口,他对两个女人说:“孩子们长大了,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不能耽误了学业,等明年开春你们写个住房申请就回大队,让孩子上学吧。”
两个女人连连点头。
“刘文卫和葛小宁去哪儿咧?”
王海英说:“你还不知道吧,前些天这条路就修通了,今天一大早,他们就拉了一车东西去分队了,再过几天把这里的东西拉完了,我们也要跟着到分队去,这个转运站就撤销了!”
“路都修通咧?我原本打算要在这儿住一晚上,明天再去分队呢,现在看来不用咧。那二位嫂子你们忙,天色不早,我们就继续赶路咧。”
江农生坐上吉普车,直奔四分队而去。
到达分队的时候,大伙儿正在吃晚饭,一看江农生来了,一个个高兴得放下饭碗围过来亲热地握手。
邵建勋凑过去对着陈少华的耳朵悄悄说:“江书记来了,我去让炊事员烧一条鱼,再做一盘螃蟹你看咋样啊?”
陈少华蹙了一下眉头,看了看江农生半天没有吭声。看陈少华不作声,邵建勋直奔厨房,叮嘱崔永杰加菜。
“不就是江农生来了吗,加什么菜啊,有什么就吃什么嘛,我就不相信,他江农生才离开分队半年时间,就学会搞特殊了。”
“哎呀,你小声点好不好,人家是党委副书记,跟以前不一样了嘛,现在到分队来是客人了,咱们应当热情招待老领导才对。”
“我只认识江农生,不认识什么党委副书记。”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怪不得这么大岁数了还在野外做饭。”
“邵建勋,你说的是啥话?野外做饭就低人一等咧?党委书记就该搞特殊咧?革命工作分工不同罢咧,我莫想到你的等级观念这么严重。”江农生走进来。
“江书记,我是想,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江农生打断他的话,厉声说道:“莫解释咧,刚要提拔你当副分队长,你就觉得比别的同志身份高一等咧,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手划脚咧,就可以不讲原则咧,谁给你的这个特权,崔师傅是个普通的炊事员,可他的思想境界不比谁差。”
邵建勋额头上渗出一层汗珠。
“这件事你必须从思想上作出深刻的检查,并且要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的职务是变咧,可是不管如何变,我们的目的都是为祖国建设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这一点到啥时候也不会变。”
“江书记,我错了,我一定吸取教训,从思想深处做深刻检讨。”邵建勋悻悻地走出去。
崔永杰笑了:“就是嘛,你江农生也不像是搞腐化的人嘛,原来是这小子搞的鬼。”
吃饭的时候,组织部长李爱军问江农生:“你看邵建勋的任命怎么办?”
“对邵建勋的任命,是队党委的决定,咱们俩无权私下更改,所以,还是照常宣布,他这个人我有一定的了解,本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就是好大喜功,爱搞一些吃吃喝喝拉拢人心,投机钻营的小动作,所以对他还要进一步批评教育。”
李爱军点了点头。
晚上开完会,已经十点了,邵建勋内心沉浸在刚才对他的宣布任命上,兴奋得红光满面,有话没话地跟这个人搭讪两句,再找那个人调侃一下。
江农生走出饭厅,抬头一看,天空乌云密布,他对陈少华说:“恐怕这两天有大雨,要注意防汛。”
“就是,看这个样子是大雨。
两人刚走进宿舍,外面就噼里啪啦地下起了雨点儿。
第二天,滂沱大雨像扯起珠帘般从天上直垂下来,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犀牛江的水开始上涨。
江农生、邵建勋和陈少华带着十几个人,把坡下库房里的备用设备一件一件地往坡上搬,到天黑时已经搬了一大半,劳累了一天,大家累得实在搬不动了,邵建勋让大家停下来。
半夜时分,干了一天重活儿的江农生,睡梦中听见有人大声喊道:“大家快起床,发大水了!”他一骨碌爬起来,顾不得穿上衣,只穿了条裤子,胡乱蹬上鞋子,就冲了出去。跑到库房边,尚大有已经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搬出了一些物资:“江书记,必须赶紧把库房里剩下的东西转移到坡上,不然就来不及了!”
“嗯,快把箱子递给我。”江农生伸手接过一个木箱放到附近的坡上,自己回身也“扑通”跳进了水里,其他人也冲了过来,一阵紧张忙乱之后,库房里的东西总算搬完。
江农生从齐肩深的河水中筋疲力尽地爬上岸,嘴里招呼着:“大有,快上岸。”
相继爬上岸的同志们刚想喘口气,水中的尚大有突然指着前方说:“不好,储油罐快漂进犀牛江了,快,给我一条绳子。”
说话间如潮的大水迅速没过他的脖子。
江农生见势,焦急地喊道:“大有,危险,快上来!”
“没事儿,我水性好。”
岸上的人扔给他一条绳子,他牵着绳子快速游向储油罐,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绳子捆在油罐上,他浮出水面,躲到一边大喊道:“快拉。”
谁也没料到,正当他专心致志指挥大家拽储油罐时,死神却一步步向他逼近,一棵顺流而下的大树正快速从背后向他扫来,等江农生和岸上的人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发现后,一起拼命地喊道:“快躲开,危险!”
顷刻间,大树重重砸在了尚大有的后脑勺上,岸上的人顿时被突然发生的变故惊呆了,水面翻着浑浊的浪花,刹那间尚大有的脑袋没入水中,没有一丝踪影。
江农生一把抓过一盘绳子,往肩膀上一背,朝犀牛江的下游飞快地跑去,身后,其他人也打着手电筒沿岸追了过去。
又跑又喊了一个晚上,天慢慢亮了,所有人的嗓子都喊哑了,可是再也没有见到尚大有的影子。
一连三天,人们继续沿江搜索。直到第四天,江水逐渐退去,搜寻的队员在离营地三十多公里、河道比较狭窄的江边,发现淤泥里露出人的半边身体,大伙儿连忙用手刨,挖出了一具尸体。几天的江水浸泡,尸体已经整个泡胀变形,童志鹏仔细地辨认,当看到遗体左胸口那颗熟悉的手指盖大小的黑痣时,他泣不成声:“是他,是他!大有啊,我的好兄弟!你咋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
周围一片呜呜的哭声。
童志鹏悲痛地拿出一块床单,盖在尚大有身上,呜咽着说:“兄弟,咱们回去吧。”大家把尚大有的遗体放在担架上,一起抬回到营地。
分队顿时笼罩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江农生把陈少华拉到一边说:“你叫上司机小李,坐吉普车去一趟转运站,把海英嫂子和孩子接到这儿来,无论如何,我们得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陈少华迟疑了半天说:“还是你去吧,看到他们尤其是两个孩子,我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还是留下来做一些善后的工作比较合适。”
江农生沉思片刻,叹了口气说:“嗨,这事谁都不知该咋说哩,可是我们必须去说,好咧,就我去吧。小李,发动车,去一趟转运站。”
看到昔日再熟悉不过的丈夫面目全非的脸庞,王海英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曾经朝夕相处的亲人就这样一句话也没有留,撒手抛下他们娘儿仨而去。她欲哭无泪,眼睛痴痴地望着丈夫的遗体,嘴唇翕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梁爱华眼含热泪,背着药箱蹲在她身边,轻轻抚摸她的脊背,恨不得能为她分担一点儿痛苦。
“嫂子,心里难受就大声哭出来吧,憋在心里会落毛病的。”柳惠琴低声劝她。
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乖乖地跪在父亲的遗体旁,仿佛在等待酣睡的父亲从梦中醒来,很久很久,儿子尚小阳伸出小手,轻轻碰一碰父亲冰凉的手,奶声奶气地说:“爸爸,你咋还睡呀,咱们回家去吧,我饿了。”小家伙看父亲无动于衷,站起身来到母亲身边,用手摇晃母亲:“妈妈,爸爸啥时才睡醒呀,爸爸最听妈妈的话了,你快告诉他小阳饿了,我们回家吧。”
王海英眼睛呆呆地盯着丈夫的脸庞,似乎没听到儿子的话语,任凭小阳摇动她的身体就是不吭一声,只有两行泪珠簌簌地落下来。
人们不忍心再看这个场面,都抹着眼泪扭过头去。姐姐尚小玲懂事地拽过弟弟,哄着他说:“小弟乖,我们不饿,我们等爸爸醒了再吃饭。”她说着话把脖子上挂的爸爸为她磨制的山桃核属相取下来给弟弟挂上,尚小阳手摸山核桃似懂非懂,点点头,跪在姐姐身边,不再说话。
墓穴挖好了,大伙儿抬着棺材,缓缓地放入墓穴中,大家肃立默哀。沈兰、梁爱华、柳惠琴将手中捧着的野山花轻轻搁置在棺木上,生怕惊醒了躺在棺木中的尚大有。
江农生看一眼王海英和孩子,默默地拿起铁锨,铲起第一锨土,倒在了棺木上。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直跟妈妈跪在坟前的尚小玲突然惊恐地抬起头,猛地站起来,发疯般推开大家,跌跌撞撞地跑到江农生跟前,小手抓住江农生手中的铁锨哭喊道:“不许你们埋我爸爸……不许你们埋我爸爸……”
江农生鼻子一酸,大声喊道:“梁医生,把孩子带走。”
尚小玲又跑到陈少华身边,抓住铁锨大叫道:“不许你们埋我爸爸!”
瘦小的身影,凄惨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一直听话地跪在地上的尚小阳,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见身边的妈妈不住地掩面哭泣,吓得不知所措,哭着跑到姐姐面前,拽住姐姐的手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我不要爸爸睡在那里面。”
柳惠琴和梁爱华哭着上前,抱起两个挣扎的孩子,离开了人群。
黄昏时分,整个营地异常沉寂。
宿舍里,梁爱华和柳惠琴守在王海英身边,温言细语地安慰着她。沈兰陪在两个孩子床边,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故事。
江农生看到这一切,心中稍稍有几分安慰。他来到炊事员崔永杰的房间,崔永杰递给他一茶缸开水,又不慌不忙地装了一锅旱烟,使劲地吸了两口。
“崔师傅,我来的时候,吴书记再三叮嘱,说你该退休咧,身体也不太好,继续留在分队不合适,要你跟我一起回大队,重新给你安排工作,这次你就不要再推脱咧,收拾一下,明天咱们一起回去。”
“小江啊,谢谢组织对我的关心,眼下我觉着我在这儿还行,你也不用再多说了,我再干个把年的,等哪天我自己觉着留在野外不行了,成了大家的累赘了,到时候不用你撵我,我会主动去找你的。”
再多的话也没用。沉默了一会儿,他又问:“崔师傅,当年你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为什么转业后放着行政科长不当,非要跑到野外做饭呢?”
“我大字不识几个,干不了行政科长。”
“可是,你是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是立过赫赫战功的大英雄,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即使不干什么,别人也不会说啥的嘛。”
崔永杰磕磕烟锅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啊,总得掂量点儿自己,要闹明白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不能没个分寸,只想着往上蹦。我参军前就是一个小饭铺里的大师傅,除了这个,我啥都不会,哦,打了几年仗,立了点儿功,我崔永杰水平就提高啦?不是那回事嘛!当行政科长,我是门外汉,那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嘛,自己难受不说,还尽误事儿,那图个啥呀,你说是不?”
江农生沉默了,他被眼前这位老人朴实的话语深深感动了。
静静的山林道路旁,站满了分队的同志,他们是来跟王海英和孩子告别的。一一握别之后,江农生带着满含泪水的王海英还有两个孩子,以及组织部长李爱军乘坐吉普车离开了大孤山。与此同时,转运站那边,刘玉荣带着童川乘坐刘文卫的卡车出发,也行驶在回酒泉258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