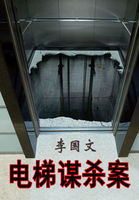乌云又厚又低,在山峡间涌动弥漫,似猛兽般铺展开它巨大的躯体,张牙舞爪地笼罩着海拔4200米的轮空大坂。周围满是重重叠叠荒凉不毛的山岩峭壁。纵横交织的窄窄的山缝,被沉积的雪屑分割成黑白相间的网格状。无底的深谷黑洞洞的令人目眩。
冰雪泥泞的崎岖山路上,两百多号人的队伍,拉得长长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吧嗒吧嗒的鞋泥接触声、声嘶力竭的吆牛声、肩上负重机械的吱咛声、偶尔岩石滚落山涧的隆隆声,各种怪里怪气的回声,回荡在山谷里。
清一色厚重膨胀的羊皮大袄敞开着,裸露着里面白色的羊毛。清一色的军绿色遮耳棉帽呼扇在两颊,分不清是男是女,蛇形散布在半山腰上,一点一点向前蠕动。
“李钢,扛不动了咋的?你瞅你那小腰拧啊拧的,白瞎你个男人了。”
“莫有,莫有,路太滑咧嘛,我害怕着小心走哩嘛!还是柳机长你厉害歪,我们两个男人扛得起的钻杆,你一个人扛着不费吹灰之力嘛。”李刚瘦小的身体扛着机台木喘着粗气。
“咋啦?眼热啊,信不信,你三个李刚我都能扛得动。”膀大腰粗的柳惠琴一本正经地说。
“哎,李刚,柳机长都发话了,还不赶紧让扛上,你这干巴瘦的身体,快省把子力气吧。”有人笑。
李刚笑着嘟囔道:“我又莫想着省力气,我是真心佩服咱们柳机长能干歪。”
“劳驾,让让道,大机器过来了。”背后有人喊。
前面的人急忙闪开。
“一、二、咳吆,一、二、嗨哟!”不断地有多个人搭伙抬着重机械吱嘎吱嘎缓缓向前移动,哈气成霜的嘴巴里吆喝着整齐低沉的号子。
分队长杨顺水和支部书记唐寅跑前跑后指挥照应着队伍。
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吴书记,强忍着关节疼痛,手执树棍作拐杖,和工人们一起扛着钻杆儿往前走,山路湿滑,脚下禁不住有点儿踉踉跄跄步履蹒跚。
“吴书记,跟您说多少遍了,咋就是不听劝啊,您指挥着大家走好就行,别再扛了,这么滑的山路,有个好歹咋办嘛。”
浓重的山东口音,豁达敞亮的声音:“我没事,没事,这不是好好的,跟走平路有啥区别嘛。你们不用管我,快去照看队伍,看看后面的女同志,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吴书记回头不停地叮嘱身边的同志:“我说老少爷们,脚下长只眼睛,千万小心不要滑倒了。”
驮满物资的牦牛艰难地前行。
江农生、“猴子”、郑魔术、童志鹏、柳田宽和一帮新招工的年轻人每人赶着一头驮满物资的牦牛前进,越往前走,山路越陡,牦牛前蹄打滑,抑制不住恐怖,向后倒退。
“借道,借道——”扛着机台木、扛着钻杆儿的同志一个个从身边走过。
“驾——驾——驾——”小伙子们怒目圆睁,疯狂地拽住牛枷,用肩顶着,一手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着牛背,一边用变调的声音大吼着,没走几里地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我娘娘,狗日的歪,咋摊上这么个鬼差使咧嘛,在老家下地干活也莫这么累过,老子这辈子咋就这个苦命,走到哪里都要下苦受累,好不容易到地质队当上工人咧,还是离不开跟这铁牛打交道。”廖爱国恼火地脱下招工时新发的羊皮大袄,捆在腰间,嘴里不住地抱怨着。
“猴子”棉帽掀到脑袋顶上,擦把汗,上气不接下气地打趣道:“你可别、别骂牛,它这么离不开你,说不上他就、就是你前世的老婆,要、要跟你永生永世白头到老呢。”
大家哄笑。
“呸,你前世的老婆才是牛歪。”廖爱国说着也禁不住笑起来。
“哎,我说你这个郑魔术,这会儿咋没得动静了,快快施个魔法把这些的东西都变到目的地噻,我们空手走路才轻松自在,大家说要得不嘛。”柳田宽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
笑声,有人学着他的腔调:“要得,要得。”
“嘿,你柳田宽怀疑我,对不对?你当我不能变啊?说实话,我是不想抢了大家的功劳,你也看到了,大家干起革命工作这热情多高啊,热火朝天的,生怕落在别人后面,谁乐意当落后分子,是不是?我一个人把活都干了,我当了特等模范,你们大家伙咋办嘛,不都对我有意见了嘛,我可不能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不过,我给你们先说好了,赶明儿有空了,我还真给你们来个大变活人,让你们开开眼界,这牛皮可不是吹的啊。”满脸络腮胡的郑魔术气喘吁吁,半真半假地说。
话虽有些夸张,江农生却不觉得有啥,肩膀死死抵着牛枷,心里着实有些佩服这个山东汉子,长这么大,他可是头一回看到耍魔术,那可叫大开眼界啊,想着就神奇。虽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脑海里还是浮现出刚招工那天,他走进大接待室的情景……说是接待室,其实是一个废旧的大仓库临时改造的大房间,高高的房顶,南北各有几扇大窗户,靠墙是一个挨一个的通铺。天气冷,大家都集中在房子中间用钢管焊接的大火炉旁,炉火熊熊燃烧,火苗蹿得老高,热气扑来,顿时感觉全身暖融融的。
江农生凑到跟前,放下行李,有人示意他把东西放在东边门后面堆放工具的地方,他连忙走过去把东西放好。
火炉旁,大家正兴致勃勃地观看一位穿着中式棉袄的小伙子耍魔术。小伙子留着小分头,满脸络腮胡,情绪激动,操着山东口音,嘴巴不停地解说着:“大家想过没有?什么叫魔术?魔术魔术,这个‘魔’字很关键,我把你麻痹了,我就开始捣鬼,这就叫魔术。”
一片笑声。
灵活的眼神骨碌骨碌闪来闪去,眼疾手快地拿出一个乒乓球,左手上亮一下,右手上又亮一下:“看好了,看好了,变——”双手一拍,啪!手上的乒乓球不见了。
“哇!”周围一阵惊叹声。
所有的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想看清楚他在哪里捣鬼,他却出奇不意,从后脖颈处慢慢挤出一个乒乓球来,神情得意地说:“它又乖乖回来了。”
“他捣鬼了,捣鬼了!”有人叫。
“对,我捣鬼了,我不是说了吗,魔术魔术,就是捣鬼。”
“那你再变一个,我就不信看不清你捣的鬼。”又有人叫着。
络腮胡笑了,有礼貌地对坐在身边的高个头小伙子说:“这位兄弟,我能借你的钢笔一用吗?”
小伙子叫姚建北,外号“猴子。”他看看对方,再看看自己插在中山装上衣口袋里黑灿灿的英雄牌钢笔,这是临来时对象赠送给他当工人的礼物,他有点儿舍不得。
旁边的人起哄,说:“就借给郑魔术用一下嘛,用坏了,他捣鬼给你变个更高级的。”接着又是一片笑声。
没等猴子反应过来,钢笔眨眼间就到了郑魔术手中。
“呦——”周围一片惊叹的唏嘘声。
郑魔术左手伸展,托着这支钢笔,看到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手,笑着对大家说:“这回看好了,看好了,我要把它送走了,走,走——”说话间左手猛地攥成一个拳头,再展开时,房间里的人惊呆了!江农生目瞪口呆,钢笔在他手中真的不翼而飞。
“这位兄弟,想要回你的钢笔吗?麻烦你去那张靠西面的床铺上拿一下。”
所有的眼光刷地投向“猴子”的床铺,周围一片窃窃私语:“你看到他咋捣鬼的?”
“不知道,我眼睛都没眨一下,也没看出咋捣的鬼。”
“没看见他挪地方啊。”
“太神了!”
“哪还用说,人家招工之前在杂技团干过两年,是真正的魔术师。”
“猴子”半信半疑地走到西面自己的床铺跟前,上下左右寻找着,顺手掀开枕头,哈,黑灿灿的钢笔就在这里。他举起钢笔,激动地对火炉旁的人喊道:“找到了!找到了!”
“哇——”满屋子的人都对郑魔术投去惊讶羡慕的目光。
郑魔术满面红光,双手抱拳:“献丑了!献丑了!”
人群中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江农生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耍魔术变戏法的,这么精彩的表演简直不可想象,自然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跟着大家使劲儿鼓掌,拍得手生疼生疼的。
江农生心想:凭郑魔术的本事,变个大东西呢,肯定也能成哩,你想嘛,众目睽睽之下,钢笔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变走咧,谁能做到——神仙才能做到歪!他侧过头,左右端量这个郑魔术,也莫啥特别的地方,倒是跟自家村子西头的全脸胡狗娃哥还有几分相像哩。
队伍突然停止前进,牦牛和负重的人都停止前进了。疲惫的人群有些焦躁不安,谁也不晓得是咋回事,隔着人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到——满眼里还是黑压压的云层和清一色的棉帽,再往前,那边是陡崖峭壁,远远看去,山峰倾斜着,好像要跌栽过去。
“前面咋不动了?就这老牛拉破车的速度,猴年马月到百泉啊?”有人叫喊。
“走不动就乖乖让开,让我们能走的到前面带路。”
“前面的,咋不吭气,到底咋了?”
“……好像是路不通了……”
支部书记唐寅和分队长杨顺水跑到吴书记面前。
“吴书记,前面接近山崖最狭窄最陡峭的转弯地段,大机械很难过去。”
“通知大家少安毋躁,原地休息几分钟。走,我们过去看看。”吴书记说。
吴书记小心翼翼接近陡壁,路窄得只有侧着身才能行走,不能转身,也不能回头,头顶上方凸出倾斜的巨大山岩把天遮住了。
“吴书记,我来——”
“我来——”
“你们没有经验,还是让我看看。”吴书记小心试探着迈过去。骨碌骨碌的小碎石滚落山涧。
“吴书记,千万当心!”
巍峨高耸的山崖转弯处,吴崇光的身体紧贴向外倾斜过来的山岩,眉头紧蹙,表情严肃,他仔细观察转弯地段的角度,又反复踱步估量坎下坡度尺寸,眉头逐渐舒展。
“我有个想法,你们看中不中?”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其他两位领导,征询他们的意见。
“我同意!”
“我看行!”
意见统一。他选择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站上去,环视一下窃窃私语的人群,大手向前一挥,山东口音在山间回响起来:“同志们,队伍里是共产党员的请举手!”
“刷——”人群中许多只手举起来。
“同志们,我们已经走过一半的路程,眼前的路段,遇到了危险,脚下是看不到底的深渊,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也没有别的选择,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也要闯过去,咱共产党员啥时叫困难吓倒过?没有,从来没有!危险的地方就该我们去,现在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是党员的,跟我站到坎下去,无论如何,今天搭浮桥的设备物资一定要按时到达百泉,虽然天寒地冻,困难重重,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尽快搭好浮桥,保证后续大批人员和物资进山,为尽快探明鼓家山矿藏提供有力保障,党员同志跟我来!”
“吴书记——”唐寅阻止他。
杨顺水说:“吴书记,您在上面指挥,让我们年轻人来吧!”
吴书记铁一般坚定的脸庞,没有理会他们,小心而又毅然地站到崖边最陡峭、最狭窄的坎下。见此情景,唐寅、杨顺水、党员、非党员二话不说,一个个扛着木板,纷纷抢着站到坎下,霎时间组成了一条长长的肩膀通路。
身边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深谷,稍有不慎就会坠落深渊粉身碎骨,江农生这个农村里长大的赤脚医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成为工人阶级一员时,竟然第一次就做出了这么勇敢伟大的壮举,站在坎下队伍中,他心中突然感到无比壮烈和激动。
“同志们,抓紧时间放心过吧!我们扛得住!”唐寅大声喊道。
一双双脚踏上来,从肩膀扛着的木板路上颤巍巍地踏过去,踏过去……一颗颗心希望自己此时身轻如燕,希望机器轻些、脚步轻些、再轻些。
我们挺得住!坎下的同志挺起胸、硬撑着脖子,咬着牙坚持着。
有人突然喊起低沉的号子:“一、二,嗨哟!一、二,嗨哟!”
天空再次飘起零零星星的雪花,时间似乎比平时漫长了许多,队伍在肩膀通路上似乎总也走不完、走不完,无穷无尽……不知过了多久,江农生脖子酸痛,肩膀麻木,身体几乎失去了知觉,瘦弱单薄的身体虚汗直冒,一再往下沉,他警告自己:江农生,你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哩,一定要挺住!挺住!
当最后一只脚踩过吴书记肩膀上的木板,吴崇光右脚下的冻土层猛地塌陷下去,还没来得及反应,失重的身体就直往崖下滑去。唐寅慌忙伸手去抓,却没有够着。
人们惊呆了!
“吴书记——”
“吴书记——”
撕心裂肺的呼喊声在山谷中回荡。
下滑中,吴崇光的手竭力想抓住岩石或者什么东西,可是急速滑下去的身体却什么也碰不到,眼看就要掉下悬崖的一刹那,无意中手却触摸到了崖边一棵枯树根,他死死抓住不放,悬空的身体垂在半空,两脚乱蹬,试图接近崖边的岩石,却怎么也够不着。
刹那间,崖上的人们心脏停止了跳动,不敢喘气,不再惊呼,唯恐一出气吴书记就会掉进深渊。
“快,拿条吊绳,我下去救吴书记!”杨顺水朝人群喊。
立刻有人甩过一根吊绳。人们呼地上前抓住绳子的一头。江农生见势,几把脱下羊皮大袄,扔在地上,来不及考虑,冲上前,推开杨顺水:“分队长,下崖我行咧。”不容分说,抓住吊绳,双脚利落地夹住绳子直滑下去,接近吴书记身边时,他把崖上垂下的另一条绑着大吊网的绳索抓起,网口张着,准确放到吴书记脚下位置,嘴里喊道:“吴书记,脚站直。”
精疲力尽的吴书记双腿蹬直,试探着站到吊网中,双手顺势抓住了绳索。
崖上的人见状,赶紧收绳,吊网徐徐上升,吴书记得救了!
“吴书记,小心!”崖上的人惊呼。
吴书记被缓缓拽上崖后,紧跟着,江农生也被人们用绳索连拉带拽拖到崖上。
吴书记躺在地上,双手、额头鲜血直流,眼睛无法睁开。身边,新任野外卫生员的梁爱华蹲在地上,手忙脚乱地为他伤口擦酒精消毒,不知是紧张还是不熟练,她的手哆嗦个不停。
江农生迟疑片刻,一向在人前有些腼腆的他,此时顾不上许多,鼓足勇气走过去,对梁爱华说:“你给我准备纱布。”他接过梁爱华手中的镊子,迅速用酒精为吴书记擦拭伤口、消毒、止血、撒消炎粉,然后用纱布熟练地包扎好手和头部,这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得心应手所做的一切,让一旁的人们瞠目结舌。
“嘿,这小伙子真行,看不出来还懂医呢!”
“嗯,动作熟练得像个大夫。”
“好像是新招工来的。”
包扎完毕,吴书记睁开眼睛,坐起身,亲切地看着眼前的小伙子:“小同志,叫啥名字?刚才下崖挺利索的。”
小伙子表情有些害羞,声音很低:“我叫江农生,以前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经常上山崖采草药。”
“噢,我说呢。今天还真多亏了你及时救我,不然我就要见马克思去了,我可要谢谢你这个救命恩人啊。”一句幽默的话把大家逗笑了。“新招工来的吧?分在卫生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