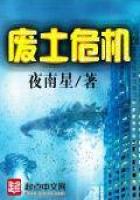十月中旬的草原已进入冬季,天空飘散着零星的小雪花。同学们已穿上了棉衣、棉裤,头上戴上了棉帽,女同学们还戴上了口罩。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上垛着小山般的麦捆,拖粒机马达高奏,响彻云霄,打破了宁静的夜晚。一个竖起的长杆上挂着一只煤气灯:打场开始了。
脱出粒的麦秆,两人一组用一个类似担架的东西把它抬走。望着天空稀疏的星星,和那不见少许的麦捆,杨涛发着他特有的牢骚,“怪哉,干了半天,只看见光秆儿多了,却不见麦捆少。”
“这是你的心理在起作用,如果把它们调换个个儿,你还会这么说的,快干吧。”江锋担起“担架”的一头,杨涛嘟囔着弯下腰抬起另一头。
“真是不懂,为什么非要三更半夜干?”
“趁这几天还没下大雪,把它脱出来,否则来了大雪就困难了,收而无获哪行。”
“同学们!”赵岩提高了嗓音,“今晚准备干到十二点,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虽然苦些累些,但和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比起来,这点苦和累算得了什么。我们就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才来牧区的,其中差别之一就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大家默不作声地干着。时间过得实在太慢了,白如玉终于忍无可忍,跑回宿舍把她房间的那个小闹钟拿来,摆放在麦捆的最高处,让人们随时都能看到它,以期带来时间缩短的安慰。小闹钟滴答的声音被马达的轰鸣淹没得无影无踪,时间按照它既定的步履分秒不差地走着,并不会因为人的愿望而加快步伐。大家忍耐着不去看表,可还是有人忍不住了,抬起头来望着那个希望的闹钟。
“天哪,才九点!我忍耐了半天,不去看它,满以为这会儿快收工了。”丁旭调侃着。
“还是思想问题,画画你觉得时间怎么样?快还是慢?”
“去你的,我今天拼了命了,白如玉把那个小闹钟拿走。”
“你不看不就完了,它也没贴在你的脸上,还是意志不坚定。”
“我们是干活,不是数钟点,活干不出来,还要加班的。”赵岩说……
麦秆越来越多了,白如玉和陈玲抬着一担光秆儿摇摇晃晃地踏进松软的垛,艰难地往上走着。突然白如玉脚底一滑倒在了上面,“如玉,如玉,快起来,你醒醒,醒醒……”陈玲使劲晃动着白如玉的手臂,“让我躺会儿……”白如玉睡着了。
“赵岩,白如玉躺在麦秆上睡着了。”
“这怎么行,快把她叫起来。”
“怎么叫她,她也不起来,她今天身体不太好。”
江锋走了过来说:“赵岩,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实在太累了。”
“如果坐下来,就很难再干下去了,而且天气这么冷,容易冻坏的。”
“那就回去,管它呢,我们尽力了。”
“不行,大雪一到就更困难了,必须尽快脱出来。”
“要不让女生回去吧?”
“不,我不回去。”张秀春说。
“对,我们不回去!”女生们异口同声。
“好!大家再咬咬牙,坚持到最后。”
“……同学们!还差五分钟。”有人报告着胜利的消息。
“哎呀,我的妈呀,可算到点了。”马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还差五分钟呢,快把它抬上去。”丁旭说。
“不行了,你自己抬吧。”
“请你再坚持最后五分钟,再坚持……”
“饶了我吧,丁军长。”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的连衣服也不脱,倒头便睡。连一向爱干净的女生,也免去了睡前的洗漱,她们实在太累了。
青年队经过整整半个月的突击,终于完成了脱粒任务。油灯幽暗的光亮将青年们的影子映在墙上,评工分会议正在进行着。江锋主持:“第一个王海军,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十分。”有人喊道。
“谁有别的意见?”
“没有,同意。”大家异口同声。
“好,一致通过。下一个是孔卫东。”
“十分。”“同意。”“丁旭?”“九分。”“同意。”“郑书怀?”“九分。”“同意。”“杨涛?”一阵沉默。
“该杨涛的,”还是一阵沉默。“好吧我来说,八分。”江锋说。
“什么?我八分,凭什么给我八分?”
“你病了三天,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没有,通过。”
“张秀春?”“九分。”“同意。”“黄雪燕?”“八分。”“同意。”“白如玉?”“九分。”
“她怎么九分?那天晚上,她在麦垛里睡觉。”有人不服地小声议论。
“那天她带病坚持到最后,谁还有意见?”江锋环顾着,会场静悄悄,“好,没有,通过。”
“最后一个,吴丽?”吴丽低着头,等待着判决。
“七分。”杨涛高喊着,“她出工不出力。”空气有些紧张起来。
“吴丽八分,”有人高喊道。大家回过头来望着他——躲在墙角里的丁旭。
“我同意,人的能力有大小,她已经尽力了,谁还有意见?没意见,通过,散会!”江锋连珠炮出语,一锤定音。
“我……我有意见,我才八分,和她一样,这不公平。我怎么和资产阶级小姐一样。”
“你……你……”吴丽咬着牙,泪水流了下来。
“她劳动态度端正,你呢,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吧。”
“不行,非给我说个道理,不然这件事没完。”杨涛愤愤地说。
“副队长,你俩多少分?”田小兵上前悄声问道。
“这个保密。”江锋合上工分簿走了。
宿舍里静悄悄的。
吴丽病了,发着烧,早晨陈玲给她打了针,服了药。今天她整整躺了一天,感觉轻松了一些。但她心里一阵阵的怅然,父母亲的影子在眼前晃动着。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家——这个令她蒙羞而又令她扯不断的东西困扰着她。她努力不去想,试图让自己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心绪始终安静不下来。丁旭的影子也不时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娇无力”“吴丽八分”交替在耳边响起。
“吴丽,好点了吗?”陈玲走了进来。
“好多了。”
“来,量一下体温。”
“谢谢,你每天干活,还要当大夫。”
“我算什么大夫。”陈玲笑着。
“31,还有些烧。一会儿吃完饭把药吃了,我再给你打一针。”
“嗯,刚收工就来看我,快去吃饭吧。”
“没事,好好休息,我走了。”陈玲走了出去。吴丽支起身子坐了起来,她拿起衣服。张秀春推开门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了进来。
“秀春,别,我自己可以……”
“别下地,你还没好利索。”
“谢谢你秀春,活这么忙,我却病了,还要你帮我打饭,真让我过意不去。”
“看你说的,吃吧。”张秀春把面条放在了炕桌。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吴丽,这是你家里给你的来信,给。”吴丽接过信放到了一边。
“你是不是一直没给家里写信?”吴丽点点头,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是不是想家了?”张秀春从铁丝上取下毛巾递给了她。
“没,没有。”
“怎么会不想呢?毕竟他们是你的父母,从小把你养大。”
“我要和他们断绝关系。”
“这怎么行,我才听说这事,今天赵岩让我找你谈谈,你应该给家里写信。毕竟血浓于水,毕竟你是他们的女儿。”
“不,我出来就是要摆脱他们,是他们害的我。”吴丽擦着泪水道。
“你知不知道,你父母亲很担心你,给赵岩来信询问你的情况。赵岩给你父母亲写了信,把你的情况告诉了她。”
“啊!”吴丽心里一热,睁大了眼睛看着张秀春。自从来到草原后,她一直没给家里去信,家里给她的来信她从来也不看,压在了箱子底。
“一个人不能选择她的出身,但可以选择她的道路。你今天走的道路是对的,希望你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与剥削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这才是你要做的。另外那次刘爱武说你,你别生她的气,她这个人心直口快,人很好,我早就批评她了。她也很后悔,哭了半天,只是现在还不好意思向你道歉。至于杨涛,你更不要在意他,你看大家还是肯定你的,给了你八分。”
“其实几分并不重要,我是怕……”
“我知道你是怕别人说你怕苦怕累。”吴丽点点头。
“不要有心理负担,希望你振作精神,病好后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谢谢你秀春……也请你替我谢谢赵岩。”
“不用谢,咱们这个集体应该互相帮助。以前我对你关心不够,思想工作没做好,还请你多多原谅。今后有什么事情及时向组织汇报,经常和同学谈谈心,性格开朗些,争取早日入团。好了,快吃饭吧。”张秀春站起身来,拿起桌子上的暖瓶晃了晃,“水不多了,我去打瓶开水。”
“你也快吃饭吧。”张秀春微笑着点了点头。
望着张秀春的背影吴丽心里既感激又不安。虽然她和赵岩很讲原则,让人有些生畏,甚至自己有些躲着他们。但今天她确实感到了他们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并没有歧视自己。她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锻炼,决不辜负他们对自己的帮助。吴丽撕开信封,一行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小丽……”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吴丽怀揣着充满父爱的信睡着了。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她又回到了儿时那些欢乐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