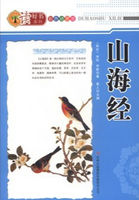医生尽量用自己会的越南语加上一大堆的手势告诉那几个孩子:“你们的朋友伤得很重,她需要血,需要你们给她输血!”终于,孩子们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但眼里却藏着一丝恐惧没有人吭声,没有人举手表示自己愿意献血!女医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一下子愣住了,为什么他们不肯献血来救自己的朋友呢?难道刚才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没有听懂吗忽然,一只小手慢慢地举了起来,但是刚刚举到一半却又放下了,好一会儿又举了起来,再也没有放下了医生很高兴,马上把那个小男孩带到临时的手术室,并让他躺在床上。
小男孩僵直着躺在床上,看着针管慢慢地插入自己细小的胳膊,看着自己的血液一点点地被抽走,眼泪不知不觉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医生紧张地问是不是针管弄疼了他,他摇了摇头。但是眼泪还是没有止住。医生开始有一点慌了,因为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肯定弄错了,但是到底在哪里呢?针管是不可能弄伤这个孩子的呀关键时候,一个越南的护士赶到了这个孤儿院。医生把情况告诉了越南护士。越南护士忙低下身子,和床上的孩子交谈了一下,不久后,孩子竟然破涕为笑。
原来,那些孩子都误解了女医生的话,以为她要抽光一个人的血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想到不久以后就要死了,所以小男孩才哭了出来!医生终于明白为什么刚才没有人自愿出来献血了“既然以为献过血之后就要死了,为什么他还自愿出来献血呢?”医生问越南护士。
于是越南护士用越南语问了一下小男孩,小男孩回答得很快,不假思索就回答了。回答很简单,只有几个字,但却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他说:“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回答很简单,只有几个字,但却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在英雄的连队服役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老马所在的特务班被敌军的一个连包围在一片密林里。他们仗着有利的地势,跟敌人展开了激战。但是,敌我的兵力太悬殊。后来,只剩下老马和班长两人了。
班长的左肩上中了一枪,老马替班长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班长说:“老马,咱俩都生还的可能已经没有了,我掩护,你撤走。”“不!不管怎么样,咱俩都在一起。”老马是副班长,平时跟班长情同手足,绝不可能扔下负伤的班长自己撤走。
“我是班长,你得听命令!”
“不!”老马含着眼泪坚定地摇头。
班长沉默了片刻,猛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叠被鲜血染红的纸对老马说:“老马,这是一封对我军很重要的情报,我身上有伤,撤不出去了,你要亲手交给首长。”“班长,不!”
“老马,不能再犹豫了!”班长的声音和握着那纸情报的手都在颤抖着。
老马别无选择地接过情报,小心地藏在贴身的衣服里。
老马成功地撤出了敌军的包围。这得益于班长的掩护和有利的地势。不幸的是,老马的腿上中了一枪,只能一点一点地向前爬行了。
那密林里的枪声停了,班长的情况可想而知。
老马当时很累,真想停下来歇歇。可是想到自己身上带着重要的情报,想到班长及全班的战士,他的心里像燃烧着一团火,爬行的速度快了起来。
终于看到我军的哨兵了,不知是太疲倦了还是失血过多,老马失去了知觉。
等醒来时老马已经躺在临时病房里了。
“我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交给首长。”他吃力地对旁边的人说。
望着来到老马身边的首长,老马掏出那份情报说:“这是班长给您的重要情报,我们全班都……”老马说不下去了。
首长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那染着班长鲜血的情报,默默地看了良久,大滴的泪珠落在那纸被鲜血染红的情报上。
“首长,这情报真的很重要吗?”老马低声问。
“很重要,很重要!”首长深深地点头。
后来,老马才知道,那其实不是什么情报,只是几张白纸。
首长说:“这比任何情报都重要,它体现了班长以及全班无私的、忘我的战友情谊……”
尘封的友谊
年冬,波恩市的街头,两个月前这里还到处悬挂着纳粹党旗,人们见面都习惯地举起右手高呼着元首的名字。而现在,枪声已不远了,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恐惧之中。
奎诺,作为一名小小的士官,根本没有对战争的知情权。他很不满部队安排他参加突袭波恩,然而,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巴黎调来的法国军官希尔顿,他对美国人的敌视与对士兵的暴戾几乎人尽皆知。接下来两个星期的集训,简直是一声噩梦,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奎诺在这里认识了托尼——一个健硕的黑人士兵,由于惺惺相惜,这对难兄难弟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使波恩俨然成为一座无险可守的空城,占领波恩,也将比较容易。而突袭队的任务除了打开波恩的大门外,还必须攻下一个位于市郊的陆军军官学校。而希尔顿的要求更加残忍,他要求每个突袭队员都必须缴获一个铁十字勋章——每个德国军官胸前佩带的标志。否则将被处以鞭刑,也就是说突袭队员们要为了那该死的铁十字而浴血奋战。
突袭开始了,法西斯的机枪在不远处叫嚣着——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在盟军战机的掩护下,突袭队顺利地攻入了波恩。然而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全是因为那枚铁十字。在陆军学院,战斗方式已经转变成了巷战,两小时的激烈交火,德军的军官们渐渐体力不支,无法继续抵挡突袭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举起了代表投降的白旗。突袭队攻占了学院之后迅速地搜出每个军官身上的铁十字。手里攥着铁十字的奎诺来到学院的花园,抓了一把泥土装进了一个铁盒,那是他的一种特殊爱好,收集土壤。他的行囊中有挪威的、捷克的、巴黎的,还有带血的诺曼底沙子。
他正沉浸在悠悠的回忆中,托尼的呼唤使他回到了现实,托尼神秘地笑了笑:“伙计,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他们的休息时间少得可怜,奎诺跟着托尼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从豪华的装饰来看,这个办公室的主人至少是一位少校。满身泥土和硝黄气息的奎诺惊奇地发现了淋浴设备,他边嘲笑着托尼,边放下枪支和存放着铁十字的行囊,走进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当他出来时,托尼告诉他说希尔顿要来了,他要了解伤亡人数,当然,还要检查每个士兵手中的铁十字。他马上穿好衣服背上枪支、行囊,与托尼下楼去了。
大厅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手里的铁十字,奎诺也自然伸手去掏铁十字,然而囊中除了土壤外竞无别物。奎诺陷入了希尔顿制造的恐怖之中,他没想到会有人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背叛战友。奎诺首先怀疑到托尼,并向其他战友讲了此事,当下大家断定是托尼所为。
所有士兵此时看托尼的眼光已不是战友的亲昵,而只是对盗窃者的鄙夷与敌视。他们高叫着、推搡着托尼,而此时托尼的眼中并不是愤怒,而是恐惧、慌张,甚至是祈求,他颤颤地走到奎诺的面前,满眼含着泪花地问道:“伙计,你也认为是我偷的吗?”此时的奎诺狐疑代替了理智,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托尼掏出兜里的铁十字递给了奎诺。
当那只黑色的手触到白色的手时,托尼眼中的泪水终于决堤,他高声地朝天花板叫到:“上帝啊,你的慈悲为什么照不到我?”
“因为你他妈是个黑人!”从那蹩脚的发音中,人人都听得出来是希尔顿来了。他腆着大肚子,浑:身酒气,随之,一个沉沉的巴掌甩在托尼的脸上。而后检查铁十字,不难想到,只有托尼没有他要的那东西。
再之后,盟军营地的操场上,托尼整整挨了30鞭。
两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浑身如鳞的鞭伤基本痊愈,但在这两个星期里,无人问津他的伤情,没有人关心他,奎诺也不例外。
又是一个星期六,奎诺负责看守军火库,他在黄昏的灯光下昏昏欲睡,忽然,一声巨响,接着他被砸晕了。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榻上。战友告诉他,那天是托尼的巡查哨,纳粹残余分子企图炸毁联军的军火库,托尼知道库中的人是奎诺,他用身体抱住了炸药,减小了爆炸力,使军火毫发无伤,托尼自己却被炸得四分五裂。然而,他是可以逃开的。
年过去了,奎诺生活在幸福的晚年之中,对于托尼的死,他觉得那是对愧疚的一种弥补。直到有一天,他平静的生活破碎了,因为他的曾孙,在一个盖子上写有波恩的铁盒中,发现了一枚写着“纳粹”的铁十字。
年近九旬的奎诺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那眼泪,是因为悲哀而痛苦,不是为自己年轻时的愚鲁,而是为托尼年轻的生命:是因富有而喜悦,不是因为那锈迹斑斑的铁十字,而是为了那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眼泪,是因为悲哀而痛苦,不是为自己年轻时的愚鲁,而是为托尼年轻的生命:是因富有而喜悦,不是因为那锈迹斑斑的铁十字,而是为了那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
生命的礼让
他们素不相识,却有着出奇相似的相貌;他们因为同样的疾病走进同一间病房;他们都已经找到了可配型的骨髓,却因为筹不到钱而无法手术;他们为了保留其中一人的生命,唱响了一曲生命礼让的赞歌。
“我们虽同样有着新婚妻子,同样有着年迈的父母,我们虽同样配上型找到了可供移植的供者;我们虽同样为昂贵的移植费绞尽脑汁……但你还有一个出生刚刚几个月的活泼可爱的孩子,还有一大笔的债务等待着你去偿还……我决定在我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帮帮你,将我剩下的3.5万元人民币无偿捐赠给你。”这是欧阳志成转赠生命的悲壮绝笔。他将这绝笔和3.5万元人民币留给病友彭敦辉,然后消失了。
湖南隆回县养古坳乡中团中学语文教师欧阳志成被确诊为白血病时,他只有27岁,他的爱人只有21岁,他们结婚仅仅9个月。
矫弱的妻子彭丽争分夺秒地向亲朋好友、乡教育办、学校筹款,但也只筹得不到万元。为了尽快筹到20万元实施移植手术,他们抱着求助牌,手捧玫瑰花,面对邵阳师院熙熙攘攘的人群跪倒在地。整个隆回县被震动了,在全县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很快筹措了近20万元。但一年多的化疗和寻找配型已经用去了12万元。配型找到了,他们却因为没钱而无法手术。
同一个病房的病友彭敦辉,也患有白血病,也找到了配型却因为筹不到钱而无法手术。这两个酷似双胞胎、同病相怜的病友,从此相互照料,相互鼓舞,与病魔作斗争。望着一筹莫展的欧阳,彭敦辉曾安慰他说,“说不定我厂子新上的项目很快就能赚大钱,到时候,我借钱给你。”彭敦辉的生意失败了,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看着此前从未向病魔低过头的病友颓废地倒在病床上,望着他活泼可爱的小孩子,欧阳的心里一阵抽搐。那一刻,他作出了一个思量多日的惊人决定:将善款转赠给坚强而善良的好兄弟彭敦辉!自己少活一段,可能成全他的一生。
作了此决定后,欧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医院负责人——遗体捐赠给医院作医学解剖用,一封写给病友彭敦辉——然后他回到了隆回老家。
接下来的日子,远在长沙的彭敦辉和妻子开始竭尽所能寻找他的那位好病友、好兄弟。他们试图通过隆回114查询欧阳的住宅电话,但一无所获;他们查到欧阳所在学校的电话,可因为暑假总是没人接听……两位护士感动地出主意:“打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呼吁大家寻找他!”
“转赠生命”的动人故事在电视台播出后,立即在省内掀起一股动人浪潮:一些长沙市民自费印刷寻人启事;虽然还没有找到欧阳,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通过特别账户为欧阳捐款。
终于,2005年8月,在热心市民的陪同下,欧阳终于回到了医院。生死之交的兄弟俩百感交集,相拥而泣……现在,在社会的帮助下,两位患难兄弟已经远离病魔,踏上了绚丽人生的旅程。
将善款转赠给坚强而善良的好兄弟彭敦辉!自己少活一段,可能成全他的一生。暖意那天坐进一辆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广播,是一个不新鲜的故事一某日某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逃逸。撇下一个叫陆小六的人在血泊中呻吟;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把陆小六送到了医院,值班大夫薛达在未收取陆小六住院押金的情况下为他实施了手术……“这年头,做点儿分内的事也能混个名人当当。医生嘛,可不就得救死扶伤,不收押金救条命也值得上喇叭吹!”司机愤愤不平地说。
电波继续传送:陆小六脱离危险后居然不辞而别,身后,欠下了上万元的医药费……“这个不仗义的东西。唉,这年头,啥样的人都有。有些人呢,就是不配念那一撇一捺——快听,要通缉那个陆小六呢!”
女播音员的声音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男声:陆小六,你好,我是你的医生薛达。你现在在哪里?腿上的伤口没有感染吧?你走得那么匆忙,连声招呼都没有打,可把我们急坏了。陆小六,我今天来到交通台的直播间,是想通过广播的方式尽快找到你。我不是向你讨要医药费的,我只是想对你说,你的腿骨上还留有两个金属夹,如果不尽快取出,你可能会面临截肢的危险……陆小六,记着,你的医生薛达在博爱医院等你。
侧脸看看那位饶舌的司机,只见他的嘴巴紧紧抿住,脸上写满感动。拐弯了,他很抒情地按了三声喇叭……总有一些小人,他们很自信,在很多事情上总是以经验和方式猜测别人。而这样的人总以为社会上只存在坏人;所以千万别和这样的去计较,不然他会把你拉到他同等的位置上,然后利用他的经验和方法击败你。在汽车里司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半个小时他的决策可以发生很多转变。一会儿骂医生想出名,一会儿骂陆小六没有道德……然而当司机听见医生是想救陆小六的病时,司机终于闭上了嘴巴。那一刻,我相信司机的内心也在反复进行跳跃,在他看来没有坏人似乎是不正确的。可以看到司机的脸上写满感动,并很抒情地按了三声喇叭。所以,像司机这一部分人,他们并不是对善良失去信心,只是没到“感动”处。如果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司机”。爱心常有,掌声常驻。珍爱在我遇见班奇太太之前,护理工作的真正意义并非我原来想象的那么一回事。”护士”两字虽是我的崇高称号,谁知得来的却是三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替病人洗澡,整理床铺,照顾大小便。
我带上全套用具进去,护理我的第一个病人——班奇太太。
班奇太太是个瘦小的老太太,她有一头白发,全身皮肤像熟透的南瓜。”你来干什么?”她问。
“我是来替你洗澡的。”我生硬地回答。
“那么,请你马上走,我今天不想洗澡。”使我吃惊的是,她眼里涌出大颗泪珠,沿着面颊滚滚流下。我不理会这些,强行给她洗了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