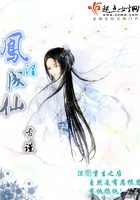在小鬼面前,我像一块玻璃般透明,类似的经历,类似的心境,让我产生难得的知己之感。以为小鬼会有同感,却如面对一块磨砂玻璃,透明中隐含着朦胧的图案,我无法了然。
像许多待字闺中的女孩子一样,小鬼以为爱情是两颗心永恒的契合;像许多家庭不完满的孩子一样,小鬼对婚姻的要求又非常之低,便形成她独特而又矛盾的爱情观。现在想来,在感情方面,她是有些轻视我的。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痴心女子,爱一个人并崇拜这个人,如一把琴,欢乐与悲伤都随他手指的拨动。小鬼便对我说,你应该学会独立。我说我知道。可我不知道能不能。当一个男人爱你,甚至为你填补了童年时的缺憾,把手掌合扰成一个摇篮里,已经完全与世隔绝了。
等待因无期而归于昼夜交替的轮回。便想起《听我吹箫》的约定,便接着写:箫声咽,吹箫的时候总是想到雨,滴滴点点,打湿心情,打湿箫声。下雨的时候总是想吹箫,长箫经雨润湿,声音格外清脆、格外青翠,似有青枝绿叶由箫孔钻出,转瞬已是遮天蔽日,心中郁郁葱葱一片幽篁。于是幽渺的,想起江南、想起游子,想起一个关于前生来世的传说……那时流行戴耳针,耳针形状千奇百怪:蜻蜓、小鱼、拖鞋、剪刀……比米粒儿大不了多少,精巧可爱。小鬼说:我们也去穿耳朵吧。我摇摇头不敢。那么一把“枪”对着我,我会觉得它不仅是对着我的耳垂儿。几天后小鬼再来,耳朵已经穿好了,缀着一对亮晶晶的耳针,形状居然是两个半块的骰子。想像着一对耳针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骰子,会摇出多大的点数来?一种莫名的宿命之感盈在心中久久不散。待到等待的日子回顾当时的感觉,我才知道,其实一切早已注定。那个约定,也只有我自己去完成:箫无言。一声悠悠轻叹,清波一转间惨淡的一笑,泪落无声。箫的心事无法破译。箫声起处,音符飘飞如雪,清冷致远,笼罩住一颗心,与世隔绝。箫在尘世没有知音,凡尘寻常的一瞥箫已哑然,叹不是给人听,泪不是给人看。只有那一笑,楚楚淡淡,无人破译,无需破译,无法破译……这样写时,丝丝缕缕的怅惘将心网住,那些彻夜长谈的日子,相对感泣的日子,雨中散步的日子,以及吹箫的日子,一一重现。人说君子长相伴,小人三日好。这么“君子”的一个过程,怎么会有这么“小人”的结局我不是俞伯牙,小鬼也不是钟子期,我也便无需砍断长箫谢知音。可也许久不曾吹箫了,因为拿起箫就会想起小鬼,看见她很珍重地双手把箫捧给我,说:再给我吹一曲吧。我想不出还有谁,能这样地陪我坐在雨中,听我吹一些低婉的曲子,或者只是随着心情随意吹出的音符。于是在等待中我只能说:箫的知音隐在月下,等着箫声一起便如约前来有时,只要你鼓足勇气跨出一步,那一切都会变得与你预先想象的完全两样。
像蝴蝶一样出生我出生在五月。我的一个朋友说,五月,是最容易出品人的。我一算,那么我的父母制造我的时候,应该是在八九月份,真的是很容易受孕的月份,天气很热,六十年代,又没有别的什么娱乐,只能够去数星星,星星数腻了,才去制造人。越穷的年代,就越容易出品人。我的上面,有哥哥,三个哥哥,还有姐姐。而我怀我的儿子,是在春天,蝴蝶就要出生的月份,也是容易受孕的月份。我记得我的一个写诗的朋友这样记述五月:五月,蝴蝶纷纷出生……很浪漫,什么东西从诗人嘴里出来,就变得很浪漫很温情,是会让疼痛变成一种流汁慢慢地流掉。
生孩子,那真是很疼痛。我生我儿子时,整整疼了三天。儿子还在我肚子里,我当时已经体重一百五十多斤了,这当然是包括我孩子的重量,我问我的一个小姐妹,她是一个工人,并且刚刚生完孩子。她看看我的肚了,她说:不疼,跟下只鸡蛋一样。我眼前立马就浮现出一只母鸡,它的羽毛很母性,它在抱窝,目光很专注。鸡每天下一只蛋,还能那么幸福地“咯咯”叫着,那真不会很疼的了。我算是放了一颗心,去医院的时候,我笑咪咪的,我是笑咪咪走着去的,我要多运动,以增加我的肺活量。我去医院的时候,肚子还没有疼,可已经过了预产期。医生给我拍完B超,就要给我做催产,说不能再等了,羊水太少,再不生会变成石胎。石胎?我不能够让自己怀了十个月的孩子变成为石胎。我说,催吧,生吧!可真一生,妈呀!我嚷着,医生啊,你还是给我剖开吧,我怕孩子在我的肚子里会没力气往外钻的,我不能够让他多受罪的,而羊水又没有了。女医生用手压着我的肚子:“不用怕,努把力,你的孩子不大,不会超过六斤。”事实上,我的儿子出来时有七斤多。医生就笑,孩子很大,我摸着就知道了,可能这样跟你说吗?我的工人小姐妹来看我的儿子,也咯咯笑着说:鸡下蛋也是疼的,不疼就不“咯咯”叫了。
不过,我算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制造了一个很不错的帅小伙了,眉眼很正,哭声很大,是带着全婴儿房的婴儿猛猛地哭,也很能喝牛奶,他喝的牛奶抵得上别的婴儿喝的两三倍,像是因为他的出品太不容易,他比别人要多努力了那么久,才可以出来见太阳。
生了孩子,我才觉得母亲的不容易,并不是我想像得那么容易,是因为数星星数腻了,才想起制造我。而现在的女人要怀个孩子就更不得了,像入了某个教替自己定了很多规矩。要算准了时间怀,怀上了,原来是看电视必须看到“再见”才再见,现在是连瞄一眼也不瞄了;不喝酒;不闻烟;感冒了不吃西药;明明不爱吃苹果,可听医生说,苹果维生素多,就不停地买苹果,生着吃煮着吃煎着吃。
我是直想向妈妈说一声,妈妈,你辛苦了。可妈妈已经在九泉之下了。
最近,一个朋友怀孕了,问我生孩子疼不疼。我看看她鼓得高高的肚子。善良地告诉她:“不疼,像蝴蝶出生一样。”出品完孩子,我看起来像个诗人了,是可以让疼痛变成一种流汁慢慢流掉,流成幸福。
毫无理性,毫无道理地沉溺于享乐的人,他的生活毫无意义。牵手那年他和她都十八岁。当他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找到她时,她正在夏日的玉米地里拨草。
他说:我们考上大学了。她停下手中的锄头,扭头睁圆沾有汗珠的大眼。惊喜地说:晤,真好!咱俩这是一所学校吗?她的笑在散发着青玉米味的夕阳里灿烂着。他的心一动,陶醉在这孩子般纯真的笑影里。
他拉着她的手回家,路上她说:牵着你的手真好!他笑了。更紧地握住了她硬茧的湿手。
但她没同他一块上大学。他父亲除了赌钱一无所长。多病的母亲除了把钱买药外就是在床上抹泪。长女的她无可争议地挑起了家庭沉重的担子。——她有三个上学的弟妹。
大学一年级时,他省吃俭用。买了一件很流行的女式手套送她。也在那年一个枯叶落地的初冬,她离开家乡到城市去打工。
好久收不到她温馨关切的信了。但他铭记了摇曳的玉米叶下的笑脸和一双依附他的小手,还有一句:牵你的手,真好大学三年级寒假,他徘徊在她冷清简隔的房前,冷的空气中传来男人的怒骂和一两声病人的绝望哭叫。他酸楚地想:这样的家,她还会回来吗有人说她月月寄给家的钱是她在外当“小姐”挣的还傍了大款。后来又有人说她被大款甩了,生死不明。
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谣言,但从此家人不曾有过她的一封信和汇款单。
大学毕业后好几年,他在父母的催促下有了自己的家。而她像他儿时梦中的仙子一样成为他永远的追忆。
当他过着全世界工人为食奔波的平凡生活时,依然没忘记玉米地里憧憬的小女孩。
多年后的又一个夏季。他在农村的妹妹送来一张印有京城邮戳却没有详细地址的包裹单。
打开针脚密密的包:一幅手工织的男手套让他想起他大学一年级时流行的那种样式。
祝福你——在风雨里孤独流浪的女孩。他闭上眼睛,默默地真诚地想。
要是你不能立刻找到我,你仍然应保持勇气,在一处错过了,还可到别处去寻觅,我总是在某处地方停留着等你。
流连的钟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的这首诗给寒山寺注入了灵性,《涛声依旧》这首娓娓动情的歌,让多少游客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说不清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那时钟声的召唤,也许是想揭开那尘封的日子,也许想看看“久违了的那张笑脸”。旧地重游的“老公”陪着我,绕过逶迤的黄墙,来到这个林木葱郁的所在。
他好像拿着“一张旧船票”在给我做导游,一路上讲着唐代著名诗僧寒山和拾得在此院当住持而得名的典故。寻其正门,伫足寺外,庙外人头攒动,庙内香烟缭绕,传来缕缕幽香;磬声,钟声夹杂着诵经声习习传来,真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庙。我等俗人到此一游,是朝圣,是祈祷,是企盼,是还愿,还是什么都不是……我这七情六欲甚浓的俗人毕竟与这寺庙缘份太少。心里正想着,门口的一位清眉清目,通身透着书卷气的小僧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问他:“枫桥在哪?”他显然看出我们错把眼前的桥当做“枫桥”了,他便颇有兴致主动地介绍说:“江枫渔火对愁眠中的‘江’是指‘江村桥’,就是这座桥。‘枫’才是指枫桥。现在在这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倒觉得他很有学问,也很可亲。好奇心的驱使,想探出其隐秘,于是在较为放松的交谈中得知他是神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显然是科班。我想本科僧人只安排他作一个守门人,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赏他个住持当当也不为过,由他来传经布道,肯定能将现代文明与古代传统的宗教文化融为一体。这样想来很为他不平,但是怎奈佛门圣地也摆脱不了世俗的论资排辈的陈规陋习,也许他毕竟还太嫩了点。
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出家人,我们作为红尘中人是无法真正辨识其高低的,但本科学历和侃侃而谈的口才,足以客观地证明他的佛学造诣了。我几次出口想打探他出家的隐私,但他那一付天机不可泄露的神情让我打住了。尊重别人的隐私权是作人起码的道德,更何况这是出家人最忌讳的话题,我只好作天马行空般的猜测。他究竟是遇到了怎样的挫折和不幸,才万念俱灰毅然离开尘世,抖掉凡心;他缘何舍弃了美妙的青春遁入了空门来伴这晨钟幕鼓,青灯黄卷。漫漫人生,孤寂长夜,怎是一个“熬”字了得。看来,每个僧人都是一个难解的谜,一部难读的经。
看他那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双眼微闭,双手合十作陶醉状;看他那白里透红的充满平和平静的脸,我读懂了他心中的满足,我破译了他心灵上的阳光。他在这属于他和他的同志者的独特的天地里,寻觅到了一种有别于滚滚红尘中人的生活。他用自己生命的灵光品味有别于我们的人生,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超越呢!这何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追求和憧憬呢!我明白了他这对佛对宗教的虔诚也是一种别样的奉献。突然,在我的心中树立起对他的崇拜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