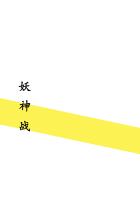“仙人赠头玉,喜上交眉语,谁欲相携去。朱丝霜雪总白头,朝雾散来尽是空。枉为世人误心事,奈何昙华不由己。桃花隔来丝竹喑,声声子规**序……”
此曲实在是妙。只是没能先来征问吴姬情愿与否,便提此要求,庄某无意冒犯。万勿怪罪才好。“
“正是仲冬时,在下正感无趣,几日前听闻姑娘有意请教,才重执笔墨,以解无聊之身,况且仅此一节,何来冒犯之说?姑娘莫要言重了。”
“多谢体谅,雪天多寒气,吴姬若不嫌弃,不如在寒舍小酌一杯暖暖身子,晚些回去?”
“也好,劳烦姑娘了。”
……
天晚了,乡间麦地行着一个人,白衣华发,腰间佩剑,面色清冷,她不停向西而行,这些天,她皆是借住在不同的农户家,离开时再将他们一一杀死,只是防范,只是为了躲避,她眉头忽然紧皱,声音若有若无地发出,对不起。
正停下修整时,她又听见麦草间有杂声,走近一看,是两个布衣,她握剑,刀剑起伏,草草两条人命,她不再停留,逃也似的转头离开,终于还是再次停下,她死死捂住胸口,一手从胸衣间取出一页竹简,望了许久,她又飞快放了回去,继续踱步。
一夜晚后,天边露了白,那白衣女子隐入了另一片林子,她在林地中间顿下步子,四处瞧一瞧,迈向了更深处,果然有一座墓园,正立在显眼处,也未有卫士看守,她将竹简取出,一手在地上挖了个小坑,将竹简小心放入,她凝重望着那一节字:宋国有士,乃吾儿也,有幸重游,未能寻去,此生只唯一遗憾,愿详其样貌,足矣。
将竹简埋好,她手握腰间佩剑,又压了平泥土,才向林外走去……
“姑娘,吴姬正在咱们院中赏花呢,瞧着天儿也凉,姑娘去见吗?”说话的女子是侍奉打扮,未踏入门槛便向里嚷嚷。
庄孟正居主厅,肩上披着一件御寒的狐袄,容貌平平,发间一样缃色梳篦,梳的是垂云鬓,手里端着一杯暖茶,闻声道,“自然要见,叫人给备好茶。我亲自去请。”
寒天大雪,有两个女子立在一片野芍药间,一个身着白衣,裹着白袄,一双似水的桃花目,细弯眉,丹红唇,不添发饰,长发只简单疏了个样式,却貌似神仙,一个弯腰低头,跟在后头,说是个侍奉,又不着发饰,及腰长发就那样散在身后,眉目干净,也不知是否是冻着了,脸色也白的难看,腰间竟还佩着一柄长剑。二人说说笑笑,中间听见有人在唤,回头看见一位红衣,她笑应了一声……
“我也久日不见吴姬了,今日到访真是稀罕,这天气虽说是转暖了,到底飘了几场大雪,还是凉的。”庄孟坐在右侧,时有时无的喝茶,目光望去,对面的女子愣了下神,而更是不后缓过,细声道:“常惦记着你这的野物,虽是冬天,还是想来看看,末了,不准还能赶上哪出曲子。”
庄孟压了压眉头,又笑弯了眼,嘴角扯了一抹笑,她道,“那真是抱歉,打扰吴姬看这野物,又赶巧今天没曲,来也是来了,再讨语些时罢。”
纱糊窗外便是寒风似箭,无落白,却冷得出奇,房檐上有两只鸽子,不时抖抖翅身,便落下散散几片羽毛,叫人看着还真是似雪一般。
“姑娘今用了胭脂?”“是,今日天冷”
“呵,说起胭脂,前几****才让素素给添了几置,色泽亮度,都是极好,人家卖的说是取几枝桃花,浸在水中,取火加热,再将捣烂,埋在地下几月便可,真是有趣,于是我今日便自个儿做了几样,取的正是这野物,可今天看你用的,却比我这儿的任何一样都好上不少呢。”
……
夜晚,忽起了寒风夹雪,且愈下愈烈,自然的,有个白衣女子无家可归,唇冻的发紫,手越发用力地握紧了剑柄,却无奈体力不支,倒在了一庄宅子前。醒时面前是个姑娘,年纪与自己相妨,欲要起身,那姑娘背对着她道了句,“此后跟着我吧。”
她无话。
她坚持不肯扔掉腰间佩剑,便一直带着,自那天起,她知道了这人的身份,名作吴姬,是个官人捡来的女儿,却没有一点的娇气,常是一副冷静。尤爱到邻家一庄戏园赏花,真是个奇怪的爱好。开始她一心想着如何杀死这人,后又一啄磨,跟着这个主子,不仅不用操心吃宿,而且方便找人。便除了这个动机。
她生来怕冷,而吴姬喜欢雪日出门,又担心着大冷的天有些乞讨人冻极了会扑向自己,以前也碰到过,有关安危,刚巧就白得了个带刀的,便一直叫跟着了。
这胭脂是母亲教的方法,她自己做的,原来做好便没用过,觉得好歹也是个拿的出手的物,送给了吴姬,哪曾想她隔天便用上了,自此还总喜欢用上,如此也算是挺好。
“吴姬身边这位我竟不面熟,是个新人?”“她唤相月,前日才来,你自然不熟悉。”
“看着倒不娇气,身架也挺高,难道习过武。”庄孟看了她一眼,仅仅一眼,后又转向吴姬,换上笑脸,不知是在问谁。
“姑娘真是好眼神,我是习过武,但是得主子救济才谋得一命,所以才跟着,尽微薄之力,保护主子罢了。”她也不瞧面前之人,尽管低着头,因为她娘便是个奴婢,自己到底也懂这些规矩的。
“听闻你在凭物寻母,寻到了吗?”庄孟纤手一顿,“我只是不知,凭着一根木簪能寻到吗?毕竟这东西太寻常,实在有些不太可能。”
“还未寻到,说不准早已归天了。有时真是觉得可笑,分明被她丢弃,差些冻死,还想着找她,”她不由拉紧了裹在脖颈上的毛披,转过头,“你也许好奇我为何收留你,并非是要你保护,只是,看你比那时的我坚强许多,而且,我总瞧你面善,不知为何,总觉得见过你……”她声音很小却明透,似要渗入人心,看着庄孟的侧身,又转过头,却看向了门前一架琵琶
她自顾自走上去,手指略略划了几下,只觉生疏,仅仅几下,又收回手,“打扰了,告辞。”她顺势转身离开,身后相月只得跑了几步,出了院门,到底相月开口“姑娘所说的木簪,是为何类。”对方未有回应,她又补充一句,“姑娘是会弹琵琶曲吧?”仍未回应,却点了下头。“那么,姑娘是否曾习过‘子规’此曲。”她顿住了,雪向她散来,她也似浑然不觉,“你是谁。”
“我唯一骗了姑娘的一点,是我并非宋国寻常百姓,其他,我说的句句属实,姑娘若问我是谁,在下委实名唤相月。”她死死抓了抓衣裳,声音几乎没有起伏,也许有,但也被那倏忽落下的檐上雪掩埋了。
吴姬只是斜了头,面容平静,“你可知道,这曲子无人知晓,甚至我也不过学习数下,而你又为何知道我习过此曲。”问过此话,她又说了一句,“你,怕是与我亲娘,有关系吧。”
“曲子跟随姑娘至今,可不比木簪好认许多,我不过试试姑娘,未曾想过,原以为是大海里寻一粒沙子,可居然如此巧合,竟不偏不倚,正是姑娘。”她欢快了些,眉头才算展平,随即又跪地,双手捧着一封竹筒,“公主。”
面前之人闻声转身,接过竹筒,上面廖廖几句:琵琶一曲,唤作子规,木簪一支,愿保平安。她收起竹筒,“你口中的我的母亲,这封竹信的主人,是谁?还有,你为何叫我公主,我那位母亲,究竟是何许人也。”她不解,就立在相月身前。
“宋国公主,卫国夫人,南子。”她声音依然平静,却起了身,正对上对方诧异眼神,“不过你猜对了,她死了,许多年前,我也未曾见过她,我母亲是她的侍从,这一件件竹信,才得以传入我手。”她转身,什么也不再说,向前面缓缓挪步,手中又捏紧了剑。
走了半晌,她才发觉身后那人一直紧随,她扭头,略略一笑,“我原本也不喜她,我总以为,一个舍父弃女的女子,是无比可恶,但是我到底无法恨她,就如母亲所说,她不过,”手指指着面前一块石碑,“不过是个可怜的女人罢了。”
吴姬只是一双桃花眼盯着那块无名石碑,二人伫立许多,雪仍未停,只是小了些许,最终的最终,我只听见吴姬道了一句“可以的话,我能否知道,南子,是个怎样的女子,就当是一个女儿,想了解她的母亲。”
我是庄孟,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和她的侍从在我这里讲述的,整整三天,万分仔细,我听了只当故事,但是,我绝无法将它想成是一个女子,真实发生过的一切,真的,很不真实,真的,叫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