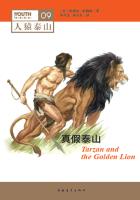屋顶垂下的灯泡罩在锥形的塑料筒里。夏克明和曹剑两个脑袋投下黑黑的阴影,在狼藉的小餐桌上晃来晃去,间或又落到地面上。
“不要上网钓女人,你偏不听。”曹剑的眼珠子被酒精烧得又红又亮,伸手按住盘中的稻香村熏鸡,又狠狠地撕下最后一个鸡腿。吐出舌头,舔舔油亮的鸡皮,嘴里吧唧两声,咽下口水。
“网络不是好东西,再过二三十年,危害大了去了。那是地球公开的档案馆。彼此间,没遮没挡,一目了然。”曹剑嘴里嚼着肉,含混不清地说:“男女生交朋友,双方家长上网互相搜索,我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女生老妈当年是破鞋,风骚**百看不厌;男生老爸以权谋私搞破鞋,一桩桩、一件件,引人入胜……”
曹剑端起酒盅,被自己逗得浑身乱颤,眼睛里水汪汪的,左耳朵上的小肉瘤泛出鲜红的血色。
夏克明一言不语。此时,他突然觉着右侧的上槽牙被姚珍爱的老公打松了。小心翼翼地用舌尖轻轻顶顶,真的有点活动,心中骤然一紧。再顶顶左边的槽牙,似乎也有点松动,再顶顶右边的,好像又不动了。
曹剑举杯示意,夏克明没搭理他,夹起一粒油炸花生放到嘴里,右槽牙毫不费力地将颗粒碾成花生碎。紧接着被一杯白酒送入肚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曹剑依旧坐在对面喋喋不休。
“你也够的,让一小矮人给揍成烂酸梨了,要是我,把胳膊伸直了,让丫跳,跳起来都够不着。不过这小矮人倒真是位壮士,把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当年上中学,要有人这么臭扁你一顿,立马在东城美术馆一带就玩响了。”
“你丫喝高了吧?”夏克明将酒盅重重地蹾在桌上,用手按按右眼眶上的纱布包。昨晚上绽开的皮肉被五针缝合在一起,从分裂到闭合时时感到袭来的锥痛和刺刺的痒。
“我喝点儿话多,但都是实话,你好色,胎里带的。小学我就看出来了。你二年级转学过来,我靠,没两天就和咱班那几个三道杠、二道杠的小丫头腻上了,一到课间,好嘛,原来挺文静的小女孩让你追的满楼道乱跑,那叫疯。
有一次,在楼梯口,我看见你被那几个小女孩摁在楼下拐角滚成一团,哥们儿的心都碎了。什么是嫉妒?什么是恨?那一刻全懂了。”
曹剑痛苦地皱着眉头,伸长脖子拱出个酒嗝,搓搓血红的兔眼,“你丫其实长得也一般,真一般。小时候胡同里的大人都说你眼睛长得好看,其实眼皮还没我双呢!嘴唇倒挺男人的,但一看就是色鬼!我一米七五,你一米七四,比我还矮……”曹剑醉眼朦胧中用手愤恨地拿捏着一厘米的分寸,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夏克明,除了这破一居室,你还有别的房子吧?”曹剑指着他大声质问。
“我给老太太买了个房,有时住在那边,怎么了?”
曹剑瞪着一对血红的兔眼审视着他,“我知道,你发财了,截长补短仨鸡俩鸭地玩着。鱼翅鲍鱼不请我吃,拘在这破一居室弄点小菜糊弄哥们儿,我去洒洒水。”
“你丫才玩鸭呢,出去吐!”夏克明探身一把攥紧曹剑的衣领子拽向房门。房门撞开的同时,俩人看见楼下老张头踟蹰欲离的窘状。
“多大岁数了?好奇心还这么强?”曹剑喷出满嘴的酒气。夏克明死死拽住他的脖领,曹剑迤逦歪斜地挣脱着,粗脖红脸地大吼大叫。
“听一次贼话易,一辈子扒黑门听贼话难。老,老……”
枯枯瘦瘦的老张头被呛得咧着干瘪的嘴直眨巴眼。
“进屋,屋里没破鞋,您去买张**看看……”曹剑咝咝哑哑没完没了地说着。
“你妈找不到你,给我打电话说她快死了,让你回去看看,不孝的玩意儿,作死吧!”老张头留意地看着夏克明的眼眶。
夏克明松开手,曹剑忽地趴倒在老张头身上,
“这酒味!……”老张头两只干枝似的胳膊立刻胡乱地推搡起来。
曹剑从深喉处舒畅地“哇”了一声,恶臭蔓延弥散,老张头绝望地大叫:“不孝的玩意儿!”枯树乱摇,疯似的捶打曹剑,反被曹剑更加紧紧地抱住。
夏克明看着老张头背上大片的污渍,贴满了胃部深加工后色彩斑斓的渣渣沫沫,幸灾乐祸地大喊:“本朝以孝治天下,没有不孝的玩意儿,都是不孝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