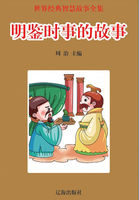坐上车后,范慧萍的肢体欢乐的像只小兔子,言语像个小白鼠一样吱吱喳喳的说个不停。
远离了校园,她的动作冰冻了,言语沉默了,变成了一只受伤的小麻雀依偎在我后背上。
我加足马力。我要冲破这份忧伤。飞啊飞,冲啊冲。我的脸被冻成了青茄子,手冻得失去了知觉。
直到油耗尽为止,车被迫停下来。
“怎么不动了?”她的脸没有离开我的后背,小声的说。
“没油了。”我说。
“怎么不多加些油。”她说。
“它之前喝足了。”我说。
“这里是那里?”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
“还在L城吗?”她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
“那你知道什么?”她又问。
“我知道我叫高鄢,你叫范慧萍。我叫你‘小孩’,你叫我‘小孩’。你是我老公,我是你老婆。”我说。我想用她爱听的话语化解她的忧伤。
“不错,记住这些就足够了。”她笑着说。我这招还真灵。
“还难受吗?”我问。
“好多了。”她的声音很小。看的出来,她的心情还是很低落。
她下了车。
我跟着下了车。
她从摩托车的左边转到右边,欣赏着周围的景色,向前走了几步,说道:“这里很棒啊。”
我这才注意到眼前的景色。这里是一片广垠的草坪,周围种栽着巨大的龙爪槐,中央是一个池塘,池塘里凸出数条荷花梗,最显眼的当属池塘边上的那棵两人伸开手臂才可以抱过来的银杏树。银杏树的树枝千丝万缕,都直直的向天空伸着。可见在其它三季中,它一定相当的茂盛。
“是故意带我到这里来的吧?”范慧萍转过脸,调皮的问。
“是没油了。”我坦诚的说。
“那就是天意了。”我说。
我无言。
“能和喜欢的人到这里浪漫一下,真是太棒了。”她转回了脸,边说边蹦跳着飘进了草坪。
我认为她的忧伤此时短暂的过去了。
“过来啊!”她走出十米后,转过了脸,朝我喊道。喊过之后,她不管我有没有跟过来,径直向大树走去。
我顺着她的脚印走了过去。
范慧萍走到银杏树下,左手抚摸着树干,围着树转了一圈,她转完一圈后,我正好也走到了树下。
“你真好。”她甜笑着对我说。
我一笑置之,在树旁坐下。
她也坐在了树旁,头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闭上了眼睛,我累了,需要休息。
不知不觉我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坐在了云上,俯瞰着下面池塘中游来游去的金鱼。我坐着很舒适,看的很安逸。不曾一阵风吹来,我一不留神,掉了下来,落进了池塘,全身湿透了冷水。
我猛的醒了过来,迅速的发现脸上全是冰凉的水。抬眼看到范慧萍虎视眈眈的瞪着我,双手在一下一下的甩着水。显然我脸上的水是她一手造就的。我收回了看她的眼神,用衣袖擦拭脸上的冷水。我知道我小难临头了。
“你昨晚去那了?”她的样子像是在审问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背着她偷了女人。
“幸福村。”我坦白的说。
“一夜都在?”她问。
“计划失败后,就离开了。”我说。
“都和哪个女的在一起?”她问。
“村长李艳。”我说。
“还有谁?”她问。
“可以不说吗?”我反问道。
“那我就杀了你。”她说。
“王秀凤一直都清楚我的行踪。”我说。
“你见到她本人了?”她说。
“是她亲自证实我掉进了套中,妄想摆脱也只是徒劳。”我说。
“你们在一起多久?”她问。
“一个晚上。”我说。
“孤男寡女?”她问。
“我们的伴侣只有酒和火锅。”我说。
“还喝了酒?”她说。
“而且喝了好多。”我说。
“醉了?”她问。
“一塌糊涂。”我说。
“后来呢?”她问。
“没有后来了。”我说。
“一定有!”她确定的说。
“恕我无可奉告。”我说。
“你们发生了关系?”她猜测道。她脸上的表情很痛苦。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会更坚定的击败她。”我说。我默认了我和王秀凤的关系。
“你会爱上她吗?”她脸上的表情更痛苦了。
“我和她只会是敌人。”我说。
“我要你发誓。”她说。
“我不会发誓,我只会用事实证明事实。”我说。
范慧萍沉默了。她满脸通红,脸上的肉在一下接着一下的颤抖着,像在刻意的压制情绪。
“我没接你电话,是因为醉酒后睡的太死,万万没有想到昨晚会发生那样的事。或许这也是她们的计谋,牵制住了我,让你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受到那样的伤害。”我解释道。
“我才不会生气呢?就是没有王秀凤,你也不会喜欢我。”她说着,转过身向草坪外走去。
我对她又拉到爱情上,产生了很深的无奈,迈着小步跟在了她的身后。
“我们现在是安全的吗?”她问我。
“我的车速应该甩开了眼线。”我说。
“换做平时的我,要是到了这里,该多么高兴啊!”她说。
“原来你也那么多愁善感啊!”我说。
“每个人都有多愁善感的一面,我只是将其隐藏住,不轻易流露出来罢了。但平时的欢乐确实是真正的欢乐。”她说。
“过去的可以让它过去吗?忘记今天的烦恼,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好多。”我说。
“用什么方法走出这种困惑。”她说。
“比如想想我们现在该怎么回去?那里会有加油站?”我说。
“对啊,我们该怎么回去啊?”她反问我。
“只要我的车喝上了油,过去一秒我们就会离家近些。”我说。
“那就让我们新的开始从到家的第一步开始吧。”她说。她的心情有了恢复。
走到摩托车前。我说往东会有加油站,她说加油站在西边。最后,我推着笨拙的摩托车,范慧萍跟着后面,说一会儿,沉默一会儿,朝着太阳就要隐下去的地方走去。
我们向西走了约有五公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见到,更别提某个加油站了。此时,范慧萍仍坚持自己的选择,相信再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中国石化的大标牌。
我没有厌烦感,因为和她有聊不完的惬意话题。又走了一公里,仍未见中国石化的牌子。
“这是什么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鬼地方啊!”范慧萍踢了一下摩托车后轮子的轮胎,问我。
“除去草木,它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感悟道。
“你没后悔?”她问我。
“你都没有后悔,我何谈悔之。”我说。
“你似乎还很陶醉。”她说。
“置身于静寂的大自然,又有美女相陪,不陶醉那还是感情动物吗。”我说。
“那你愿不愿意在不影响前进的情况下让美女休息一下下呢?”她说。
“美女累了?”我反问。
“确切的说美女很累了,她脚破了腿酸了腰麻了肝颤了心疼了颈扭了头蒙了,屁股都歪了,你说,美女应不应该休息?”她精神抖擞的说。
“如果不让美女休息,那就太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了。”我说。
“那你还不停下来。”她立刻命令道。
我停下来,转过头看她怎么个休息法。
她眯合着双眼,对我笑了笑,灵活的爬上了摩托车,像一个将军似的坐下来,迅速的做了一个前进的手势。我叹了一口气,苦笑着推起摩托车向前进。
她狼腔鬼调的唱起《走西口》。
她唱完后,催促我也唱一遍,或者唱个别的。
我摇了摇头,没有答应。
她笑我脸皮儿怎么一下子变薄了,之后又唱了起来。唱到一半,她突然欢声喊道:“乖乖隆地洞,我们的救星来了。”
“那不是加油站,只是一辆卡车而已。”我看着前方,叹道。我是从车灯判断出来者是辆拖挂卡车。
“马儿,快快停下来。”她对我喊。
我停下脚步,转头不解的看她要耍什么花招。
她从摩托车上跳下来,几步跑到路中央,毫不思索的躺在了地上。
我看她躺下后,才想出她的目的,我快速丢下‘老婆’,跑过去。此时,我失去了思想能力,脑袋里一片空白。
卡车已经近在咫尺。按正常车速来算,我没有拉起或者抱起范慧萍,我们就已经身在车下了。
我拼命的拉扯范慧萍,她没有理会我,闭上眼睛,仰天吟道:“生我者天,葬我者地。”
卡车在离我们四米处猛然刹住了车。发出了一串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声。
我双腿一软,瘫坐下来。
范慧萍转过脸,睁开眼,吟道:“汝等何称之为大丈夫,不如一小女子也。”
我无心理她,只是一味的安抚心的狂跳。
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大肚便便的年轻男子,他那粗狂的言语几乎和双脚落地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
“你们找死啊!”不必描述他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猜到他此时头顶冒烟了。
“我们不找死,我们找你。”范慧萍说。
“找我做什么?”司机气恼的问。
“找你借样东西。”范慧萍说。
“你们想抢劫?”司机醒悟着说,接着从驾驶室里抽出一条长有一米二粗如小孩手臂钢棍,来捍卫自己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