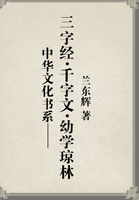“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千三百多前,宋之问说出我此刻的恐惧,只不过当时他是唐代有名的诗人、进士,而我只是一个不定期回家的乡下孩子。
首先遭遇的还是那条崎岖的小路,多少年了,依然是那样的曲折和坑洼,且感觉越来越窄,甚至容不下我两只并立的脚。表层的泥土和植被都被雨水给冲走了,只露出醒目的一道道深刻的印痕,像水井边沿被绳子勒出的凹槽一样,成为麻雀的饮水池或是蚂蚁的藏身之所。来来往往总有自行车一不小心陷进这些道道里,差点摔倒,只好推着车慢慢走过去,还忍不住回头望几眼或骂咧几句。现在,我就走在这可怜的路上,道路两旁是半人高的杂草,间或有几只放养的黑猪在草丛里觅食,当我抬起头,迎面遇上的便是这个叫“罗岭”的村子。
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特定的表征,历经千年,仍然不失其本色,比如池塘,池塘里将整个身子潜在水里的老水牛;比如田野,田野上已收割的稻子和已插下的秧苗;比如山坡,山坡上安家落户的农民和草木鸟兽,如此等等,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而那突然蹿上来向我吠叫着的土狗,不是表示欢迎,而是满怀敌意,似乎暗示我户口簿上外乡人的身份。那是龙道友家的狗,大了很多,我认得它,它却不认得我,或许它只是象征性地叫几声;而它的主人道友就站在门前,跟我打着招呼,回来啦?嗯,回来了!我笑着应了声,却没有任何多余的话。我心中压抑的许多话,好像一路走就一路被丢弃了。他家门前的枣树结满了枣,青的,红的,大的,小的,有很多已经熟透,在风中,摇摇欲坠。
其实在这里,我只认识极少的人,我的父母,亲戚,左右邻居,小学或初中的几个同学,就这些,远没有在城里结识的朋友多。在我手机储存的上百个电话中,只有几个与这里有关,除了他们,大概也没人认识我。
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出父亲或母亲的名字,“哦,足和平(风英)家的小儿子啊!”对方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很仔细地看着我,似乎在寻找我父母当年的痕迹,而我也因此在这里获得存在的身体认定和相应的辈分归属。
这当然很好,因为有的人在这儿生活了近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他们仿佛是这里的过客,或是多余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来处,也不知道自己的去处,只有浑浑噩噩的现在的生活。比如八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光棍,看见他,我就想起了阿Q。八爷年轻的时候有的似乎只有力气,他把大把大把的气力都花费在为别人建房子、收割庄稼、迎亲发丧等诸多乡间事宜上,却从未为自己建一所像样的房子,种几分地,或是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他把劳动得来的辛苦钱,很快转换成几包好烟和麻将桌上的赌本,烟抽完了,钱也输得一干二净,再四处给人做活,抬预制板,挑砖石、稻谷,以及抬棺材。几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哗哗地过去,如今他是村里不多的五保户之一,每个月领上两三百块钱,管一个人的生活,除了偶尔给人家帮帮忙,就是抱着用罐头瓶做的茶杯,站在棋牌室的角落里看别人打牌。他的眼睛常年浮肿,耳朵更是聋得厉害,要么大声说话,要么一声不吭,街上的人不得不得出结论:那个有力气能干事的八爷真的老了!
老去的又何止八爷一个人呢?我走过那些寡妇或鳏夫的门前,他们的蜗居里常年不见灯火,蜘蛛网密布在屋梁上,蛛丝悬垂下来,像一张张奇异而恐怖的抽象画,黑暗的门洞永远阴森着,透出寒气,正如我不敢靠近的他们冰冷的内心。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不愿拉亮灯,仿佛是惧怕那耀眼的光明,他们习惯了在黑暗中一个人摸索,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总让我去街上的严爹爹家拿学校订的报纸,每次走进那间黑洞洞的房间,我的心总跳得厉害,那浓重的中药味裹挟着一个老人衰弱的身体和呼吸,也让我不由地心生寒意,呼吸困难,话语哆嗦。我从未看清过他的面孔,更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只感觉中药味越来越浓烈,而他的气息却越来越微弱。每次拿了报纸出来,都如释重负一般,赶紧飞奔回家。现在想来,我的身后,总像有什么东西在跟踪着,追赶着,呼呼作响。许多年了,我不敢回头。
赶紧回来吧,母亲打来电话说,石榴已经红了,再不回来就都给人家摘了。石榴其实是长在邻居家的后院里的,如果没有中间那堵形同虚设的土墙,它们也相当于我家后院的一部分。邻居家的两个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我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尤其是中风后软绵绵地躺在椅子上,斜过门口的夕阳覆盖在他们苍白变形了的脸上;他们的几个儿女也早在别的城市成家立业,极少回来,房子租给一个精痩的老女人照看着。爬山虎郁郁葱葱,爬满了整个外墙,看上去生机勃勃,其实却反衬出无人打理的颓败。倒是院子里每年开花结果的石榴树、枣树似乎成了共享的资源,成为周围的人们进入这个房子的唯一理由。母亲好像也经常给我找些回来的理由,这一次是那些已经红透的石榴,咧着嘴,在召唤我哩!
可谁又能听懂神的召唤?不是爱神,不是美神,而是死神;不在眼前,不在耳边,而在无时无刻。那辆摩托车开得真快,像飞一样,后来的目击者反复说着这句话。他听见风声在耳畔呼嘯,却无法想象那是死神向他发出的致命召唤。半空中突然断垂下来的一根电线,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瞬间横扫过他的身体,他的头颅飞出很远,而他身后的妻子也仿佛被风卷起,像一张单薄的纸片,翻滚着,摔倒在路旁,当场死去。当我在电脑上敲下这几行残酷的字词,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敲打着近在咫尺的死神的衣袍。那被风吹散的血腥,似乎再次凝聚成巨大的阴影,将整个村子和我团团围住。
我们像经历过大风大浪大喜大悲的旁观者,围坐在桌旁,一边剥石榴,一边聊那些远远近近的人和事。柏油路已经铺到了街尾,自来水也接进了村,母亲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办下来了,父亲的工资改革也终于兑现了,这些让人望眼欲穿的事情在苦苦等待之后终于有了比较圆满的解答。然而与此同时,有些等待却注定无法逃脱破碎的命运。十步之外,江龙喜老人已经无法像往常一样走路,他必须借助各种物体的支撑,才能挪动沉重的身体,通常他只能坐在椅子上,膝盖上搭一件旧衣裳,从早晨一直坐到黄昏。我回来的时候,他先于我的父母听到我的脚步,回来啦,他笑着说,我照例喊一声,眼光便很快掠了过去。现在,他和他的老伴又必须接受一个突然降临的噩耗:他们的还不到五十的大女婿,刚被检查出身患癌症,肝癌晚期。他们的小儿子,我的朋友江华,陪着他姐夫在上海治疗,他跟他姐姐、他姐夫都说是肝炎没关系的会好的,像大多数病患家属一样尽可能地掩饰着这个不幸的真相,然而他又能坚持多久呢?一双正在上初中的儿女还在等着他们的父亲早日回家,可当他们真的看到经过化疗之后瘦骨嶙峋的父亲又该如何面对?年近八十岁的江龙喜望着门外,他在等待遥远的消息,而那未知的消息又将是怎样的消息?母亲说,罗岭竟出这怪事,许多年纪轻轻的突然就得了癌,老的八十、九十了,还活得好好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是水质,饮食,生活习惯,还是人的命数?聊到后来,竟没了言语。黄昏的余光随着母亲转身进了厨房,父亲也紧跟了过去,他们剥好的石榴籽散落在桌上,饱满,晶莹,红得透明,接近于白。
一夜无话。自然的声响依然清晰而热烈,我却无心过问。母亲说,菜地里还有辣椒,小白菜秧,弄一些带上吧,城里什么都要买,菜也贵得要人命。我说我也去吧,很久都没去过菜地了。曾经的菜地连同一座梨园早已因为修路而消失了,只剩下道路旁的一块地,也只有五畦,还是母亲向生产队里讨要来的,需根据时令轮流耕种,才能保证每日饭桌上都有新鲜的绿色食物,除了厨房,这巴掌大的地方是母亲施展才华的又一舞台。然而很不幸,那些母亲预留给我们的红辣椒在我们到来前被人洗劫过了,只有小的嫩的还零星地挂着,幸免于难。一定又是大胞(音),母亲显得很生气,这个大胞,老是偷人家的菜!她为什么不自己种呢?没地吗?我很奇怪地问。那不就是她家地嘛,荒着呢,母亲指指旁边,她啊太懒,整天就知道打麻将,没菜了就四处偷,冬瓜,茄子,瓠子,什么都偷,家家菜地都被她偷遍了,又没当面抓到过,你还不好找她说,哎!听着母亲的愤懑和叹息,再看身旁那几块寸草不生的菜地,我的心刹那间仿佛荒原一般,曾经那些欣欣向荣的绿意,那些朴实勤劳的身影,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偷”了去,只留下一片荒芜,一片茫然。
刚近中午,便有人来喊母亲去打牌,母亲本不愿去,但拗不过劝说和诱惑,还是去了。来人是棋牌室的老板娘,地点离我家只有百米。棋牌室,这个合法公开的赌博场所,我常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居民区里见到,不知何时也在这里扎下根来,不管在哪,都是一样的人头攒动,烟雾缭绕,生意兴隆。牌客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小学教师,小店个体户,以及无所事事的乡间闲人,主要活动项目已简化为唯一,那就是麻将(我从未在任何一间棋牌室见过象棋或扑克),输赢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罗岭街上许多人的无数个下午,包括母亲的无数个下午,都在那一间十几平方的小屋里稀里哗啦地度过。父亲笑着说,和别人吵架受了气的母亲,输了钱的母亲,赢了钱的母亲,是不一样的,他可以从她刚回到家的脸上提前找到答案。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母亲,她那看似坚韧实则虚弱的身体,根本不能长时间低头,僵坐,动脑,受气,赢少输多的定理她也是知道的,然而在料理完繁乱的家务事之后,沉浸于四方城中找寻片刻的轻松和慰藉,似乎已成为她最后的精神寄托。不打牌,一个下午做么事呢?母亲问我,我想了半天,竟无法回答。
风落下来,吹拂松动的树叶和我翻开的书页,每一叶(页)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一个人的悲喜忧伤,生老病死,把它们按时间的线索编连在一起,就是整个村庄的历史吧。只是此刻,有许多身强力壮的树叶还飘在异乡的土地上,冬天的时候,他们才会成群结队地飘回故里,和守在这里的枯黄的稚嫩的亲人们短暂团聚,然后再去往城市继续飘荡。像一片树叶,或像一只候鸟,他们坚信这就是他们的宿命。而这中间,只有极少的树叶或候鸟能够停歇在灯火辉煌的枝头,重新长成一棵树,或一根草一根草地慢慢筑巢;也有一小部分因为意外,因为绝望,永远地滞留在他乡的半空中。现在的罗岭,正像一棵深秋的树,根须还在,枝干还在,树叶却禁不住摇摇晃晃,生机黯淡。
又到了离开的时候。江龙喜老人靠着门框睡着了,他的脸、头发和墙壁一样苍白;路过棋牌室,母亲正埋头专注于“东西南北”,这一次,她没有看到我的背影;人群里的八爷眯着眼冲我摆摆手,随即就被烟雾和人声淹没了。再次经过村口那陂池塘,池塘名叫龙塘,当然没有龙,只有过度繁盛的水藻,占据了整个水面,几条筷子长的鱼浮在其间,死去多时。谁能想到,在那看似平静的水面、看似诱人的绿色之下,却暗藏着让生命窒息的杀机。那些缺氧的生命,注定坚持不了多久,要么跃出水面,寻找新生,要么在貌似繁荣的美好里草草了却一生:这多像一个悲喜交织的隐喻!
越来越像一个神圣的仪式,越来越惧怕自己成为悲观的听众,在不断死去的消息中,完成对一个乡村的怀念和终极叙述。我终于知道,那个近乡情怯的宋之问后来被流放钦州,赐死异乡。如果说死亡是回乡的一种仪式,那么他最终以生命完成了这首神圣而悲凉的诗歌;而如果死亡也是一种寄寓希望的“往生”,那么我何时才能看见一个在涅盘中浴火重生的乡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