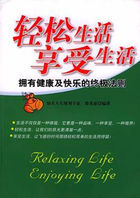蜿蜒逶迤的砂石路面,棱角分明的众多暗红色小石块紧挨在一起,在夜晚微凉的空气中形槁心灰;它们和两旁禅絮沾泥的树木一样,犹如被潮湿的空气沾染了,一副漫不经心的慵懒模样。
一身戎装的景腾和口含雪茄的张啸天肩并肩走在上面,步伐镇定;像走在前面、高度戒备的李少强手提的钢枪。
来到申公鹤居住的小岛,景腾提议下车走走,感受一下夜晚静谧的风景;张啸天欣然同意——能和好友吹吹林涧的清风,听听夜莺的啼鸣,倒不失为人生一件乐事。
头戴德式军盔、手持冲锋枪的高进和花溢从砂石路两旁的树林中敛声息语地穿行,侦查有无隐蔽的敌情;作为华夏军队的最精锐之师,单射击来说,他们都能做到听声辨位,弹无虚发!
申府的院子里,两名护院躺在地上,没有了呼吸;一同遭殃的,还有那两条和他们形影不离的大狼狗——一条被浪人们开膛破肚、架在了火堆上烤;另一条挂在石榴树上,正被武士残忍地剥皮。别墅的大门,由一个手持长刀的武士把守;别墅内,铃木一郎和四个武士得意忘形的在申公鹤夫妇、若兰母子、来福和艾青的面前耀武扬威。要不是艾青“抬”出张啸天,申家老小早已遭了毒手——申公鹤在纱厂的一把大火,烧掉了铃木一郎的“心头肉”,能不让他狗急跳墙?铃木一郎考虑到张啸天是东瀛国即将任命的淞沪市长才迟迟没有动手,他要等未来的市长夫人走后行动;因为张啸天和申公鹤是老友,杀申府的人,必须顾及张啸天的感受。他没有想到,被帝国寄予厚望的人就要离开淞沪了。
高进来到别墅的偏门,发出了三声怨鸟的叫声;花溢在别墅的另一面,也发出了几声相同的鸟叫。
那是他们的暗语,意思是一方准备发起攻击了。
高进将冲锋枪背在身上,从围栏翻入院内,蹑手蹑脚地走到墙角,手指抠着墙体青砖间仅有的一点空隙,加上脚的配合,一气呵成爬到了别墅顶层的天台。天台中央的桌子上,放着几本小人书;这儿是若兰哄亦双和亦轩玩的地方,她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讲故事。
孩子的陪伴,冲淡了若兰不少的孤单。
高进把小人书揣进怀里,将冲锋枪的绳索紧了紧,掀翻了桌子。
一楼客厅内的众人听见声响,齐刷刷地望向天花板。铃木一郎以为还有“漏网之鱼”,挥了下手,两个武士拔出刀,顺着楼梯往上层跑;检查完二楼,再到三楼,没有任何发现的他们不死心又上了天台。倚靠在天台门后的高进待两个武士上来,掐住后面一个,扭断了脖子;走在前面的武士察觉不妙,刚转过头,即被捡起武士刀的不速之客削去了脑袋。
高进在武士的尸体上擦去刀刃上的血渍,来到二楼,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完,将茶壶丢在了地上。
铃木一郎和另外两个武士到底是骄横惯了,急于弄清楼上情况的他们不管是不是对手的调虎离山之计,想都没想,另两个武士又“蹭蹭蹭”地跑向楼上,看见一身军装的高进,二人挥起长刀即砍了过去;高进身体一歪,蛮横的长刀砍在了他身后的桌子上。没等武士再起刀,高进手起刀落,划开了他的喉咙;另一个见势不妙,转身飞快地向楼下跑。高进将刀竖起,倏地掷出,从背后穿透了他的身体;武士闷哼一声,倒在楼梯口挣扎了几下,一命呜呼!铃木一郎大惊,大声呼喊着往外跑;情急之下,竟然没想到抓个弱者做人质。门口的武士不明就里,提着刀往别墅进,正好和慌慌张张的铃木一郎撞了个满怀,同时跌倒在了地上;高进走上几步,用刀指着他们。
烧烤的武士听到屋内的异常,忘记了狗肉的醇香,抄起地上的长刀赶了过去;花溢从围栏上跳下,挡在了六个浪人的面前。凶相毕露的浪人们大叫着挥刀砍来,花溢抓住一个,夺下刀,一边用他的身体抵挡其余浪人的进攻,一边对他们一击致命。
可伶被花溢抓住的浪人,在做了刀下之鬼前,还捱了同伴的好多刀!
解决掉几个浪人,花溢从背上取下冲锋枪,抱在怀里,隐藏在了暗处。
李少强打开大门,让景腾和张啸天走进。景腾笑着对张啸天说:“啸天兄,请!”张啸天神情自若地掏出火柴,划着,点燃含在嘴里的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舒服地吐出,笑了笑,搂着景腾的肩膀,一齐走进了别墅。
高进将铃木一郎和武士拖到了一边。
亦双见景腾进来,满脸委屈地跑过来叫大伯;景腾笑了笑,牵着她的小手,坐在了沙发上,说:“亦双不怕。”亦双点点头,看着景腾的衣服,羡慕地说:“大伯的衣服真好看!我也想穿。”景腾笑着说:“等你长大了,跟着大伯,大伯送一件比这还好看的衣服给你。”“嗯!”亦双认真地点头。景腾看了看若兰怀里安安静静的亦轩,问亦双:“弟弟好像没亦双勇敢,亦双不会欺负弟弟吧?”亦双跑过去,把弟弟拉到大伯的身边,答:“不会。姆妈说,我的性格像爹爹,弟弟的性格像姑姑。”“像姑姑不好。”景腾面色凝重地对亦轩说,“要改。”
妹妹的出走,景腾感到不快,却又做不了什么。
“公鹤兄,东西收拾好了吗?”张啸天问。
申公鹤走上几步:“啸天,你怎么才来?”
“我也想早来,可早来也不能这般顺利地救下大家。”张啸天拍着景腾的肩膀说,“景腾老弟麾下一个人,顶上我手下一百个人!我带一百个人就是能救下大家,或许大家还要受点皮肉之苦。”
“多谢景长官了。”明白过来的申公鹤说。
景腾笑了笑,说:“叔叔客气了!亦双和亦轩是景家的骨肉,如果出了事,我会深感内疚的;他们还小,却要面对如此的鲸涛鼍浪,实在是我景家没尽到责任。”
“都过去了。”张啸天说,“赶紧走吧。”
申公鹤答应,招呼家人拿行李。
“这位是张先生吧?”铃木一郎强作镇定,希望通过和张啸天套近乎,使自己脱离险境。
张啸天笑了笑,明知故问:“鄙人正是;请问你是哪位?”
“我叫铃木一郎。田中武官的好友。”铃木答。
“恕在下眼拙,我们好像没有见过,更谈不上认识啦。”张啸天说。
“现在不认识不要紧,等您做了淞沪市长,我们的接触自然会多起来。”铃木一郎说,“到时还请张先生多多关照。”
“谁说我要出任你们任命的淞沪市长?”张啸天皱起眉头,走向铃木一郎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大淞沪的地下皇帝,还稀罕你们这些禽兽任命的一个市长?你们不来,我不知有多快活!”
申公鹤走近哑口无言的铃木,说:“这世上,有多少人是以慈悲怜悯的目光、幸灾乐祸的心理去看待某一件事的?今日你东瀛欺凌我华夏,西方列强看着,想坐收渔利,却表现得像仁慈的上帝;等到西方列强凌辱你东瀛时,你们的国民又会是何种心理?人啊,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今天你种下什么样的因,明日必结下什么样的果,没有人是永远的赢家。”
“跟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好说的?”张啸天拿过高进手里的刀,说,“今天我来送这两个东瀛鬼子上路;用他们的血,祭我们的航程!”
“啸天兄,等一下;小孩子不看,我先带他们出去。”景腾说完,牵着亦双和亦轩往外走,问若兰,“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若兰似乎还没从恐惧中回过神,木然地点了点头。
“有人帮忙收拾了。”艾青指着铃木一郎和武士说,“我来时,这两个人在客厅挟持申家老小,还有几个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都搜刮在这儿了。”
景腾看了一眼地上的金银细软,让高进帮申家带上。
张啸天哈哈笑了笑,让艾青、卓莲枝和若兰赶快离开;艾青等人走后,他笑嘻嘻地看着申公鹤,问:“公鹤兄,你要不要看?”
申公鹤想了想,向外走,说:“我……还是不看了。你帮我宰了铃木,到了香江,我请你喝酒。”
“好说,好说。”张啸天笑容依旧,手中的钢刀已刺穿了武士的胸膛、劈开了铃木的头颅。
申公鹤走到在院子里垂泪的管家跟前,说:“来福,我有件事要托付给你。”“老爷尽管吩咐!”来福说。“我放了三百块大洋在桌子上;你拿一百;另外的两百是给护院师傅的,你帮忙给两位师傅的家人送去。”申公鹤说,“昨晚走的下人,钱都给他们了吧?”“都给了。”来福哭着说,“按您的吩咐,每人五十块大洋。”“那就好!”申公鹤说,“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走,多保重吧。”来福点头:“老爷、夫人多保重!”
景腾把亦双和亦轩抱在怀里,深情地说:“大伯送你们一程,以后要照顾好自己,还要帮丑爹照顾好姆妈。”亦双点了点头,摸着景腾的下巴,说:“大伯,你的胡子该刮了。”景腾和身边的艾青、卓莲枝都笑了起来。若兰说:“还是我们亦双会照顾人。你跟着大伯好不好?让大伯带你去找爹爹。”“好!”亦双点头,认真地答。
花溢全神贯注地瞄准快速奔袭过来的七八个人;确定来人的身份后,他放下枪,发出了三声猫头鹰的叫声。
领头的杨绎举起手掌,让队伍停了下来;他蹲在地上,仔细地辨别了一会儿,也发出了几声“呜呜呜呜、啊啊”的叫声后,起身更加快速地前行,很快到了别墅。
“命令!”景腾放下孩子,威严地说。
杨绎等肃立。
“后队变前队,肃清此地通往汇丰码头、对我方构成威胁的一切障碍。逢鬼杀鬼,遇魔降魔!”
杨绎等挺胸应答,做着出击的准备。
景腾蹲下来,摘下钢盔戴在了亦双的头上。高进取下自己的给亦轩戴上。亦双摸着钢盔,说:“大伯,我的头小了。”景腾笑了笑:“是帽子大了。”
砂石路恢复了生机,因为受到了行人的感染——全副武装的杨绎等士兵形成战斗队列走在最前,应对突如其来的敌情;高进、花溢和李少强殿后。刚刚赶到的陆逸尘和五十多个手持利斧的门徒围成了一个圈,将怀抱亦双、亦轩的景腾、张啸天夫妇、申公鹤夫妇和若兰护在了中间……
两声长鸣的汽笛过后,飘扬“米”字旗的轮船缓缓驶离了岸边;甲板上,张啸天、艾青、申公鹤、卓莲枝、若兰和彩蝶神情恍惚地注视着码头上朝他们挥手的景腾和陆逸尘等人。随着轮船马力的越加越大,他们深情对望的身形越来越小。手握小人书的亦双和亦轩在甲板上欢快地跳跃,像迎着浪花飞翔的海鸥;他们还小,还体会不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