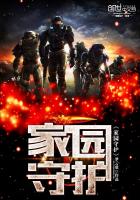那一连串关于小时候的记忆,都是在人界度过的,在那间叫做“汇茶坊”的山涧小屋,有陪着自己长大的爷爷奶奶。
虽然山上并没有住其他人,但我总还是自己一个人在竹林里跑来跑去。偶尔也会来一些到汇茶坊喝茶歇脚的人,但很快就都离开了。所以平时并没什么朋友,那些花花草草还有满山的竹子和茶树,就是我最好的玩伴。
后院角落的藤椅上,我正在编织刚从山里折下来的竹条,完全不成形,就是胡乱穿来腾去,立着的竖着的竹叶全部拉出来,就成了一股绳。
“你好。”一个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跑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抬起头来,歪着脑袋看她,黑溜溜的眼睛放着光,可神气了。穿一条粉蓝色及踝连衣裙,一件白色高腰泡泡袖小外套,看上去特别乖巧。
当时我穿着白色斗篷长得拖到地上,斗篷帽子搭在肩上,每天都那么穿,因为记忆中,我的衣服全是那样的。
“你的衣服真好看。”女孩继续说道。
“你跟我说话吗?”我问道。
那女孩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当然啊,这里又没有其他人。”
“那你来这里干嘛?”我问。
“我看到那儿有一扇门,觉得好奇,就过来了,然后就看见你在这玩竹叶。”女孩说。
我将手中的藤条递给女孩,说道:“诺,给你。”
女孩接过去,将我编在一起的枝条一一拆开,一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想了想,说道:“爷爷奶奶都叫我叶子。”
“叶子,是长在树上的叶子吗?”女孩新奇地看着我,问道。
“是的。”我说。
“我叫倪儿。”女孩说。
“倪儿。”我叫了一声。
“嗯,你叫我干嘛?”女孩答应道。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觉得面前这位叫倪儿的女孩很有意思,除了爷爷奶奶,很少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话。
实际上,我会经常从山上采很多树叶,折很多竹子枝条放在后院里。这倪儿一来,我们俩就将这些干了的以及新鲜的枝条翻来覆去折腾。把枝条铺在地上,将叶子揪下来在地上拼很多乱七八糟的图案,拼出来不喜欢的,就在上边跳,用脚使劲踩,踩得汁液满地都是。汇茶坊后院石块铺成的地面,就这么被染得青一块绿一块。
“你喜欢这些叶子吗?”我问道。
“真好玩,以前我从来没玩过,爷爷奶奶都不让我碰。”倪儿说。
听到倪儿的话,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问道:“可是我的爷爷奶奶天天都让我玩这些东西,你的爷爷奶奶怎么就不让你玩呢?”
“他们说上边有虫。”倪儿说。
我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些树叶,在手里翻来翻去地看,说:“我什么虫都没看到啊。”
“这些树叶打过除虫剂吗?”倪儿问。
“什么是除虫剂?”我问。
“我们家阳台上种的花,叶子上长虫的时候,奶奶就会拿出来喷一喷,可以杀死叶子上边的虫子,让花健健康康地长大。”倪儿说。
“我走过的地方,树叶上都没见过虫。”我说。
“那太神奇了吧,居然有不长虫的植物。”倪儿说。
倪儿说,她是同爷爷奶奶到山上来行茶事的,行完茶事下山的路上就会到汇茶坊停留片刻,汇茶坊里提供的茶汤特别甘洌,好喝的不得了。
后来,倪儿每次跟着爷爷奶奶上山,都会到汇茶坊来坐一坐,实际上就是她爷爷奶奶在堂内坐坐歇口气,她就跑到后院来找我玩。
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倪儿居然觉得植物都会长虫,可我从来没见过,可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啊,怎么会这么大的差别呢?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见到的世界跟其他人见到的世界会有些不一样。又或者,很多人见到的世界相互之间本来就不同。
有一次,我拉着倪儿的手,说:“我带你去竹林里玩,那里边的竹子又高又大,还很绿,都没有虫子。”
“真的都没有虫子吗?我都不敢相信。”倪儿说。
“我带你去我经常去的地方。”我说。
我们俩就这么手牵着手从偏门跑出后院,沿着我平时玩耍的小路,听着流水叮咚去寻找那一条涓涓小溪。
刚开始,一路上竹影婆娑,阳光窸窸窣窣地洒在石板路上,倪儿见到那场景又惊又喜,兴奋地赞叹了一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地方,平时出去都有好多人,看不到人的地方又不敢去。”
“这就是我每天都会走的路。”我说。
“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来吗?”倪儿问。
“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走这条路。”我说。
走出很远,天变得阴沉起来,风也哗啦啦地吹,竹子就开始疯狂的摇摆,竹叶也被狂风卷得纷飞乱落了一地。踏着竹叶铺成的小道,依旧听着流水叮咚,伴随着竹叶被风吹得刷刷作响,织就交响乐曲,缠绵悱恻。
倪儿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紧紧抓住我的斗篷,颤颤巍巍地贴着我走,还说:“刚刚还有太阳的,这里怎么这么黑。”
“这里没有太阳起落,是因为你刚刚看到了强光,突然光线弱了,就有些不适应,习惯就好了。”我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倪儿把我抓得越来越紧。
“是的。”我说。
“这里边会不会有奇怪的东西?”倪儿靠近我耳边,问道。
继续往前走着,小溪流水的声音越来越近。溪水拍在石壁上,清脆的响声回荡在竹林里,久久徘徊不忍离去。从我会走路到这之前,都是我一个人来这里,从来没想过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
“没有。”我说。
“真的没有吗?这跟电视里的恐怖片特效太像了。”倪儿说道。
倪儿这么一说,我才想起自己几乎不看电视,电视里的东西都太奇怪了,那些人和事发生得根本不符合人的意愿,全都是不可扭转的命理程序。
“你经常看恐怖片吗?”我问。
“就是跟我哥个看过几次,吓得我晚上都不敢回屋睡觉。”倪儿说。
一阵疾风吹过来的时候,头顶的枝条呜啦啦响彻云霄,光线的确很暗,除了能看见眼前的路,远处的情景根本看不清楚。不过,没在视线范围内的东西,看不清很正常。可倪儿不知怎么的,“哇”的一声扑过来将我紧紧抱住,怎么都不肯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