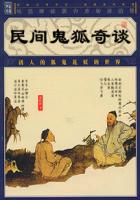屋内的打斗声很快引来了门口放哨的和准备埋伏我的几个喽啰,几个人把男人团团围住,你一拳我一脚的厮打起来。由于距离太近使用枪支不方便,那几个大汉也只好把手枪别在裤腰带上在地上随手捡了些竹竿木棒就上前加入了混战。但即使男人面对十多个大汉的集体围杀,却任然能暂时不落下风,不禁令我刮目相看。响声一大,正在休息的方光军顿时被吵醒了,一开门就被一个被打飞的大汉压倒在地半天不能动弹,顿时气得直骂娘:“靠,我去你娘的狗东西,姓鸡鸡的你别TM的不识好歹,看老子一枪崩了你!”“是吉吉!”男人顿时恼怒的吼道。“嘿嘿,我就这么叫,咋地!”方光军顿时就贱起来了,一边重复那两个字,一边居然还扭起屁股来嘲弄男人,哪有半点老大的风范?“草!”但是男人明显是个爆脾气,这招十分管用,男人顿时气得面庞通红,手中的砍刀瞬间就向着方光军甩了过去!“嗖~!”伴随着一道破空声,砍刀准确的射在方光军刚才站的地板上,插进去数指深,而方光军那老狗却在千钧一发之际闪到一旁,连皮都没蹭到,顿时不屑的道:“真他妈好激,蠢得跟牛一样。老子要是这么好砍中的话这十几年的沙子就白淘了。哥几个加油上啊,蠢牛没了角,蹄子没什么好怕的。”言罢打了个哈欠,转身回屋。男人呆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不禁破口大骂起来。他呆了几个狗腿子可没呆,一下子男人的身上就中了几棒子疼的蜷缩在地板上抱头蜷膝任几个大汉打了好一会儿才停手,我伸头一看,整个人早已血肉模糊,筋疲力竭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一双眼睛还在不屈的喷吐着愤怒的火焰。“妈了个巴子的掉老子五颗牙!”先前那个砍男人的大汉不再“晕倒”从地上一跃而起,捂着生疼的脸上前狠狠地踢了几脚连吐几口唾沫还不解气,顿时从地上拾起一只手枪“嘭”的打穿了男人的小腿。男人顿时惨叫一声几度晕死过去。
“嘿嘿,叫你拽!”碎牙大汉见男人如此痛苦的表情很是受用,狞笑着还要开第二枪。“够了。”一直闭目养神的二叔冷不丁来了一句,声音不大却饱含威严。碎牙大汉的手顿时一哆嗦,乖乖的退到一边不说话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同样是被困在笼子里的动物,一只狮子和水牛所展现出来的威严是不同的。二叔一行人任由大汉们把自己捆牢,对一旁的男人道:“唉,穆子,我告诉过你,没用的。该来的总会来的。”被称为穆子的男人捂住正在流血的左小腿,冷哼道:“哼,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二叔不禁哑然失笑,对着穆子轻轻耳语了几句。穆子顿时浑身一震,不着痕迹的对我这边看了一眼,小声道:“林爷,您确定能行吗?”“哼,怎么不行?穆子,你瞧不起我们老林家人吗?”“怎么会!我只是怕林灵…怕小灵…爷……对,我只是怕小林爷是新手,没什么经验啊。”穆子一句“爷”顿时把我捧上天了,使我对这个能打的汉子又多了几分好感。“屁,什么叫没经验?你刚生下来就会手艺啊!”二叔瞪了穆子一眼,随即又面色阴狠的望向一旁的角落道:“至少我能保证不会再次看走眼,像某些人叛变!”“…”我这才注意到一旁的角落里有一个蜷缩的人影。人影听见二叔的话顿时吓得又忘身后的干草堆里面缩了缩。叛变?什么叛变?我看见穆子顿时变得狰狞的脸和二叔杀气毕现的脸庞,难道是他出卖了二叔?我想道。也应该是这样,还记得父亲曾跟我提起过,早些年二叔盗了一地主的祖坟,那地主二话不说花重金请了几百个道上的汉子来长沙追杀二叔,近千人地毯式搜索愣是没从芙蓉区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找出来,后来才知道二叔这家伙居然冒充当地的导游大摇大摆。二叔这个老狐狸想这样白白抓住他基本上不可能,只有内部人走漏消息才会中招。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迷迷糊糊的看见腕上的表已经指向了“三”,稍稍揉了揉发麻的双腿,随即小心翼翼的抬起头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大汉们一个个哈欠连天,穆子的鼾声足以掀开房顶。凌晨三点,正应该是人一天当中最疲乏的时间点,也是我预定下手的时间,我能强打精神从12点挺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此期间,我也想过离开找胖子帮忙,但只要我往后挪一步,腐朽的地板就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吓得我一动都不敢动。那个可恶的方光军中途也醒过来一次,好像是问问那几个守门的大汉有没有抓到我。笑话,你爷爷我一直蹲在你们屁股后面,能抓到我才怪。那个守门的大汉回答也是可笑,他迷迷糊糊的说:“好像抓到过一次。”“什么‘一次’?人呢,在哪抓的?”方光军四下看了看,好奇的问道。“在…在…在梦里……呼~”大汉说着说着居然站着睡着了,把方光军气得直跳。我对着假寐的二叔眨了眨眼,二叔不着痕迹的点了点头。我又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当几乎所有人都打呼噜、连二叔都迷迷糊糊时,我看准时机悄悄地推开这扇门,随即蹑手蹑脚的移到二叔他们旁边,看了一眼地上那个伙计,尼玛,瘦的跟猴似的。随即我注意到在这群全部几乎受伤的人当中,穆子伤的最重,但是有两个人身上几乎完好无损。一个是我二叔,他只有脸上一块小淤青;还有一个是一个戴着黑色面纱的神秘人,身上完全没有受鞭打的伤痕,皮肤白嫩的不像话,跟女人似的,睡得很沉。我轻轻地唤醒每个人,慢慢地用指甲剪一个个剪开他们手上的绳子。正当我准备推醒那个神秘人时,二叔眼睛突然变得血红,一双大手狠狠地钳住我的那只小嫩手,疼得我眼泪都下来了。“二叔你干嘛?”我轻声道。二叔面色阴沉的放开我已经变得红肿的手,声音低沉的说道:“别碰她!”那声音低沉的不像是人话,更像是一种野性的嘶吼。穆子他们看向我的举动吓得一哆嗦,连忙应声道:“小林爷别,千万别碰。”我从来没见过二叔这么发怒,吓得脸色惨白。穆子示意我看神秘人的下身,我一看,尼玛,他手腕上根本没绑绳子,屁股下面还有一个天鹅绒的软坐垫,跟二叔他们比起来这待遇明显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方光军他们对二叔这么忌惮都没有给这VIP待遇,我不禁邪恶的想道,难道姓方的看上了这小子?嘿嘿,也难怪,这细皮嫩肉的,哪个gay不喜欢啊?二叔明显看出了我的疑惑,轻声道:“如果这位想走,没有人能拦得住他。”我擦,还是个高人啊!我不禁对这位神秘人多了几分敬畏。穆子轻轻地用一根小木棍碰了碰神秘人的左臂,假洋鬼子轻轻地扛起那位昏迷不醒的伙计,我们一共八个人,乘着夜色快速向外跑去。屋外的大雨已经停了,几颗星星镶在这被雨水洗过宛如明镜的夜空之上,散发着璀璨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一路小跑到那苍蝇铺子,七个人挤在一张一平米的小木桌旁,二叔点了一碗臭豆腐、一份卤鸭舌、一盘土豆丝、一锅水煮鱼一大桶米饭和一箱啤酒。铺子的老板老张和二叔有过旧交情,刚吆喝完菜就被老张拉去喝酒了,见我欲言又止的模样扭过头对我说“等下次再和你说缘由,以后可以信任穆子”后就闪到内屋去了。我们一行人此时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一旁有说有笑的喝酒吃菜其乐融融。我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刻意与那个神秘人拉开距离,好像十分忌惮一样,碰杯痛饮时也不与神秘人的杯子有半分接触,神秘人也毫不在意,一言不发在一旁自斟自饮好似习以为常。我不禁好奇宝宝一样凑到穆子旁边问道:“穆子,那神秘的家伙是谁啊?感觉好不合群。”穆子本来喝红了脸在一旁大着舌头讲荤段子,一听我这话顿时清醒了,也不大舌头,对我耳语道:“小林爷你别管那么多,只要知道这个女人千万不能碰,连头发丝儿都不能沾!”“女人?”我诧异的看向这个离我们远远地的女人,胸前的“飞机场”真是太容易令人产生误会了,应有的翘臀也平平的,整个一“I”字型啊!“为什么不能碰?”可我这回无论怎么问穆子都不回答了,只是向二叔那个方位努努嘴便不再理我。我怔了一会儿,难道她是二叔的女人?我草二叔品味什么时候下降了这么多啊!但既然是二叔的女人,那就是我二伯母级别的人了,自然碰不得。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二叔看见我碰她的时候会那么激动了,唉,看来是真爱啊。不过二叔居然也会找到真爱,真TM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酒过三巡,我这个根本不会喝酒的人自然醉的一塌糊涂,两瓶啤酒就让我头晕目眩了,穆子直笑话我“小林爷长相和酒量都像娘们”。我不服,想起今天方光军的叫法,就故意问他道:“那穆子,我问你,今儿个那方老狗为什么叫你‘鸡鸡’啊?”“呃……”老实巴交的穆子一下子憋红了脸,我们一行人全部哈哈大笑起来。穆子气急败坏的叫道:“笑什么笑!再笑老子一刀让你断子绝孙!”众人这才稍稍平息了下来,但还有偷笑的。这时,一个略显猥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因为穆老头是蒙古人,全名吉吉特穆尔,那方光军和我猴哥一样看他不爽,都叫他‘鸡鸡’。”我们一扭头,那个浑身是伤的瘦瘦伙计咳嗽了几声从木榻上慢慢的爬起来,冲我们一笑,夺过一瓶酒一干而尽。一个伙计乐道:“哎我说瘦猴,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喝酒不怕呛死啊?”“你懂个屁,酒是最好的疗伤药!”瘦猴“嘿嘿”笑道。我不禁好奇的问道:“这位瘦猴同志,你为什么受了那么严重的伤,比他们重好几倍?”“嘿,小子,老子是在墓里……”没等瘦猴说完,穆子就打断道:“小林爷你别听他扯淡,这小子指力大练得一手三脚猫的打弹子功,爱耍阴招,在我们被包围的时候耍阴用石子打爆了人家一只卵蛋一只眼,被几个人围殴打得半死不活直接晕死了,这TM是活该!”说罢,几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虽然穆子说是三脚猫功夫,但能精确的打爆眼球和卵蛋,我想这个瘦猴的指力绝对练得出神入化了,但能用打卵蛋这个下三滥的招,此人一定猥琐到家了。那瘦猴知道我是“小林爷”后明显对我有了一丝敬意,不敢再叫我小子了,对我尴尬一笑就和穆子他们拼酒,两个活宝你一句我一句的骂了起来。在此期间我曾想找那个假洋鬼子道歉,但他一看见我的目光就冷哼一声扭过头去,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穆子明显醉了,搂着我满口酒气:“小林爷,你要知道,这刘瘦猴可是我们这儿唯一一个摸金的,满肚子坏水,嘴巴里荤段子绝对不少,来大家掌声鼓励,让死猴子给咱爆一个!”“哈哈,好!猴哥来一个!来一个劲爆的!”众人起哄起来,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