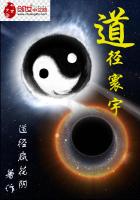天渐渐地夜了。
傩傩去集市上一天了,不知怎么回事,此时,尚未回来。难道,狼肉不好卖吗?英子与撒撒坐在自己那个破败的屋子门前,不住地望着小路那头,希望看到傩傩扛着一包东西突然出现在村边那株老社树下。月亮升起来了。渐渐地,星星也开始在天空不住地眨着眼睛了。但是,傩傩依旧没有出现在村边那株老社树下。
见如此,英子不管那么多了,她本来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便关上了那扇破门,准备睡觉了。不过,她平生相当怕老鼠,不敢一个人呆在那个老鼠很多的屋子里。她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砍脑壳的,死在哪那去了?!”英子站在屋子门前不住地张望着,希望看到傩傩扛着什么东西出现在村边那株老社树下。
不过,又过了一段时间,傩傩仍旧没有出现,使英子不禁“砰”地一下关了门了,却又不敢一个呆在那屋子里。这时,如果有一个人给自己做伴,那该多好啊。她想起了雨花。正好,雨花这时也从自己屋子里走过来了,站在英子那个破败的屋子门前不住地看着什么东西,似乎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却又一时没有找到。
“雨花,在这儿干什么呀?”
“无聊,在这儿散散步。”
“今夜依旧给我做伴好吗?”英子的声音。
“好啊。”雨花的声音。
于是,雨花又走进了撒撒的屋子了,脱了衣服,上了床,与英子睡在一起了。
太阳好高了,雨花仍在躺在英子的床上,直至听见闲花站在屋子门外不住地吼叫着了,才慌慌忙忙地爬了起来了,衣服也忘记穿了,便匆匆走出门外,在闲花的骂声中离去了。
闲花把雨花赶到自己屋子里后,便相当气愤,自己女儿成了什么人了,竟给她英子做伴。
闲花不禁相当气愤,走出自己屋子门外,走到大宏门前那株大柳树下,站在人群中,无语着了。她见了英子,不知为什么,几乎想过去咬几口,以泄自己心头之恨,却又不敢,怕自己打不过英子。她只好那么无语地站在大宏屋子门前那株大树下,在一片风中,听着人们不住地窃笑着,笑自己女儿夜里睡在撒撒的屋子里。
她本来想走回家好好地把雨花打一顿,却又怕这样一来,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以后叫雨花怎么做人呢?于是,她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吃了早饭,没有什么事的她依旧走到大宏屋子里,坐在那张木桌上,与老欢之流打着牌玩。不过,较比昨日稍有不同的是,她已精心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翻,身上也抹上了香水了。当她走到人们身边的时候,老欢闻到了那股香水味,本来坐得离闲花较远的地方的他竟刻意凑到闲花身边,不住地大口大口地吸着气,见人们用惊咤的眼光看自己,便谎称头晕,权且做做深呼吸以缓解之。不过,闲花却知道其真正的用意所在。他不就是想坐在自己身边闻女人味吗?却又如此狡猾地以深呼吸做幌子。她渐渐地对老欢厌恶起来了,不过,又没有在脸上露出来,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任其不住地在自己身上闻着,大声地笑着。
她要报仇,为自己的女儿,不能就这么让撒撒把自己女儿睡了不是,却又不敢声张。撒撒一家人不是那么好惹的,这,她又不是不知道。文文是没有什么用的,只会打铁,只会坐在那个木桌上不住地喝酒。不要告诉他了,告诉他了反而不好,届时没有把撒撒怎样,自己家里却先闹翻了天了。文文只会拿她出气,对此,闲花是相当清楚的。
她要找人来为自己报仇,却又不知道找谁。山村的人大部分不是撒撒的对手,不要说打了,就是与之相相骂也不可能。
不过,也还有那么一个人敢于与撒撒较量,此人便是老欢。由于没有妻子,一到了赶集的时候,他便会搭毛大那只船,去绿萍镇,去那个小醉楼喝酒,直喝到月亮出来了才罢。
老欢不光在那个小醉楼里喝酒,还要做点儿什么事,那便是抱女人的大腿,特别是年轻女人的肥嫩的大腿。不过,这事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丑陋,却每每以之作为在人前炫耀的资本。对此,石头村的人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任其那样,难道还能打他一顿吗?老欢的儿子在城里发了财了,谁敢得罪老欢?
闲花坐在老欢身边,任其不住地在自己身边闻着,不仅没有介意,反而高兴,生怕他不这样做了。她要用这个办法笼络住老欢,而后,想个什么法子利用这个人为自己报仇,雪去扣在自己头上的屎盆子。
但是,老欢也好像怕着撒撒。是啊,撒撒他妈的也太那个了,怎么连狼也杀得死呢?与这样的人能打架吗?而现在,闲花好像要利用自己去打撒撒,他不禁不那么肯干了,到时没有打赢是小事,说不定还会像那头野狼一样悄悄地死去了呢。
“杀到!”闲花这样边出牌边说着这样的话。
老欢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想叫自己去杀撒撒,不过,他不会那么傻的。他不禁坐得离闲花远了一点儿了,对此等之人,还是要敬而远之的比较安全。
见老欢坐远了,不再不住地闻自己身上的那股香水味了,闲花的脸不禁黑下来了,甚至想骂他“砍脑壳”了。不过,这不是自己的男人,岂能随便骂?她什么也没有说地坐在那儿,不住地叹气,却又是那么悄悄地,以至于一个人也没有听到。
这时,雨花不知从什么地方走进来了,坐在老欢身边,看着其手中的牌,闲花看到了,不住地对雨花翻白眼,却又不便大声地说出来,怕人们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