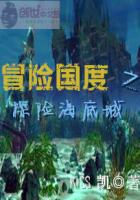我跟大头缓缓抬起头,IC卡的光照向上方,只见天花板的床上趴著一人。这人的动作有些扭曲,活像一隻壁虎一样。当光线照到了她的头部,我看见了她披髮散乱,目光狰狞地瞪著我。这是一张苍白而又充满怨恨的脸孔,恐怖得无法描述。她的一隻手,几隻指甲在不断地抓挠著床沿的金属支架,发出勾魂般的刺耳声音。
我被彻底吓傻了,只感觉双脚酥软无力,一屁股坐倒在地。接著,她朝我扑了下来!
我迅速地抽动身体,坐了起身,开始大口喘著气。
眼前有光,好像是在一个光线充足的房间内,可头还有点晕眩。
我发现我满头是汗,背后的衣物都被汗水浸湿了。而我现在正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床前有位穿著护士装束的阿姨正吃惊地注视著我。
我看了看她,又检视了一下我所在的房间。这才意识到我是在一间医疗保健室裡,这儿的空气裡散著淡淡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我的床头靠著窗户,浅绿色的两摆窗帘束拢起来像两条辫子。外面正是黄昏。
原来是我在做梦。
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但那个梦似乎非常真实。在梦中,我,大头和KELLY进入了老鬼的房间,我们被电晕后醒来,发现已经被锁在了斗室裡面。后来KELLY变得很奇怪,她爬到了我们的头顶,然后朝我扑了下来……这一切都太真实了,回想起来都令人心有馀悸。
“小朋友,我这裡有尿布,你要换吗?”护士阿姨面带讥讽道。
她这麽一说,我才意识到下半身还是湿热的,我竟然尿床了……我顿时觉得无比羞愧,脸红耳赤。
“雷子,你太逊了。”
说话的是大头,他躺在我旁边的另一张单人床上。他朝我眨著眼睛,看样子也是刚醒过来没多久。
“你们总算醒了,再睡就要天黑了,想在这儿过夜,我可要算你们工分才行。”护士阿姨笑道。
“我们怎麽会在这?”我问。
“你们在──”
电话的铃声突然响起,护士阿姨不得不中断说话,走到门口接听起挂在牆上的电话。
我听不清楚她在电话裡头说甚麽,只见她捂著嘴,故意压低音量。匆匆说完几句话后就挂掉电话,又回到了我们床前。
“你们两个太顽皮了。两个小时前,C区巡逻的警卫发现你们昏倒在隔离中心,把你们送到保健室。”她说。
“原来如此。”我说。
看来我们现在还在疗养院。
“阿姨,我口渴。”大头道。
“你们两个捣蛋鬼可耽误了我下班时间。”她边说边给我们各倒了一杯温水,端给我们,”现在已经严重超过了探访时间。”
我一口将整杯水喝进肚子,感觉自己的状态稍微好了点。同时,我感到手掌在胀痛,也不知道具体是甚麽部位,但又好像是别处在胀痛。不,好像全身好多地方都在胀痛。
“雷子。”大头趁护士阿姨走开后,悄声叫我。
“怎麽了?”
“你刚才是不是做了噩梦?”他脸色有点古怪。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把我在梦中见到的情景跟他讲了。结果他听完,脸色变得铁青,我马上问他有甚麽不妥,他说他竟也做了一个跟我同样的梦。
这太诡异了。我们昏倒在老鬼房间后,然后做了同样的噩梦。
等等,会不会我们其实并不是做梦,而是又一次昏倒了?
护士阿姨听到我们在左一句右一句的,忍不住插嘴进来叫停我们:”行了行了,你们都烧坏脑子了吧?有个大麻烦还等著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擅自闯入隔离中心是违规行为?刚才警卫打电话来说要审问你们,现在你们赶紧起床。你……”她指著我,又指向我的床,皱了皱眉,”这床单记在你工分上。”
我一听警卫要审问我们,就心叫不妙,我爸好歹是民生党总干事助理,人民公仆,要是他知道自己儿子擅闯疗养院禁区,肯定要臭骂我一顿。如果总干事助理的儿子在外头闯祸的事传出去,肯定有人会说三道四的,搞不好最后还会涉入到甚麽政治问题。而大头可能还好一点,扣扣工分甚麽的,他家没有政党背景,谁也不会关注他们。
此时我竟有种衝动想逃跑,就像干了坏事的小孩怕被家长发现一样,但这念头随即又在心中扼灭了。他们都已经见过我的脸,如果找到我的话肯定会罪加一等,我估计我爸到时要气疯了。现在这情况也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或许我应该指望坦白认错,然后被从宽处理。
敲门声骤然响起,就像审判日的刽子手来访一样。护士阿姨打开了门,进来了两名手持防暴棍,穿著宽鬆警卫服的中年男子。他们跟她交头接耳了两句后,其中一人朝我们走了过来。这人走近我时,他忍不住用手捏住鼻子,一脸鄙夷地看著我。
”跟我们走。”他厌恶道。
我和大头闯了祸,不敢说不字,只得乖乖起床跟著他。
走到门口时,大头似乎想到了甚麽,转身便问:”阿姨,只有我俩被送来这裡吗?”
护士阿姨眯著眼道:”你们还有其他同党?”
我推了一把大头,代他回答:”不是,我们睡糊涂了,在梦裡遇到了别人。”
“你最好把情况一会交代清楚。”她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
我们跟随著两名警卫离开保健室,进入了一条走廊。这裡是一座大楼,沿途经过了不少房间。大头边走边一脸疑惑,小声问我刚才为甚麽不让他问清楚。我说也许KELLY醒来后先离开了,总之不能被其他人知道是她带我们进入隔离中心的,他才恍然大悟,作出了个OK的手势。
其实我当时很傻,并不知道警卫只要调出IC卡记录就可以查到谁进入过那栋建筑物,不过当时我只想著无论如何也不要连累KELLY,并没考虑太多。然而这件事情接下来的发展似乎比我们料想中更加复杂。
两名警卫将我们带到了一间拘留室,这房间整洁得像是刚搬进去的办公室一样,空气裡有种清洁剂的味道,以及化纤地毯的面料味。
我不理解为何疗养院会有拘留室,简直像是个常备的设施,难道他们这儿经常有人被拘留?
警卫将我们留在了拘留室后便离开了,我听到门外传来上锁的声音。房间裡只剩下我和大头,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安下心来,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见面审问我们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决定了我们将面临甚麽样的处罚。
拘留室大概二十平方,牆壁和天花板都是白色,地上铺了地毯,走起路来特别消音。房间正中摆放著一张桌子和四张椅子。
大头和我坐了下来。
我本以为他会跟我说点甚麽,或者抱怨我硬是要调查老鬼的事情才惹得一身麻烦,不料他却发著愣。良久,他像是想到了甚麽,问我:”雷子,你说他们凭甚麽拘留我们?他们又不是治安队的。”
我知道拘留室一般都有监控,所以双手抱头趴在桌上,我的额头压著桌沿,脸向下,小声说:”也许是想在事情调查清楚前,才决定要不要把我交给治安队。”
“他们一定会问我们为甚麽会昏倒在老鬼房间”大头也学我降低了声音。
“接下来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迷路了。”这话一出口我马上意识到太不靠谱了,哪有人跑到地下室乱逛,还在裡面昏了过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想找个厕所。”
“不知道他们甚麽时候开始审讯我们。现在几点了?”大头心烦道。
我坐直了身,看了看手表,发现表盘破裂,指针停在了3点10分。我心想,我的表为甚麽会摔坏?难道是在老鬼房间摔破的?
“快7点了,我看到了,门口有时钟。”大头道。
“嗯,我记得离开食堂时是2点半,两个小时前警卫找到我们,那时是5点,说明了我们在老鬼房间裡昏迷了两个小时。”
“下午4点访客就必须离开疗养院。”大头匝匝嘴,“我们已经过了末班车时间,看来我们今晚要走回家了。”
“别想了,现在还不知道要待在这地方多久。”
我们不约而同叹了口气。
突然,大头的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饿了。”他说。
“我也饿了。”
我揉著自己的肚子,忍受著自己满身的臭味。我想到今天中午我只喝了一杯果汁,现在全身早就没力气了。
之后,我们就这样坐著,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著话。大半小时过去了,始终没人进来过,也没人给我们带来水或食物。事实上,门外一直没动静。
我突然想起自己带了手提电话,于是从口袋裡掏出来,试著拨出一个电话回家,但是没有拨通。疗养院位于山裡,信号就比较弱,而这儿没窗,除了排气孔外,近乎是密封的,所以手机上才会一格信号都接收不到。
摆弄了一会后我不得不放弃,看看大头,他也无奈地摇摇头,显然他的手机也没信号。我感到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全身乏力,实在有点忍不住了,于是起身走到门前敲门,盼著有谁至少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就算扣我工分也愿意。我用力敲了几下门,接连喊了几声,门外终于有动静了。
我心中当下产生了一种喜悦感,但随即又感到了紧张。
有个满头银灰色短髮,脸上尽是鬍渣的中午男人迤迤然走了进房间。他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脸上有条七寸的刀疤,面目吓人。只见他不发一言,似笑非笑地掩上门,示意我先回到位置上坐下。我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来审问我们的,并且从他的言行看来,他是个狠角色,这对我们而言并不是好事。
当我回到位置上时,他也跟著坐到了我们对面椅子上,我听见椅子发出”咯吱”的声音。在光线下面,我看到他铜色皮肤像抹了油一样,身板结实,可见这人不是经常锻鍊身体,就曾服过役。
银髮男先后打量了我们一眼,直奔主题道:“你们到C区隔离中心有甚麽目的?”
“我们是瞎逛的,跟导游走散了。”大头抢著回答。
“为甚麽会昏倒在那裡?”他继续问。
“因为太饿了。”大头临时编了一个答案,我感觉这个回答弱爆了。两个人同时饿昏了,这哪裡是来探亲的,这明显就是流浪的。
银髮男把视线停在了我身上,续问道:”谁带你们进入隔离中心的?”
“都说了我们自己瞎逛──”大头有点不耐烦,银髮男突然伸出手,宽厚的手掌朝向大头的脸,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我看见他的手背上有不少伤痕,在手腕的部份有一块褐色纹路的皮延伸到了袖管裡头,那是严重烧伤后,重新植上的皮。
银髮男冷冷地盯著我,清了清喉咙,重覆一遍刚才的问题:”谁带你们进入隔离中心的?”
显然他是想我来回答。
这人的目光太锐利了,我不由自主地避开了与他视线交锋,说:“大头说得没错,我们迷路了。”
然后,他没再提问了。
我感到心很悬,也不知道他在想甚麽,我悄悄看向他时,感觉他的视线一直凌厉地盯著我看,我心慌得低下头,再一次避开他的视线。
突然,他双手用力一拍桌板,撑起了身子。这举动把我跟大头都震慑了一下。
接著,他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我听见门又被锁上了。
“怎麽又把我们关在这裡……”大头怔住道。
“他看穿了我们。”我说。
“不会吧?我刚才明明表现不错。”
“不是表现的问题。”
我们编的太假了。特别是刚才他看向我时,他就好像一条银色的鲨鱼,嗅穿了我们的谎言。可我懒得跟大头解释,有时候我觉得他太迟钝了。
随后又过了两个小时,银髮男没再回来过,也没有其他人进来过拘留室。
门口的时钟已经指向了10点,平时这时候我早就在家吃完饭,坐在沙发前看著週日剧场。我突然想念起我妈烧的饭菜,我想她现在一定也在担心著我怎麽那麽晚都没回家。
我有点饿过头的感觉,口也很渴。我看看大头,他也是一脸没精打采,像是被剃了毛髮的动物一样。我感到气忿,我觉得他们对待被拘留的人是毫无人性的,难道他是是要先精神折磨我们一顿,再继续审问吗?
大头索性趴在桌子上睡觉,不去想了。我也有点犯睏,只能趴下来。迷糊间我感听到觉门再度开启的声音,有人走了进来。我立马坐直身体,拍醒大头。
来的人是刚才的银髮男,他手上拿著两瓶瓶装水,站在我们面前,还是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让我想起电视剧裡典型的反派表情。他说:”你们可以走了。”
我愣了一下,以为是听错了,都没反应过来。
“这是给你们带上车喝的。”他把两瓶瓶装水放在了桌上。
我太口渴了,看见水后反而更加觉得口乾舌燥,但我不敢去领,我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耍我。大头见我没去领,他伸到一半的手也立即缩了回去。
“不打算走吗?”他眯起了眼。
我看向他,并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感觉。说真的,我不明白他为何要放我们走。但看他的表情似乎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想,现在不走,万一他反悔了可不好?
我下定决心,拍了下大头,示意快走。他点点头,领到我的意思。
我们两人旋即起身,领过瓶装水,像是捡了条命一样朝门口快步行去。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不料他居然一手揪住了我的肩膀,那股力道很结实,就像大人抓小孩一样,捏到了我的肩骨的凹位。我心想不妙,难道他真的反悔了?当我侧过头看著他时,我发现他没有正视我,他的眼睛像是散发著诡异光芒的黑曜石,一直看著前方。
他的手指开始用力,我觉得非常疼,我想要掰开他,却发现两隻手都使不上力气。大头见状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忙。
忽然,他鬆开了手,用眼角的馀光扫射了我一眼,从嘴裡溜出了一句充满警告的话:”别再多管閒事。”
我疼得根本没心情想他话中用意,不断揉著似要脱臼的的肩膀,大头扶著跟我,我们屁滚尿流地离开了房间。
一出拘留室,我就见到之前带我们来到拘留室的两名中年警卫,他们要带领我们往大楼外走。我边走边迫不及待去看手机,仍然没有信号。试著换到不同的角度也收不到一格信号。
出了大楼后,警卫安排我们上了一架刚充完电的小巴。我们上车后发现车裡面没开灯,有点暗,除了司机外,还有几名乘客。看他们衣装都是疗养院的工作人员。而这是一班疗养院的员工专车。
车子在夜色中开进了山道。
起初,我跟大头都没说甚麽话,可能大家都很疲累。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外枝桠不断飞速掠过,全身冒著冷汗,肩膀的刺痛仍然触感犹新。
突然,我手机像是活了过来一样,连响了几声,那是我设置的提示音。我打开一看,有好几个从家裡打来的未接来电,如我所料,我妈一直在担心了我。我正犹豫要不要马上打回家,可手机忽地黑屏了,按了两下没反应,我心想,难道是没电了?
”大头,借我手机用一下。”我一边继续摆弄著手机,一边说。
大头并没有理会我。
”大头?”我又喊了一声。?
这时小巴突然刹车,骤然停在了公路上。我整个身子因为惯性往前面椅背猛倾,压得我胸口的肋骨都麻了,手机也掉了。
我揉著胸口,疑惑地看向小巴外头。外面黑云遮月,光线惨淡。我又看著前面,司机一动不动,其他乘客也像木雕一样,只剩下幽黑的背影。我心想这是演哪出啊?赶紧去叫我旁边的大头,可没想到大头瞌著了,怎麽推他叫他都没反应,好像房子烧起来都可以照样睡。这让我感觉十分不安。
四周一片死寂。我的视线被车窗外一棵形状怪异的大树给吸引了。这棵树很丑,惨白的月光从缝隙中渗了下来,树干上的疙瘩像是恶魔的表皮,树枝如同爪牙,隐约溢漫著阴森的气息。
我心头不禁一紧,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感觉非常不祥,似乎从我背后隐隐飘来了阴冷的气流,说不出有多怪异。
我整个人打了个冷颤。
一整天遇到的怪事真多,难不成还没结束?
突然,后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尖锐而刺耳,一听之下我就头皮发麻,全身血液像凝结了一样。我在心中大骂糟糕,该不会是那个KELLY一直跟著我们吧?
果然,我们在老鬼房间裡并不是做噩梦。
此刻我完全不敢回头。我听到指甲抓挠金属的声音,时快时慢,俨如深渊裡恐怖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