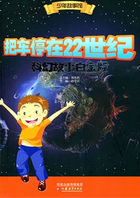这种公开辩经的方式并不罕见,在婆罗门中经常出现。因观点不和,相互约定时间,旁观者作见证,如同武士决斗般,两人用辩论决一胜负,输的人名誉扫地,赢的人获得荣誉与众人的尊敬。
“乌玛必胜!乌玛必胜!”
婆罗门都来观看这场辩经,他们高呼“乌玛必胜”的口号,个个雄心万丈,仿佛已经赢了。
另一边,楼陀罗的信徒也聚集起来,尽管大祭司严令禁止他们入,可楼陀罗的信徒已不把陀刹的命令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陀刹并不是什么领袖,更不是什么权威,只是另一个教派的头目而已。他们高呼“王子必胜”,如果王育赢了这场辩经,对他们不利的形势将彻底扭转。
乌玛依旧身穿白袍,圣洁高贵,她一出场,婆罗门立即沸腾。乌玛登上高台,她环视全场,台下观众密密麻麻,在她眼中似若蝼蚁。然而在这些蝼蚁中,却未见到对手崩德罗迦,乌玛忽然间有几丝失望。
螺角吹响,人群再度沸腾,宫门打开,国王和国师出现了。妖连王穿了身便装,遮罗夫人呈现人类外形,作贵妇打扮。他们走上这座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仆人同时把国王的宝座抬了上去。台上台下的婆罗门向他微微欠身,以示敬意,妖连王对他们微笑点头,算是回礼了。
“你的父亲不来吗?”妖连王目光扫过众婆罗门,问向乌玛。
“父亲说,这是小事,他不用出席。”乌玛回道。
国王来了,大祭司却不来,显得大祭司比国王还尊贵。妖连王对此呵呵一笑,“我也只是有空来看一看。”他说完,坐上宝座。女国师遮罗夫人坐了他身边,婆罗门也都坐下了。
“还不开始吗?”妖连王问。
乌玛只是微笑,不答话。
立即有婆罗门说:“国王,你的儿子还没到,怎么开始呢?他怎么迟到了?”
婆罗门约好似的,都起了哄,责问王育为何还不出现。婆罗门一闹,其他观众也闹了起来,有跟着婆罗门斥责王育迟到的,也有为王育辩护的,维持秩序的人连呼“肃静”,都制止不住。乌玛走到铜锣前,一声锣响,声音盖过众人,这才安静了。
乌玛对着众人说:“凡事都讲规矩,崩德罗迦王子如果再不出现,就视为弃权认输。我再等他一会儿。”说着,她把沙漏倒转,细沙在漏斗里如水流动。
遮罗夫人起了忧色,王育去哪儿了?他不出现,整个国王派系的颜面就丢大了。遮罗夫人不安地看着国王,妖连王面色无波,对她悄声说:“你还不放心他了?他如果没遇到意外,一定会来的。如果他遇到了意外,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借口。”
什么借口?向婆罗门兴师问罪的借口。这也是妖连王不慌不忙的原因。遮罗夫人自然明白这点,但他还是为王育担心,看着已经流逝过半的沙子,轻叹了声气。
而婆罗门的得意神情越来越重,他们马上就要不战自胜了。可乌玛却不怎么开心,她约王育辩经就是想看看他有多少智慧,王育不来,她的目的如何达到?
沙漏还剩一小半,约十息时间,就会漏个干净。
“不用等了!临阵退缩者来不了!”婆罗门已经兴奋,十息时间,不可能出现在此。
观众们嘘声不断,他们白来一趟。楼陀罗的信徒也都失望摇头,王子怯战,他们再无翻身之力。
“怎么不用等呢?”台下,突然有人说话,一个披着斗篷的平民抬起了头。兜帽滑落,正是王育。“我早就在这儿了,只是没穿王子的衣服,你们就认不出我。哎!这个看衣服的世界!”他边说,边解开斗篷,登上高台。
独斫和尼沙陀人也都在声,他们从人群中出现,集中起来。独斫接住王育丢下的斗篷,尼沙陀人呼吁观众为王育打气呐喊,楼陀罗的信徒们立即为王育高呼,嘘声消散,又热闹起来。
乌玛同样露出喜色,对王育问道:“你为什么不现身?躲在人群里是何用意?”
“因为我在犹豫,要不要与你辩经。”王育对道,“我这几日熟读经典,突然发现,这场辩论其实不合正法,是非法的。”
“哦?王子怎么认为的?”乌玛笑着问。
辩论已经开始了,王育直指正法,而正法是一切的核心。
王育负手说道:“我是刹帝利,你是婆罗门,我们之间怎么能辩经呢?以前从未有这样的先例。对经典提出看法,只有婆罗门才有资格,刹帝利只能聆听。所以,刹帝利罔论经典就是非法,这种事我怎么能做?而乌玛小姐,你主动提出要与我辩经,那就是提出了非法要求,你已经冒犯了正法。”
“竟敢污蔑小姐非法,你懂什么!”婆罗门气愤道。
乌玛抬手制止他,她对着王育微笑道:“刹帝利与婆罗门一样,自小学习吠陀,一个优秀的刹帝利,他的品德如同婆罗门般圣洁高尚。再说辩经并不是质疑经典,更不是否定,是在学习理解的基础上相互交流。虽然没有前例,但万事万物不都有第一次吗?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以前没生过孩子,就说自己没有生孩子的前例,不生孩子了,岂不可笑?王子以为呢?”
“照小姐这么说,正法不必追寻前例,只要本意是好的,就算突破传统也可以?”王育问。
乌玛冲他眯了眯眼,始终保持着笑容,“并非可以随意创新,正法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虽然正法微妙,对它的解理有无数种,但最基本的道理不可变动。就像男人可以娶几个女人为妻,但他不能娶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底线不能过。政治也是如此,国家要发展,墨守成规当然不可,但无论君王怎么改革,国家的基本结构不可动摇。种姓就是社会基础,是社会秩序的保证,如果告诉首陀罗‘你可以干婆罗门的工作’,那么这个首陀罗就会放着自己的本职不管,想着怎么做婆罗门。要是人人都如此,望着别人的职责,不专心干自己的事,国家还怎么运转?你说是不是呢,王子?”
王育点头,“小姐确实说得在理,每个人都要专心自己的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乌玛说这番话,就是想堵住王育的嘴,当王育提到正法不必遵循前例时,就一定会引出新政改革。新政是婆罗门心头的刺,乌玛此说釜底抽薪,管你怎么改革,正法不能改,种姓制度就是正法,谁动谁就是非法,就是制造社会动荡的罪人。
“可是乌玛小姐,如何判定一个人该做什么呢?靠出身判定吗?祭司的儿子就该做祭司,掏粪工的儿子永远掏粪?”王育问道。
“不该如此吗?”乌玛反问,“一个人出身在什么样的家庭,是由他前世的业果决定的。前世积德,今生投得好胎;前世作恶,今生受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一个人投生在掏粪工家庭,一定是前世做了不好的事;相反,一个人如果做善人,安于本职,贡献社会,那么他将投生为婆罗门,走上修行之路,最终摆脱轮回。”
“如果婆罗门作了恶呢?”王育再问。
乌玛答道:“婆罗门作恶,自然也有处罚。来世将不再为婆罗门,可能转世为低种姓,甚至牲畜,根据他犯的罪来决定。”
王育裂嘴一笑,“乌玛小姐,能否为我解答一个疑惑呢?前世、今生、来世,甚至是更远的前世、更远的来世,是否都是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