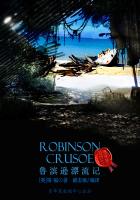“安妮,”戴维坐在床上,双手托着下巴说,“安妮,‘睡觉’在什么地方?人们每天晚上都要去‘睡觉’,当然啦,我知道我总是到那里去做梦,可是我想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每天穿着睡衣去那里,然后又回来,怎么一点儿也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呢?它究竟在哪里?”
安妮正趴在绿山墙西屋的窗口上,看着夕阳映红的天空,此时就像一朵硕大的花朵,橘黄色的花瓣,橙黄色的花蕊。她听到了戴维的问话,转过头来,梦幻般地回答道:
在月之山外,
在影之谷底。
如果是保罗·艾文,他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算他不明白,他也能自己去弄个明白。可是,眼下是头脑简单的戴维,正如安妮经常绝望地评论他那样,没有一丁点儿想象力,所以他仍然是一头雾水,迷惑不解。
“安妮,你没有认真回答我,简直是在说梦话。”
“你说得对呀,可爱的小家伙。你难道不知道,要是一个人整天都说些大道理,不是件很愚蠢的事情吗?”
“哎,我在认认真真地问你问题,你应该认认真真地回答我才对。”戴维给惹急了。
“噢,你太小啦,还听不懂。”安妮说。不过话说出口,感到有些羞愧。因为她突然想起自己小的时候,遭遇过很多次类似的冷落,于是她曾庄严发誓,决不会对任何孩子说“你太小,听不懂”这种话。可是现在她这样说了——很多时候,理论和实践相隔十万八千里。
“唉,我也想尽快长大呀,”戴维说,“不过这种事情着急也没有用的。要是玛莉拉对她的果酱不那么小气,让我多吃点儿,我相信我一定会很快长大的。”
“玛莉拉不是小气,戴维,”安妮严厉地说,“你说这种话,真是太不领她的情了。”
“还有一个词也是这个意思,听起来要合适一点儿,不过我想不起来了,”戴维皱着眉头说,“那天我听玛莉拉亲口说的。”
“你是不是说‘节俭’?它的意思跟小气完全不同。如果说她节俭,就是说她有着优秀的人品。要是玛莉拉小气,你妈妈死后,她怎么会收养你和朵拉呢?难道你喜欢和维金斯太太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我不愿意的!”戴维的语调陡地一下提高了八度,“我也不想到理查德舅舅家去。我只想住在这里,就算玛莉拉给我们的果酱很……节俭,可是这里有你,安妮。嗯,安妮,我现在要到‘睡觉’那里去啦,你可不可以先给我讲个故事?我不想听什么小精灵,那是小女孩才喜欢听的故事,我要听那种很刺激的故事……就像杀人啦,开枪啦,放火烧房子这种事情。”
所幸这时候玛莉拉在她的房间大声叫喊,安妮这才得以脱身。
安妮跑回东屋,透过夜色,看到从戴安娜窗户一闪一闪地亮着灯光,每次闪五下,这是她们儿时约定的信号,意思是:“赶快过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安妮赶紧用白围巾裹着头,飞快地穿过闹鬼的树林子,从贝尔先生牧场的一个角落直冲过去,来到果园坡。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安妮,”戴安娜说,“我和妈妈刚从卡莫迪回来,我在布莱尔先生的店铺里看到了玛丽·森特纳,她从斯潘赛山谷来。她告诉我说,在保守路的科普家里,老姑娘们有一个蓝柳陶盘,玛丽觉得那只盘子很像义卖会晚餐上的那只。她还说,她们愿意把它卖掉,因为这家的玛莎·科普一点儿也不会持家,只要能卖掉的,她决不会白白留着。就算她们不愿意卖,在斯潘赛山谷的卫斯理·奇森家也有一只,而且她知道他们愿意出售,只不过她不清楚这只盘子是否和约瑟芬姑妈家的一模一样。”
“那我明天赶紧去一趟斯潘赛山谷,”安妮果断地说,“你得和我一起去。这样会减轻我的心理负担,你要知道,因为后天我就要去镇上见你的约瑟芬姑妈,没有蓝柳陶盘,我没脸面对她呀。那次跳上客房床踩着了约瑟芬姑妈,我后来不得不向她坦白交代,而这次的情况比那次更糟糕。”
想起往事,两个姑娘都大笑起来——关于那件趣事,如果哪位读者不清楚而又好奇的话,我建议去阅读安妮早年的经历。
第二天下午,安妮和戴安娜踏上探寻陶盘的旅程。斯潘塞山谷离这里有十六公里,今天的旅程非常乏味。天气闷热,没有一丝凉风。最近连续六个星期没有下过一滴雨,干燥的天气让马路上尘土滚滚,四处飞扬。
“唉,我真希望马上能下场大雨,”安妮叹着气说,“什么东西都被烤干啦。干涸的土地让我心里很难受,树木伸出枝丫,仿佛在向上天祈雨。每当我走进我家的花园,看到枯死的花草,心里都感到阵阵伤痛。不过这比起农民的痛苦来还算不了什么。哈里森先生说,他家的牧场全部烤焦了,可怜的奶牛连一口鲜草也吃不到,每当他听到这些牲畜的叹息,心里都感到愧疚万分,这对它们太残酷了,可是他无能为力。”
经过一段让人厌倦的旅程后,她们到达了斯潘塞山谷,驾车转上了保守路。这是一条僻静的林间公路,两边绿意盎然,车辙间长满了绿草,看得出这条路很少有人光顾。两边年轻的云杉树排列整齐,密密匝匝,浓密的枝叶伸展开来,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公路。不过,偶尔也有一些稀疏的地方,可以看见一闪而过的斯潘塞山谷景象,农场后面的田地篱笆,一大片树桩,还有一片大火烧后的土地,现在长出了许多杂草和黄色的小花。
“为什么把这条路叫保守路?”安妮问。
“艾伦先生说,正如某个地方一棵树都没有,却会命名为林荫大道,这儿叫保守路也是同一个道理,”安娜说,“这条路上人烟稀少,常常从这条路上经过的只有科普家的老姑娘们,还有大路尽头的马丁·博维叶。年迈的马丁是个自由党人。保守党执政期间,把这条路修缮了一下,因此命名为保守路,以此来炫耀他们的业绩。”
戴安娜的父亲是个自由党人,而绿山墙的人从来都是保守党人,正是这个原因,戴安娜从来不和安妮讨论政治。
两个姑娘终于来到老科普家的庄园。从外表看,这里非常整洁,让绿山墙相形见绌。房子是老式的风格,坐落在一个斜坡上,所以房屋的一端下面用石头砌着地基。正房和外屋用石灰水粉刷过,白得晃眼。还有个传统的厨房花园,用白色栅栏围了起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看不到一根杂草。
“遮光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戴安娜沮丧地说,“我估计没人在家。”
事实正是如此,两个姑娘互相看着,束手无策。
“我们该怎么办呢?”安妮说,“如果那个盘子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那我就在这里等她们回家,等多久也无所谓。可要是不一样,我们再去卫斯理·奇森家可能就太迟了。”
戴安娜看着地下室上面的一扇小方窗。
“你看,那应该是储藏室的窗户,”她说,“因为这个房屋的格局我见过,跟纽布瑞切镇的查尔斯叔叔家的一模一样,他们家的储藏室窗户就在那个位置。恰好窗帘没有放下来,我们爬到前面那个小房子的屋顶上,就能看到储藏室里的情况,说不定就能看到那只盘子。你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很不礼貌?”
“没问题,”安妮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说,“我们并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才这么做的。”
很重要的道德问题解决了,安妮着手准备攀爬前面提到的那个“小房子”。它是用木板条搭建起来的,屋顶尖尖的,以前是个鸭棚。科普家的姑娘们已经不养鸭子了——“因为这些家伙脏得要命”——这个房子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只是偶尔让母鸡进去孵蛋。尽管如此,它也被刷上了石灰水,不过,树木已经有些变朽了。安妮把一只小桶倒放在一只木箱上,从最方便的位置爬上去,心里七上八下,老觉得这个房子摇摇欲坠。
“我怕它承受不住我的重量呀。”安妮说着,战战兢兢地走上房顶。
“把身子靠在窗台上。”戴安娜建议说。于是安妮斜靠在窗台上,透过玻璃往里边窥视。让她惊喜万分的是,她看到紧靠窗户的储藏架上放着一只蓝柳陶盘,正是她要寻找的那种。可是她正想看得更清楚点,灾难就降临了。兴奋不已的安妮忘记了脚下的危险,不再小心翼翼地靠着窗台,而是激动得跳了起来。转眼之间,她踩穿了屋顶,整个人就往下掉,幸好两只手平放在屋顶上,滑落到齐胸的位置,她就被死死地卡住,吊在了半空中。安妮使出浑身解数,怎么也把自己弄不出来,真是进退不得。戴安娜冲进鸭棚,拦腰抱住她这位倒霉的朋友,想用劲把她拉下来。